处所宾语初步考察
http://www.newdu.com 2025/12/23 07:12:56 华语桥 史有为 参加讨论
| 《大河内 康宪 教授退官纪念,中国语学论文集》,1997,东方书店,日本
处所宾语初步考察
史有为 零 引言 0.1 处所宾语向来缺乏严格的界定,《动词用法词典》(孟琮、郑怀德、孟庆海、蔡文兰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对此在语义和形式上作了一些限定,指出:语义上说明“动作或行为及于某处所或在某处所发生。”句法变化的形式上则“有些处所宾语和动词之间可加‘到’”,或者宾语可放在“到…里/内”。“有些处所宾语可放在‘在…上’、‘在…里’之中,整个短语或放在动词前或放在动词后”;“有些处所宾语后也可直接加‘上’”;“有些处所宾语可用加‘从’字或放在‘从…里’之中提到动词之前”。但是从第二语言学习和人工智能工程的角度考虑,这样的说明是不够的,人和电脑无法从中获得理解和生成的必要条件,因此仍然有必要对该类宾语在形式上和语义上作进一步的描写和解释。 0.2 《动词用法词典》主要是以北京话作为描写对象的。本文认为,词典作者在举出“名宾类”例语(作为例子的短语或句子)时,虽然会因编者不同而在举例多寡以及例语的代表性上有某些不统一,但是也肯定会考虑到宾语的代表性,因此例语内所收的处所宾语足可以囊括汉语处所宾语的各种类型,与其相配的动词也将有足够的代表性,尤其在北京话口语方面是如此。因此,本文以该词典列出的例语作为本文的基础语料,相信在此基础上作出的分析也应具有较好的涵盖度与说服力。 0.3 本文采用统计分析与形式对应、语义分析与形式对立相结合的方法。重点考察:无介词形式的处所宾语和有介词形式的处所补语之间的对应关系;处所宾语同相关论元成分的关系;不同类的处所宾语同与其充当者的形式之间的关系。最后进行必要的综合讨论。本文采用手工统计,可能会有某些误差,但相信不至于影响结论的基本精神。
一 初步分类和统计
1.1 “处所宾语分布。《动词用法词典》选收1328个动词,按义项出条,共有2117个单义动词,其中标明带处所宾语的共有568个。经过检查,另有“排①1”(此处数字为原词典标号。为简化形式,以下均略去)和“忘”共2个,也可以带有该词典所认为的处所宾语,补入计算,合计共有570个单义动词。 带处所宾语的例语共有1550条(同一例语但有两种理解的,作为两条计算),经笔者检查,按照词典编者的处所宾语标准,某些动词还有遗漏(包括遗漏某种处所宾语类型),连同以上补充的两个动词的例语共补入15条(出现在11个动词中),总共得1565条。例如: 忘家里了| 排门口儿| 跪搓板| 点鼻子里| 住旅馆里| 乌鸦落房上了| 浇二号模 子| 留厂里| 打左角| 抹手巾| 闻闻手 有些例语作为处所宾语可能有疑问,这是留待下文讨论的。 1.2 处所宾语初步分类。本文按宾语前、动词后可否加入“在”或“到”,把宾语大致分成4类: 1)只可加“到”(包括动词为“到”)者,以D作为代号。 2)基本上只可加“在”(包括动词为“在”)者,以Z作为代号。 3)加“到”或“在”两可,以L作为代号。 4)不能加“到”或“在”,以F作为代号。 带D类宾语者,共62个动词(其中有10个可以兼带F类宾语);带Z类宾语者,共96个动词(其中有20个可兼带F类宾语);带L类宾语者,共117个动词(其中有38个可兼带F类宾语);只能带F类宾语者,共295个动词(另有68个动词兼带D/Z/L类宾语,如果两项相加计算,则得363个动词)。有个别动词可以兼带D/Z/L几种宾语,为统计方便,都以其中一种宾语为主加以统计。以上分类是相对的。 1.3 各类宾语概况。 1)D类宾语共在62条单义动词中出现,占全部带处所宾语动词570个的10.87%。其中52条是只出现D类宾语的,占9.12%(另有10个动词可兼带F类宾语)。该类宾语的例语共有120条,约占全部例语1565条的7.66%。例如: 沙子吹眼睛里了| 滚沟里了| 一口吞肚子里了| 拾篮子里了| 淋药 壶里| 添碗里| 开便道上| 放天上(去了) 2)Z类宾语共在96个单义动词中出现,占全部带处所宾语动词570个的16.84%。其中69个动词只出现Z类宾语,占12.10%。该类宾语的例语共有233条,约占全部例语1565的14.88%。 这里所谓带Z类宾语是从宽泛的意义上说的,并非完全地、绝对地不能加“到”。具体来说可以分成两种情况: Za. 基本上不能加“到”,但是相当部分可以放在“到…去”中。共有32个动词(包括兼带F的10个动词)82条例语。例如: 东西在桌子上| 在组织| 住北京| 丢路上了| 停新加坡港| 留南京了 Zb. 以加“在”的形式为主,有时也可以加“到”,也可以放在“到…去”中。共有64个动词(包括兼带F类的20个动词)151条例语。可以认为是Za类和F类之间的中间状态。例如: 放办公室| 趴沟里| 铺地上| 蘸馒头上| 界线划哪里| 养笼子里 3)L类宾语共在117个动词中出现,占全部带处所宾语动词570个的20.50%。其中79个动词只出现L类宾语,占13.85%。该类宾语的例语共有234条,约占全部例语1565条的14.92%。例如: 躲地洞里| 树叶落地上了| 沉深水区了|泼菜地里| 搀煤里| 扔我头上了 4)F类宾语共在295个动词中出现,约占全部带处所宾语动词570个的51.75%。另有68个动词兼出现其他三类宾语(已计入前三类),约占11.92%。如果把这68个动词重复统计入内,则该类有363个动词,全部动词则有636个,则前者为后者的57.07%。该类宾语的例语共有978条,约占全部例语1565条的62.49%。例如: 流传各地| 摸这儿| 伤哪儿了| 捆中间| 留心后面| 抄小路| 烫手上了
二 处所宾语的构成形式
2.0 处所宾语构成形式的分类。处所宾语核心部分的构成形式有5种: 普通名词+方位成分(包括已经词化的,如“天上”;还包括含有方位意义的一些词语,如“门口”、“桥头”。以下用“名方”代表); 方位处所词(除一般复合方位词外,还包括处所指代词以及某些单用的单音方位词和不常提到的复合方位词,如“这里、哪儿”“东、北”和“左上角”,以下用“方处”代表); 地名(包括可作为地名用的学校商店名和该词典认作处所宾语的专名,如“北京大学”、“(通过)辛亥革命”。以下用“地”代表); 开头含有方位成分的名词(如“里屋、南房”。以下用“方名”代表); 普通名词(不属于以上类型的名词。以下用“名”代表)。 另有一类是动词和名词宾语的组合已经或正在熟语化者(包括已经或正在变成词或熟语的。如“到站、上学、太阳落山、走钢丝”。以下用“熟”代表)。 2.1 D类宾语形式。 2.1.1 分类统计。D类宾语共有120条例语,出现于62条单义动词中。各类构成形式占有的例语数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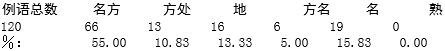 2.1.2 宾语同“去/来”的关系。D类宾语例语中原来有43条在宾语后加上“去”或“来”(极少数,仅2条)的。实际上宾语后(包括前面加“到”时)可带“去”或“来”的形式共有113条,占D类例语的94.16%,其同现的倾向性十分明显。个别不能加上的(如“到站、举高处”)都是可以解释的。例如: 那么个大个儿调前边去了| 蚂蚁爬洞里(去了)| 都把他挤墙角(去了)| 撵外头 (去)| 弄河里(去)| 把他们叫这边(来)| 接家里(来) 2.1.3 方言中的表现。在吴语中,相当多的该类宾语是不能说的,必须使用有“到”的介词短语形式。例如: 北京话:把这块木板拖院儿里(去)| 跑亲戚家(去)了| 退山头上 上海话:拿格块木板拖到院子里向(去)| 跑到亲眷屋里向(去)勒| 退到山头浪向 常州话:拿至块木板拖到院子里向(去)| 跑到亲眷家勒(去)连| 退到山酿 因此,从某个角度说,这里的处所宾语可以认为是介系补语的省略形式。 2.2 Z类宾语形式。 2.2.1 分类统计。Z类宾语共有例语233条,出现于96个单义动词中。这里的Z类宾语实际上包含Za和Zb两个部分。分类统计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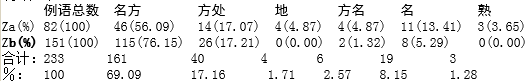 “名词+上/上面类”,108条例语,占该类的67.08%; “名词+里/里边类”,36条例语,占该类的22.36%。 2.2.2 同“去/来”的关系。这类宾语在未曾加“在”时,有时可以带上“去/来”,而且相当一部分可以出现在“到…去”中。但是一旦加上“在”(包括动词已经是“在”者),就几乎完全不能带“去/来”了。统计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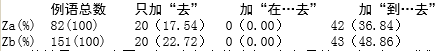 我一直在办公室| 丢路上了| 忘家里了| 掉床上了 当然也有意志动词,例如: 把书带身上| 馒头蒸上屉| 他把东西都留这里了| 这个螺丝应该上这里 这说明“在”同趋向没有太大的关系,倾向于表存在的静态。相反,“到”则与趋向的关系十分密切,它倾向于表过程的动态。而无介词形式则是介于以上二者之间。 2.2.3 方言中的表现。在上海话中,“在”相当于“勒辣”或“勒”,而在常州话中则用“勒”表示。上面的Z类除了Za中的“在”(组成“在世、在位、在职”以及表示参加、属于义,组成“在组织、在党”等)以及某些北方口语中专用的词语无法换用或增加上述方言词以外,一般都需要换用或增加这些方言词。例如: 北京话:东西在桌子上| 住北京| 把底稿留家里| 丢路上了 上海话:物事勒辣台子浪| 住勒北京| 拿底稿留勒屋里向| 落勒路浪勒 常州话:东西勒台子酿| 住勒北京| 拿底稿留勒家勒| 落勒路酿连 这说明,Z类宾语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看成是有介词形式处所补语的省略形式。 2.3. L类处所宾语。 2.3.1 分类统计。L类宾语共234条,出现于117个单义动词中。从宾语构成的形式上出发,各类宾语占有的例语可统计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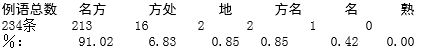 倒水里(去)了| 躲地洞里(去)| 打球台角上(去)了| 扔我头上(来) 了| 他分北京(来)了 这时一般都可以在前面加上“到”,但是很难加上“在”。 2.3.3 方言中的表现。在上海话和常州话中,它们的对应是不整齐的,一般都可以用相当于“在”的形式,大部分也可以同时用相当于“到”的形式,但是它们的常用形式可能不完全相同,有的倾向于“在”,有的倾向于“到”。例如: 北京话:把鸡蛋打(到/在)碗里| 投(到/在)信筒里 上海话:拿鸡蛋敲勒碗里向| 笃到/勒信筒里 常州话:拿鸡蛋敲勒碗勒| 笃勒/到信筒勒 2.4 F类处所宾语。 2.4.1 分类统计。F类宾语共有978条,出现于363个动词(包括68个兼出现其他三类宾语的动词)中。分类统计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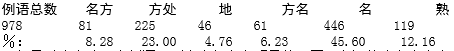 2.4.2 同“去/来”的关系。“去/来”表示的是趋向,而且是表示趋向动作进行的终点或某个命题成分移动的终点。按照这种理解,不属于该类语义的宾语,其后的确不能带“去/来”,但是属于该类语义的也仍然有许多不能带。例如: 登山去| 下车间去| 上窗台上去| 闯关东去 ×签(缝)下边去| ×到达广州去| ×登记表格去| ×抓伤口上去 目前我们很难找到有说服力的、可以概括以上正反两种情况的条件。 2.4.3 方言中的表现。北京话中加“到/在”表示终点。在上海话和常州话中,表示终点的例语许多也不能加与“到/在”相当的成分,其中有的是双音节动词,有的是北京话风格的,有的是熟语性单位,除此之外大部分仍使用相当于“在”的成分。例如: 北京话: 登记表格| 串胡同| 进大门| 上伤口上 | 煮锅里 上海话: 登记表格|?走弄堂| 进大门| 遢勒伤口浪| 烧勒镬子里向 常州话: 登记表格|?走弄堂| 进大门| 遢勒伤口酿| 煮勒锅勒 如果把有介词和无介词之间的区域看成是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的话,那么,北京话显然走得更快些。
三 处所宾语的语义类
3.0 处所宾语的语义分类。从处所宾语同动词(以及相关论元)的语义关系来看,有的是动作或论元移动的终点,有的是动作发生的场所,有的是动作及论元经过的通路(经路)。根据实际出现的例语,可以把宾语分为以下7类: 终点:〔例〕切桌子上| 挂(挂电话)北京| 醉外头了 起点:〔例〕下飞机| 离开重庆| 抽里边 经路:〔例〕过马路| 抄小路| 经过赤道 方向:〔例〕脸对着窗外| 通左边这条管道| 扇这边 起点-终点:〔例〕来往两地之间| 转学校| 过户头 坐标:〔例〕靠近山西| 离车站(很近)| 绕着桌子(转) 动作场所: 转了一下菜市场| 爬山| 流传各地 另外,例语中还有一部分表示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处所,而是“受事、工具、对象、方式、原因/目的”等类别,我们也立项予以统计。这5类的情况是: 受事:〔例〕批文件| 炸山头| 占领别国领土 工具:〔例〕坐飞机| 烧炉子| 插手 对象:〔例〕担心家里| 教毕业班| 问公安局 方式:〔例〕唱堂会| 吃食堂 原因/目的:〔例〕赶路| 赶庙会 3.1 D、Z、L三类宾语。带这三类宾语的动词共273个,例语共585条,宾语都是表示动作以及相关论元移动的终点的,因此,不再予以分类。三类之间的区别不在于是否终点,也不在于宾语本身,而在于它们加上介词后(已成为补语)所带有的“状态”不同。(请参见以上第二节) 3.2 F类宾语。《动词用法词典》收入的该类宾语比较复杂,包括了3.0中的所有类型。具体统计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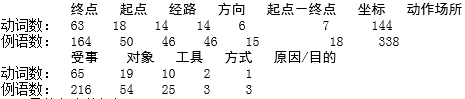 首先是语义,观察宾语在意义上同动词所表示的动作与相关论元之间的关系。 其次是形式上的依据,即转换成何种有介词的同义形式,以及询问形式。比如,起点类一般可以转换为“从…V”,动作场所类一般可以转换为“在…V”,方向类一般可以转换为“向/朝…V”,受事类一般可以转换成“把…V”,而且有动结式,对象类一般可以转换成“对/跟…V”,工具类一般可以转换成“用…V”。询问是一种广义的转换,问“哪儿”是处所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足条件,就是说处所一定可以用“哪儿”来询问,但非处所也并非不能用“哪儿”询问。如果询问的是“怎么V”或“干什么”,那宾语就不大可能是处所了。 我们之所以把语义放在首位是因为有很多宾语没有同义的有介词形式,尤其是熟语化的形式。有的似乎有,其实内涵(包括意味)很不一样。而询问形式也常常有“V哪儿”和“V什么”两种,不容易把握。下面我们举例说明归类的具体操作及其存在的困难: “奔(去声)目的地”,可以有“奔向目的地”的同义形式。以此确定为方向类。 “跑码头”,语义上看既可以认为是起点-终点,也可以认为只是动作的终点。“跑码头”一般是游动的,但是“跑广州”却相对固定,为了在同一词项下尽量取得一致,本文选择了终点类。这说明分类或归类是相对的。 “到达广州”,由于动词的限制,已不可能有另外的有介词同义形式,只能根据语义确定为终点类。 “大军压境”,由于动宾甚至连同主语已经熟语化,也不能有相当的有介词同义形式。此处归入坐标类。 “吃食堂”,并非仅仅在食堂里吃,而是依赖食堂,因此是一种吃饭的方式,从食堂里把饭菜买回家去吃也是“吃食堂”。至于“吃全聚德”,则是动作场所。这二者在询问形式上是不同的:前者问“怎么吃”,后者问“吃哪儿”。因此需要分别处理。 “坐飞机”,不是坐在飞机上,而是乘用飞机,飞机是工具。此处询问“坐什么”,而不问“坐哪儿”。 “唱堂会”,整个短语已经熟语化了,有专门意义,也很难有同义形式,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堂会是一种演出方式,并非单纯的什么处所。询问“唱什么” 而不是问“唱哪儿” “裹伤口”,可以有相当的有介词同义形式:“把伤口裹一裹”,还可以询问“裹什么”,以此可以确定为受事类。 “踏地雷”,这和“踏泥里了”不同。后者的“踏”是不及物动词,后面接处所,而前者的“踏”已经变成及物动词,需要被支配者。后者询问“踏哪儿”,而前者询问“踏什么”,还可以转换成“把地雷踏响了”。因此前者是受事类。 “教毕业班”,毕业班怎么成了处所?我们可以说“给毕业班教数学”,还可以说“教毕业班数学”,这同“教毕业班同学数学”是同义的。同时询问的是“教什么”,而不是“教哪儿”。显然这里的毕业班只是对象。 “经过辛亥革命”,只能询问“经过什么”,绝对不能问“经过哪儿”,这和“经过赤道”很不一样,后者是属于处所的经路类,而前者虽然有经路的意思,却不是处所类。然而,为了统计方便,本文也暂时把二者归为一类。 以上举例一方面说明分类具有相对性,另一方面又说明有些宾语归入处所是有疑问的,不能仅仅看所用词语是否处所词语。无论如何,有一条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F类中所包含的语义类型是绝不能用“处所”二字可以概括得了的。有的只能说处所意义只是其中的部分含义,同时还有其他意义;有的则显然是错认成了处所。 3.3 宾语语义类型和充当者形式之间的关系。以上分类是相对的,但也可以以此为基础,观察它们同充当者形式之间的关系。上面已经说明,D、Z、L三类都是表示终点的,加上F类,例语可以统计如下:  3.4 动词类型同宾语语义类别之间的关系。就终点类而言,动词的及物与否,动词的有意志与否,似乎与宾语类别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例如: 及物: 盖桌子上| 桥搭哪儿| 泡酒瓶子里| 把灯装墙上 不及物:住北京| 站门口| 在组织| 死家里了 意志: 把手抄袖子里| 签原稿上| 铺地上| 鞋脱地上 非意志:掉路上了| 挂裤腿儿上了| 忘家里了| 淋衣服上了
四 与处所宾语直接相关的论元类型
4.0 关于同处所宾语直接相关的论元。这里指的是经过动词(动作)的引导而同处所宾语发生直接关系的论元(本文称为G论元),它们可以在例语中出现,也可以不出现,而所发生的关系可以落实在宾语的语义类型上。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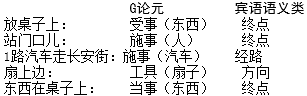 施事:托盆底(用手)| 屁股不能着椅子(用屁股) 工具:照上身(用镜子)| 绕脖子上(用绳子) 显然,G论元的类型同动词的个体性质最有关系。为了简化统计,我们以动词作为单位。动词与G论元之间基本上是一对一的关系,但偶尔也会出现一个动词有两个相关G论元(本文用“施事/受事”这样的形式来表示)。例如: “(手/图钉)按墙上”: (G论元)施事/受事 4.1 对G论元的统计。我们按照宾语的D、Z、L、F四类分别对动词和例语进行如下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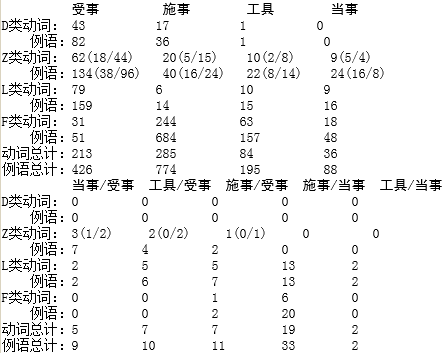 4.2 关于G论元与宾语语义类和宾语形式二者之间的关系。为了更清楚地看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把宾语语义类中 的“地”、“方名”、“名”、“熟”四项合并为“名词”。这样可以列出如下每类G论元出现的优势形式(论元后数字为该种例语数,横线表示缺该类例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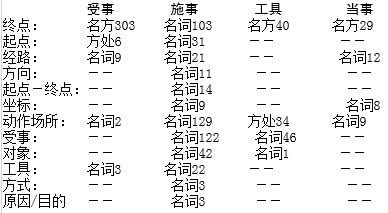
五 总的讨论
5.1 有介词形式和无介词形式之间的对应。 5.1.1 “到”和“在”的分布与分类。本文试图用加介词“到”和“在”的方法来鉴别处所宾语的类型,然而实践的结果证明,这种方法是很难达到以上目的的。从统计看,“到”和“在”的单独分布区十分小(“到”有62个动词,“在”有32个动词,以“在”为主的有64个动词),大部分则是双方重叠(有117个动词),呈现“交”的状态。因此基本上不能作为分类的依据。同时,这种分布的必然性也不能在动词语义上获得解释,并不能在宾语充当者的形式上得到完美的解释。因此,按照同介系补语形式的对应/转换来分类只有部分可能,其价值是很有限的。 5.1.2 存在一种简化过程。北京话中不加“到”、“在”现在已经是一个常态现象。许多无介词形式在口语中可以看成是语音脱落造成的介词省略。这种脱落过程至今在口语中仍然明显地存在着。例如: 放在桌儿上-→放de桌儿上-→放(音渡n)桌儿上-→放桌儿上 寄到家里-→寄de家里-→寄(音渡r)家里-→寄家里 这应当是这类无介词形式的一个来源。但是这只能解释部分。就现在看到的情况而言,这种无介词形式已经比加“到”、“在”的形式更为普遍和自然。许多例语从语义上看应当属于加“到”或“在”的范围,但是实际上却不能加或加上后反而不自然。这说明北京话正在经历一次形式简化过程,在口语中不加介词的形式已经成为主要形式,并且已经开始走上一条脱离介词的形式独自发展的道路。古汉语中原来就有的这种形式,以及现代汉语中存在的以无介词形式来表示起点、经路等处所的方式,不但从给简化提供了基础,也给简化增加了发展的动力。这与许多南方方言是不同的。这是一种新的模式,一方面给学习者带来了方便,同时也给使用者带来了理解上的某些困难。 还可以看到:“到”和“在”在语义上的区别在相当部分的正在逐渐消失,尤其是在L类表示终点的例语中,有些宾语加上介词“到”或“在”后,二者基本上可以互换而意思上没有什么差别。有的也只是留有趋向意味上的些许不同,加上“到”比加上“在”有时更多一点儿趋向意味。至于趋向意味,口语中则用后加“去”来补足,以弥补失去介词“到”后表义上的不足(当然这只是弥补,而非等同)。例如:“扔里边儿”和“扔里边儿去”。这说明相当一部分动词的后面,这二者的区别已经变得不重要了,甚至没有什么区别了,这也就为口语中“到/在”介词的消失,即为新模式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5.1.3 宾语形式和补语形式的区别。在处所问题上,我们通常称动词后无介词形式为宾语,动词后有介词形式为补语。其实,这两种形式在表达上是很不相同的,在分布上也是不完全相同的。在表达上有两个主要差别: 1)补语形式是明确的,而宾语形式却是含混或混沌的。加“到/在”就是表达论元移动或动作的终点,含义是明确的。“到”和“在”的区别只是,前者侧重于动态,有趋向意味,因而后面一般都可以带“去/来”,而后者侧重于静态,因而一般不能带“去/来”。宾语形式,尤其是名词和方位处所词形式,则常常难以确定处所的类型,有的存在二义性,或者跟补语的含义不同。例如: “存旅馆里”:存在旅馆里(终点.静态);存到旅馆里(终点.动态) “排这儿”:在这儿排(队)(动作场所);排在这儿(终点)。 “窗户开北面”:窗户开在北面(终点);在北面开窗户(动作场所) “写黑板”:在黑板上写字(动作场所);写黑板字(方式) “挪里屋”:挪到里屋去(终点);从里屋挪(东西)(起点);挪里屋 (的东西)(受事) “提这儿”:可以是“(从那儿)提到这儿”(终点〕,更可能是“提着 (水壶的)这儿”(动作场所)。 “吃食堂”:既可以在食堂吃,又可以买回去吃;既表示依赖对象,也表 示一种方式。本文暂时处理为方式类。 2)加“在”的补语形式表示的是事例,动补之间比较松散;宾语形式“名方”、“方处”和“地名”表示的也是事例,但动宾之间相对来说比较紧密;宾语形式“名”表示的则是事类,动宾之间比较紧密,常易熟语化。事例和事类的区别在于:事例的信息焦点在例语的后部,一般只提问后面的部分;事类的信息则倾向于整体,一般整体提问动宾,因此给人的感觉是在说明动作方式和类别。例如: “跪在地板上”:他跪在哪儿? “写在黑板上”:你写在哪儿? “跪地板上”: 他跪哪儿? “写黑板上”: 你写哪儿? “跪地板”: 他干吗? “写黑板”: 你干吗? 至于可以加“到”的补语形式则一般没有以上事例和事类的对立,只是松紧的区别。因为带上方位词的形式一般是不能删除方位词的。它们也没有熟语化形式。例如: “传到他手里”:传到哪儿了? “传他手里”: 传哪儿了? ד传他手” 由此可知,表示终点的无介词形式(所谓宾语,主要是“名方”形式),实际上许多仍是一种补语,只不过比有介词形式更紧密罢了。 3)有介词形式和无介词形式不是简单对应的。本文统计已经揭示,许多同样表示终点的处所宾语(L类宾语)是没有相对应的有介词补语形式的。另一方面,也并非所有的“到…”补语都能把“到”省去,或者意思大变,或者不能成立,或者省去后相当别扭。例如: 我走到上海。(对比:我走上海--意义是“我从上海走”,表示经路) 挖到河底。(对比:挖河底--表示动作的受事) 他边走边唱,一直唱到办公室。(不能省略“到”,否则不能成立) 汽车开到西安。(省略“到”后句子很别扭) 这说明补语形式和宾语形式它们各自都有部分成员不相对应,都有一定的独立地位。所谓的简化过程,即口语中有“到”形式正在有条件地向无“到”形式过渡,也是有条件的。有介词的补语形式依然有存在的价值。 5.2 处所宾语的再分类。 5.2.1 分类的困难。宾语是一个涉及范围很广的单位,所包含的类型也相当多,仅仅用一个“处所宾语”来概括是远远不够的。根据在不同语义下形式对立的原则,其中表示论元和动作的终点、起点、经路、方向等都是应当分别标明的类型。而动作进行的真正处所(动作场所)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语义上,都是不能不分别的。对于自然语言理解和生成都是必不可少的,对于第二语言学习和应用也是十分需要的。 可以从语义和形式两个方面给处所宾语再分类。但是,由于处所宾语前后没有形态标志,因此形式上的分类只能依靠转换。然而根据 5.1.2 和5.1.3,宾语转换成有介词形式常常同语义发生不协调。有介词形式只能作为一种可能条件,而不能作为必要和充足的条件。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北京话口语中已经开始了一个无介词模式独立发展的过程。 在分类实践中,我们发现有很多宾语存在着如下多种定类困难。 1)宾语语义类别的混沌现象。所谓“混沌”就是同动作和G论元的语义关系含混,不能按照通常给出的类目定类。例如: “吃食堂”:可以在食堂吃,也可以从食堂里买回去吃,既是依赖对象,又是一种 方式,语义关系很模糊。 “蹲监狱”:可以理解为蹲在监狱里,也可以理解为在监狱里蹲着。 “跑码头”:是从一个码头跑到另一个码头,不断变换码头,依靠这种方式来获得 生活来源。其中既有起点-终点,又有方式。 “闯关东”:既是“到”关东闯荡,又是“在”关东闯荡,并以此开辟谋生之道。 2)宾语语义类别的中和现象。所谓“中和”是指原来对立的两个类在某种环境下失去对立,以其中的哪一种定类都可以。例如: “进攻左翼”:此处“左翼”既是受事,也是处所。左翼不过是敌人的一部分而已。 受事和方向在此处中和了。 “参观校园”:此处“校园”既是终点,又是受事。我们既可以提问“参观哪儿”, 也可以提问“参观什么”,二者在这里是等价的,也就是中和了。 “骑上边”:此处“上边”既可理解为终点,又可理解为动作场所,二者不对立。 “流行全国”:此处“全国”既是终点,也是动作场所,二者也中和了。 3)宾语语义上存在二义性。例如: “排(排队)这儿”--义1:排到这儿。表示终点。义2:在这儿排。 表示动作场所。 “腾里屋”--义1:腾出里屋。表示起点。义2:腾到里屋。表示终点。 “提这儿”--义1:(把水壶)提到这儿。表示终点。义2:提(水壶)的这儿。 表示动作场所。 “夹中间”--义1:夹住(物体的)中间。表示动作场所。义2:夹在(两个部 分的)中间。表示终点。 4)宾语的转换形式语义不明确或者无转换形式。例如: “着眼全局”--“着眼于全局”:该词典对动词的解释是:“〔从某方面〕观察 考虑。”其中“于”相当于“从”,同一般的对应不一致。按照“于”应该定类为终点 或动作场所,按照“从”则应该定类为起点。 “跑路”:没有对应的有介词转换形式。“跑在路上”不是“路”加“在”,不能 以此确定为终点。 “看内科”:没有对应的有介词转换形式,不清楚“内科”是疾病的分类,还是医 院的科室,或是医学上的分工类别。 “生炉子”:没有对应的表示处所的有介词转换形式,而且可以说“把炉子生上火 /好”,很难确定是何种语义类别(本文根据询问“生什么”等暂定为对象类)。 由上可知,处所宾语的语义分类是相对的。以上除第3项可以分化外,另外三项很难处理。就实际统计过程所见,大部分是可以确定的,但仍然有一部分无法明确确定,只能作权宜处理。我们当然可以把这些难以分类的宾语分别定成一个个特殊的类,但是那样一来,类的价值就消失了。因为类一定有相当数量的支持,它的价值就在于不是个别的,可以集合一批成员去认识、去使用。 5.2.2 共济处理。由此看来,较妥善的办法应该是既有一个大致的有点模糊的类,又需要具体掌握每个动词所控制的具有一定个别性的命题框架以及由此生成的表达形式。这就是所谓的“共济”。 对于后者,比如可以设立一种以动词为控制中心,配合论元以及其他相关重要成分的模式来描写动词及其相关命题的生成。就是说既有词义描写,又有生成必要成分的规则(包括词语形式和相对位置)。例如: “跳”:施事-人或动物【~动词】(〔例〕谁跳); 工具-人或动物的腿【施事+用~动词】(〔例〕你用腿跳); 方向-向上/同时向前【施事+往/向~动词】(〔例〕你往/朝/向前跳); 结果-〖离开原地〗经过某点【施事+动词~】(〔例〕他跳水沟了)/ 到达某处【施事+动词~】(〔例〕他跳台阶上了)。 “吃”:施事-人或动物【~动词】(〔例〕小狗吃了); 工具-人或动物的口/其他工具【施事+用~动词】(〔例〕小狗用嘴吃/ 我用筷子吃); 受事-生物类及其制成品/药物类【施事+动词~】(〔例〕他不吃肉/我吃 了很多中药); 终点-吃入的物体到达的处所【〖施事〗+把+受事+动词+〖到/进〗~ /〖受事〗+〖施事〗+动词+〖到/进〗~】(〔例〕我把扣子吃〖到 /进〗肚子里了/钮扣〖我〗吃〖到/进〗肚子里了); 动作场所-人或动物可进行动作处【在~动词+〖受事〗】(〔例〕在家里 吃〖黏糕〗); 动作目的场所-具体饭馆名【〖施事〗+动词~】(〔例〕〖我们〗今天吃全 聚德); 动作依赖场所-泛指的饮食处(“食堂/馆子”)【〖施事〗+动词~】(〔例〕 〖我〗老吃食堂)。 以上“【】”表示生成时的位置,“〖〗”表示生成时不出现,“-”表示该成分生成时的许多位置,“/”表示或者。由于这是个体的描写,也鉴于以上论述中所显示的分类上的困难,因此参与构成的成分可以不拘目前的术语或类别,可以用较为普通易懂的词语。这只是初步的构想,其中还有许多细节必须讨论。总之,词的个体语法框架和生成规则并不就取消词语总体的语法框架和生成规则。这是两个相辅相成的彼此共济的方面。 5.3 可能的处理模式。 5.3.1 可能的理解模式。上面的统计分析告诉我们,试图用有介词形式来控制北京话这的无介词形式是不能成功的,因为它们之间缺乏整齐的对应关系。在考察了动词的语义类型同处所宾语的关系以及动词类型与主语位置论元角色类型相关条件下同处所宾语的关系之后,我们不得不宣布,至今还找不出它们之间明确无误的规则。那么北京人或掌握北京话的人是如何正确理解的呢?在经过考察以后,我们发现,人们可能采取的方法可能有三种: 1)动词语义形成的隐含命题框架提供了处所的类型,在积聚了相当多动词提供的命题框架之后,就可能形成处所类型和充当词语构成类型之间的倾向性联系。这种联系可以表现为数量关系,并按照数量的大小形成不同的序次。这是一种非确定性规则。这种序次可以大体表现在本文所统计的各种处所宾语出现的次数上,以及按照次数所列出的次序上。这可以作为理解时的第一步,是预置条件阶段。 2)按照动词语义形成的隐含命题框架去直接确定处所宾语的类型。以上猜测之后,可以作为理解的第二步,也就是初定阶段,依靠命题框架删除猜测时的不确定因素,使理解调整到基本确定的状态。 3)在具体语境条件下,从几种可能宾语类型中确定最合适的处所宾语类型。这是最后的确定阶段。 我们设想,这三种方法的配合使用可能有这样几种方式: a.三种方法一起用,方法1作为理解的第一步;方法2作为理解的第二阶段,;方法3作为作为理解的最后阶段。 b.只使用2、3两种方法,即一开始就使用方法2进行初选,然后才用方法3来调整并选定。 这两种配合方式可能交替存在于人的理解过程。因此,对于第二语言学习者来说,需要向他们提供由统计支持的宾语类型序次,同时也要求他们掌握各个具体动词语义所体现的命题框架和具体的生成形式。至于第3阶段,就必须在活的话语中学习和掌握。这说明,在第二语言学习中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既有弹性的适当范围的倾向性规则,又有具体的个体性规则,而且还需要活的话语。这三方面都是不能缺少的,它们共同组成了一种柔性的学习模式。 至于自然语言理解,也可以模仿人的理解过程,提供不同类型处所宾语的序次,提供具体动词语义中所隐藏着的命题框架,同时还要提供在话语中处所宾语位置和类型的确定规则。这最后一项是最困难的,也是我们要努力的。但是对于人来说,由于人有很强的自学习能力和自总结规则的能力,我们可以不必让学习者耗费这方面的精力。 5.4.2 可能的生成模式。人在生成含有处所宾语的合格句子时,可能有以下一些阶段: 1)根据听到的句子/话语以及以前自己所生成的而且被肯定的句子/话语,形成一个大概的、模糊的规则/框架,包括不同类别处所宾语出现的可能程度及其同动词类别的一般关系,也包括语境条件下歧义消除规则、语句接应规则。该规则/框架是动态的,可以继续不断地通过接受新的句子/话语来调整或丰富。 2)在以上1的规则/框架指导下,根据动词提供的命题结构将需要表达的思想转化为语言形式框架。 3)在以上1的规则/框架指导下调整2的成果,在形式上尽可能地消除歧义、使语句得以接应为合格话语。 人工智能的自然语言生成也应该建立与以上三阶段相类似的模式。为此,必须在电脑中建立以上1的规则框架,并同时设置自学习、自调整功能;必须详细描写每个动词的命题结构以及可以转化的语言形式,并在电脑内建立相应的词汇语法库。 【后记】 修改完最后几个字,我已经精疲力尽。半年来,从抄写、制作卡片,到一遍、二遍以至三遍的分析、统计与复查,又到推倒一稿、否定二稿、再拟三稿,其间困惑、疑问和困难纷至沓来。现在这个稿子只是在估量了目前条件后的一种现实的处理,许多议题不得已而简缩或删除。因此,本文只能说是初步的考察与尝试。 1996年仲夏于大阪外国语大学 (本文载于《大河内 康宪 教授退官纪念,中国语学论文集》,1997,东方书店,日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