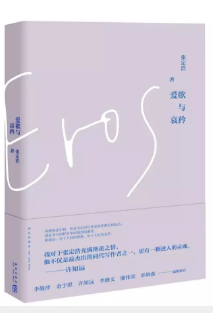
诗人、评论家张定浩日前推出新作《爱欲与哀矜》,书中收入他近十年所写的文学随笔二十余篇。其中所涉及的,从格雷厄姆·格林、爱丽丝·门罗到奥登、布罗茨基,从《斯通纳》到《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基本都是作者钟爱的作家与作品。某种意义上,这是一本阅读之书,也是一部写作之书。日前,张定浩与著名评论家、作家李敬泽在任晓雯的主持下就文学、批评及其他展开了一场谈话。
理论与文学
任晓雯:在张定浩这本新书《爱欲与哀矜》里面有一篇文章的名字,叫做《尽头与开端》,里面有几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比如说他引用杰夫·戴尔的话说,绝大多数学者写的书是对文学的犯罪,他本人也写到说,只有糟糕的庸常的学者才被冠以学院派的标签,就像只有生产不出好作品的作者才被称为文学青年一样。我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有时候会有共鸣,因为有时候写作的人聊起评论家,有的时候会觉得某位评论家写的东西有点隔,可能好像理论的成分太多了,不能深入小说内部。所以我就想请问一下两位,你们怎么在看文学评论中理论和文学的关系,以及怎么看“学院派评论家”这个词?
张定浩:关于学院派,刚才听到晓雯引述我的那句话,自己觉得很汗颜,因为那里面明显有一种火气,那是不应该的,是作为一个写作者应该避免的。那篇文章写的是英国作家杰夫·戴尔那本以劳伦斯为题材的小说《一怒之下》,我记得书中一开头他就说,我为了研究劳伦斯,我已经看了他太多的东西,也去过他所有生活过的地方,我已经筋疲力尽了,但是我依旧写不出来怎么办?他从他的焦虑开始写起。这让我很感动。我觉得他虽然是小说家,但他写一本虚构作品的时候依旧会穷尽所有需要和不需要的材料,他首先会自觉地去研究过去,也就是说,所谓文学也好理论也好,首先都是基于对过去的努力把握,不仅是一种无中生有的创造或规训。
李敬泽:晓雯的问题,也是理解定浩的写作的一个重要线索,就是何为批评家。定浩现在执著地声称自己是诗人,但好像大家主要还是承认他是一个批评家。我觉得,实际上存在两种批评家,一种批评家,他的背景和资源确实是高度理论化、学术化的,他的志向在于学术的知识生产,和文学的创作、阅读其实关系不大;还有一种批评家,包括我自己和定浩,当我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谈论鲜活的文学经验——那些更近于诗,难以成为知识,甚至是反知识的经验。这样的批评家可能更近于作家,作家型的批评家。前一种批评家必须“隔”,后一种批评家致力于“不隔”,这不涉及褒贬,腊肉和鲜肉各有各的好,但张定浩显然是一个作家型的批评家。
诗人与批评家
任晓雯:在我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做过学术青年,我对评论蛮感兴趣,但感觉写评论的东西跟写作的东西会在我头脑里面打架,我就迅速地放弃了评论。那么我就很好奇,在你们身上是否感觉到打架的时刻?比如说作为写作者的话,我自己觉得他一定是非常具有偏见的,因为偏见能够使得他产生独特的趣味,而趣味能够形成他的风格,但是如果作为评论家的话,是不是有的时候必须要放弃一些偏见,去容纳一些自己趣味之外的东西,尝试做出相对更客观的一些评论?我觉得好像这个问题有的时候会困扰我。
张定浩:我没写过小说,或许我可能是失败的诗人,在写评论文章的时候,对于行文措辞,可能会有类似写诗那样的要求。我觉得在写诗和写评论文章之间,其实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它们都需要积累,以及准确。
诗歌它需要情感的积累,写评论文章需要知识的积累。所谓的偏见,可能很多时候,如果自我积累到足够程度,这个偏见会消散一点,那个“小我”会一点点大起来,偏见会转化成洞见。其次,诗歌和评论的关系,有点像音乐和数学的关系,都需要一种内在的精细准确,都需要用准确的字句,去表达准确的情感,把别人不能够表达出来的感受用准确的词去表达和传递出来。
至于两者的不同,对我来讲,可能写文学批评的时候,我是面对一个要说服的人,一个抽象意义上的,男性的“他”,我心里面会想着他会怎么样跟我辩驳,我会在心里面一直设置一个对立者,他一直在跟我说你这样说不对,那样不对,那么我就在想我可以怎么样让你觉得我对;但是写诗的时候,我的对象可能是一个女性的“她”,是一个相对亲密的人,我只是跟她进行一种私语,我不需要说服她,我只是在召唤她出现。诗歌和评论,在这个层面,的确又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其实没有回答晓雯的问题,但是晓雯你的问题很好,激发我说了这些。
李敬泽:晓雯说到作家的偏见和评论家应当具有的客观,但对任何一个批评家来说,我觉得他一生中可能需要克服的一个幻觉,就是以为有某种巨大的“正见”已经被我发现。实际上这是非常虚妄的。客观是相对的,因为任何批评家的观点都立足于他特定的知识、经验、趣味,以及他的时代的具体条件等等,诸多因素影响之下,他形成了他的一套观点,这里边很难说不包含偏见。
有的偏见,就像人的毛病,有的毛病很坏,需要改,需要治,但是也不能全治好,成了一个没毛病的人。风格就是局限,从这种局限里也可能抵达定浩所说的某种洞见。我最近没事翻批评史,中国的文学批评史就是一个没完没了的纠偏过程,永远是后边的批评家在整前边的风,结果他刚整顿好了还没有多少年,后边又有人来修理他了,一个无穷无尽的辩驳和批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那个“客观”可能类似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它肯定在,它就在这个批评过程里,但具体到一个批评家,你得有多狂妄才敢宣称自己达到了这个绝对的客观。
批评家与表扬家
任晓雯:我想问一下,我现在感觉到有时候评论家成了表扬家,当然这不是评论家的本意,但可能因为大家在一个圈子里面,说出来的话和心里面想的会有所偏差。就比如说我自己的性格,我觉得我就是一个老好人,肯定不敢得罪人,我这种人是不能做评论家的。所以我想问一下两位资深评论家,你们会觉得有这种顾虑吗?你们觉得除此之外,一个好的评论家需要具备哪方面的性格和素质?
李敬泽:批评家的工作不是为了得罪人,当然也不是为了取悦人。在与作家、与读者的对话过程中,一个批评家的根本志业就是帮助这个时代获得一种自我意识,让好的、有价值的东西浮现出来、确定下来。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批评家会投入有形无形的争辩,有时他要独持异议甚至力排众议,不管他的方式是激烈的还是从容的,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他都应该是真挚的,但这种真挚不是他工作的全部,随便一个读者都能作出真挚的判断,而批评家除了说真话,还要讲道理,他要见多识广,要有领先的发达的感受力,要说出他自己的道理。当然一个时代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好东西是什么,这是一个艰苦复杂的过程。陶渊明在他的时代就没被认出来,到宋代才被苏轼他们认出来。批评最终是为了认出陶渊明,而不是为了找出世上的烂书,烂书自有废品收购站和造纸厂和时间进行“武器的批判”。
张定浩:我就觉得一个作家写出一本糟糕的书是值得同情的,而不应该去批评,他本身就已经很难过了写了一本糟糕的书。
李敬泽:是这样,我看到谁写一本很差的书我都替他不好意思,我也不想用他的愚蠢折磨我自己。
张定浩:前几年我自己倒的确写了一批言词尖锐的文章,但我觉得不是针对那些作家本人的,而是说,一个作家写了一部糟糕的小说,竟然依旧惯性般地获得那么大的赞誉,我觉得这些赞誉本身是不正常的。尼采说过,假想一个人具有一种他实际上并不具有的美德,这是接近疯狂的行为,会让一个人或一个时代一天天变坏,也就一天天不公正。在美学意义上和对自我生命的滋养上面,我非常赞成奥登的话,但另一方面,某些时刻写作有一种伦理学的要求,要求你面对一种不公正去发言。当然,这种发言也不能持续太久,太久自己也会生厌,所以我这两年也是尽量只评论自己喜欢的书。
李敬泽:定浩说的对。一个批评家要有战斗精神,这不是对着作家的,一个批评家和作家没必要搞成天敌;而是说当围绕着某一本书或某个作家的书,形成了某种文化趣味、文学风尚,如果我认为这是一个坏趣味或者是坏风尚的话,那么我们要为此而战斗。在这种意义上,批评家有他的文化责任、伦理责任,就像刚才定浩说的。
当然,批评家也并不必定真理在握。批评家和作家有时会形成张力,我们看到很多大作家经常对批评家咬牙切齿,美国人性子比较直,像海明威、诺曼·梅勒等都有在公众场合殴打批评家的劣迹。通常来讲作家的身体都比批评家好,我们真打不过作家。但这个事情如果换个角度看,如果批评家和这个时代最好的作家,能够形成精神上的张力、一种精神上的紧张、争辩、对抗,这本身就是一个时代文学的活力所在。
张定浩:这种张力的确有益。我在想,一个批评家基本都是立足自己时代的,他就置身在这时代看所有的问题;而好的作家往往都是超越自己这个时代的,他要等待下一个时代的读者,很多时候是这样。因此,这样的批评家和作家之间的张力,就会转换成这个时代和即将到来的那个时代的张力。
爱欲与哀矜
任晓雯:谢谢,两位都讲得非常好。那我接着想问一下,像定浩你写作很大的一个主题,就是爱,包括新书《爱欲与哀矜》,其实也是把爱放到了一个关键词上。但现在很多人会觉得,其实中国作家是缺乏爱的,包括我看到一些非常优秀的青年作家,也会被评论说太灰暗。而像许多西方作家,即便写人性的阴暗,比如奥康纳,可能因为有宗教的背景,就会每每在这样完全的人性黑暗当中召唤出一个恩典时刻,使得人性的黑暗和某种更高处的光之间构成某种秩序。但在中国当下,可能是一个信仰比较混乱和缺失的时代,好像就觉得始终在一个苦难和人性善恶的循环当中彼此伤害和打转。
所以,这个问题并不是关于个人写作的,它似乎是一个普遍的困境,想请教一下两位关于这个问题的困惑。
张定浩:写人性黑暗,写生老病死,这种东西特别容易打动人,而一个作家要避免这样的打动人,因为太轻易了,作为一个使用文字和掌握修辞的人,他要保持某种自律。如果一个人写得很糟糕就不管他了,如果一个人写得还不错,那么他更要警惕自己,不要滥用修辞的煽动力。要认识一些不好的东西,根本不用通过文学,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糟糕和不愉快,而对写作者而言,要有能力去看到那些更好的东西。我理解的好的写作,是一种转化的过程,把生活的阴面向着阳面转化,这种转化过程,就是创造,这不是伪善,而是说我们要有能力把黑暗的东西消化和转化,继续更好地生活,借助爱。
法国诗人布勒东说过一句话,艺术最简洁的定义就是爱。所以关于这个“爱”的主题其实不是我自己的发挥,而是在我阅读过程中,不停地会遇到这个词,不停地会遇到一些杰出的作家在谈论爱,因此阅读他们也是领受一种教养,爱的教养。
李敬泽:我觉得对着这么多人谈论爱是一件很要命的事,在这样的语境中谈论爱,很容易轻浮。
更何况,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爱欲,而不仅是爱。在柏拉图那里Eros(爱若斯)是一个中心概念,不只是《会饮篇》,他的对话的其他各篇里反反复复在谈爱欲问题。这个爱欲远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人和人之间的爱,更不是两性的那种爱,如果一定要比附,我觉得它类似于佛教里讲的,生命的欲和苦。
我们之所以要活着,而且大家都活得兴致勃勃,是因为我们有所欲,实际上就是有所爱,但是我们所有烦恼也都由此而来,这是佛家的看法。那么当柏拉图用“爱欲”这个词的时候,我觉得其中也包含着它的对立面:爱与恐惧,或者欲与苦。
在这个意义上说,爱欲本身就包含着哀矜。至于中国作家对人性对生活的看法,是看黑暗看得多一点,还是看光明看得多一点,我觉得不是这么简单,人生也不是这么简单。可能我们的问题恰恰是觉得可以有一个简单的方案,可以决定是从黑暗的角度进入,还是让世界充满爱的角度进入,这样简单的角度,都不能真正看清我们自己的生活和内心。我想我们是欲着也同时苦着。在爱欲中充满生命的力量,同时也充满了生命的渺小、卑微和痛苦,这些,我们都要面对。
所以,小说家不是应许什么,我觉得他们也没有能力应许什么,他们只是在爱欲与哀矜中,力图使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有光芒焕发出来。
张定浩:说到光芒,我知道敬泽老师现在开了两个文学批评写作之外的大专栏,一个是关于《左传》的,回到古典;一个是立足当下,把那些“痛苦”的批评家生活写成虚构和非虚构混杂的文本。
李敬泽:这就是爱欲,痛苦中或许包含着隐秘的幸福和快乐,当我感到开这个会或者做这个活动很烦很痛苦的时候,至少我可以回去把它写成小说。
张定浩:对,这可能是写作者(创造者)才具有的快乐,他所有的痛苦,所有的不愉快,都可以变成他的素材,以至于他所经历的事情都成为有价值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