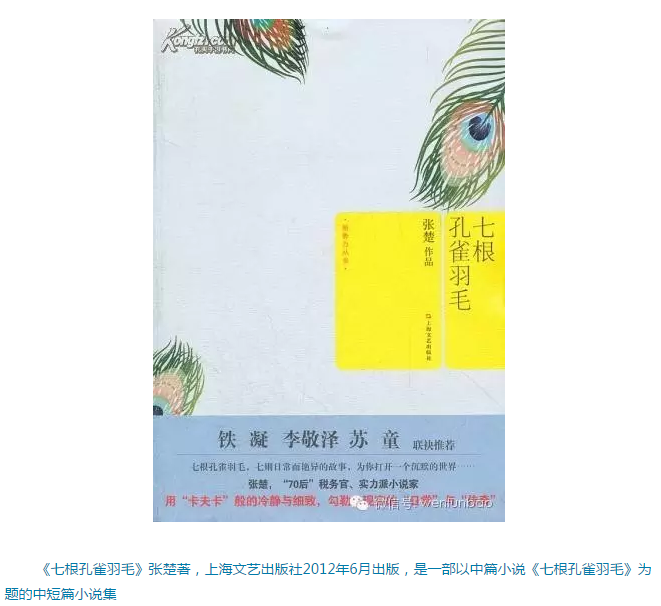
张楚的中篇小说《七根孔雀羽毛》(《收获》2011年第1期)的话语风格基本秉承了新写实主义小说流派的一贯特征,并力求在现代新语境下,运用更为开放性的写实手法,还原生活本相,不动感情地叙述日常生活中的庸人琐事,喜剧化效果明显。读他的小说,总能让人看到刘震云、王朔的影子。
作者看似站在“新写实小说”的延长线上来从事写作,其实并不如此。形式因素仅仅是张楚处理文本结构的某种美学效果,而作为当代文坛的新锐作家,他的小说《七根孔雀羽毛》同时也具有其独特的当下性情感基调,它不像“王朔式”调侃那样肆无忌惮、玩世不恭,又比“刘震云式”的灰色幽默多了些许忧郁和颓废。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似乎被某种莫名的情绪压抑着,性格扭曲,行为怪诞,就如同一辆笨重的卡车抛锚后滞缓的惯性滑移。
《七根孔雀羽毛》采用近乎“流水账式”的碎片化(现在与回忆相交织)絮语,讲述着现代人平淡地近乎荒诞的日常生活,冷酷地暴露出中国小县镇在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所形成的不伦不类的文化景观,以及生活其中的人们畸形的存在状态。冷峻、平静的叙述背后是对“物质丰收/精神荒芜”主题的严肃思考与质询。恰如作者本人在小说创作谈(《一个人杞人忧天<七根孔雀羽毛>创作谈》)中所言:“现实生活中,稀奇古怪的事越来越多,不妨以我们这个小镇为例说上几件:朋友楼上住着的两家人,其实是一家人,大老婆和小老婆住对门,吃饭一起吃,逛街一起逛,只不过晚上,男人没有分身术,只能陪一个睡;某镇的两个有钱人,因为口角生怨,于是其中的某个和《七根孔雀羽毛》中“丁盛”的遭遇如出一辙;几十万人口的县城,去年一年就添置了二千四百多辆轿车,单位离家300米,也要开车上班……我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为何人人如此忙碌、焦躁。他们如是热爱物质、热爱机械、热爱权色,他们从来不会停下脚步,等一等自己的灵魂……后来我认识了一个信基督的小伙子,我想,有信仰的人,也许会有丰盛的灵魂吧。可他脸色苍白,眼神迷茫,喝酒聊天时,只是用双胆怯的眼睛逡巡着我们,几次交往后我们发现,尽管他有所谓的信仰,可他的内心并不强大……”“中国今天面临的根本危机是道德危机,这个危机不是表现在信仰与道德的真空,而是表现为信仰与道德变成了精神的废墟。”在消费意识形态与市场经济政策的合谋作用下,现代人在欣喜物质充盈的同时也渐渐沦为了权力、资本、色欲的奴隶,“再也无法欣赏到自然的美”了。
《七根孔雀羽毛》无疑在警告人们赫胥黎所预言的“美丽新世界”正在悄然且迅速地变为现实。现代消费社会中的人们所面临的轻与重、灵与肉的痛苦抉择都通过作者巧妙的反讽式话语方式给以无情揭示。
首先,小说题目《七根孔雀羽毛》本身就构成了巨大的反讽/隐喻,文中不时出现的七根孔雀羽毛的意象,无疑象征着主人公宗建明那些尘封在心底的理想(责任/纯真的爱情/美好的回忆),然而他却迟迟不肯行动,甚至连说出自己理想的勇气都没有,即使在小说最后李红(宗建明情人)去监狱看望他再次问起那七根孔雀羽毛时,他依然不敢正视自己的内心理想,只是说:“这些破羽毛狗屁秘密没有。我早忘了是谁送我的了。要不就是我自己逛动物园时花钱买的?谁知道呢?况且,有些秘密,除了它是秘密外,什么也不是。”心存理想却又惰于行动,不敢正视理想的心灵悖论不也正是每个现代人所面临的精神困境吗?
其次,小说主人公宗建明也是一个反讽性综合体,他身为一个已婚男人却偏爱收看少儿频道的《海绵宝宝》(其在反映现代人的“精神退化症”的同时也揭示出现代生活本身也如同动画片一样荒诞不经);自己一事无成,整天浑浑噩噩,却自诩是天才,长得像普京;生活淫靡混乱,狼狈不堪却视李红的女儿丁丁是一坨狗屎,还自命不凡地教育她“别想得到得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否则以后会很难堪”;自己不敢直面内心理想却对李浩宇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冷嘲热讽。最具讽刺性的是,宗建明将从事非法活动得来的三十万元钱藏在存放七根孔雀羽毛的皮箱里时,竟把自己最珍爱的孔雀羽毛落在了书桌上,这无疑揭示了宗建明物质得以满足的惨痛代价便是对精神信仰的抛弃。
此外,构成反讽的意象还有很多,如“桃源县”这样充满诗性的名字与县里人们的庸俗、势利、糜烂、腐败的生存状态;县城中“富人”的物质膨胀、色欲泛滥与文化修养的浅薄、价值观的混乱;以及宗建明的“选择性失忆症”、丁丁的“自闭症”、李浩宇的“宇宙恐惧症”等等。
宗建明与前妻曹文娟、情人李红之间的关系不禁会使人联想到米兰·昆德拉哲学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的男女主人公(托马斯、萨比娜、特蕾莎)。宗建明在前妻与情人之间的游移、徘徊也在隐喻着现代人所共同需要面对的困境,即灵与肉、轻与重、精神与物质、责任与放纵的抉择。而宗建明的儿子小虎与那条流浪狗或许可以看做“卡列宁的微笑”,成为小说中唯一亮色和温暖,似乎也只有小虎和流浪狗还能唤起宗建明内心里仅有的一丝责任感与同情心,从而证明自己曾经拥有“七根孔雀羽毛”。
作者张楚对待小说中的人物始终保持冷眼旁观的姿态,既没有激烈的抨击也没有感伤的同情,这不仅体现了作者鲜明的写实主义艺术追求,反映他反对纯情、拒绝升华、躲避崇高的创作理念,同时作家也在试图叩问:面对精神荒芜、信仰坍塌、价值失范的酷厉现实,是人们主动地抛弃了理想与道德呢,还是残酷的现实逼迫人们亲手杀死了自己心中的理想与道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