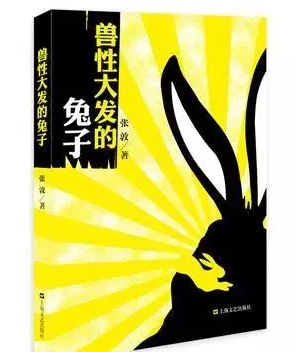
《兽性大发的兔子》,张敦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3
“80后”作家的出道方式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新概念”+“网红”模式,即写作者先以“新概念”作文大赛展露头角,随后经过网络文化产业的推波助澜而迅速赢得市场与版税;另一种是“高校+作协”模式,即写作者经过高校作家班的“孵化”和训练,并借助作协系统的引荐与推介,而一跃成为各大传统文学期刊竞相追捧的新宠。与上述两种“闪亮登场”方式不同,河北青年作家张敦的出道则显得既平静而又艰辛。他没有惊人的天赋,没有值得炫耀的学历,也并未接受过系统的专业培训,但长期在社会最底层的摸爬滚打、横冲直撞,却为他积淀了极为真切而深厚的生存经验与生命体验,从而,使得他的小说相较于其他同龄作家而言更具“野性”。这里的“野性”蕴含两层含义:一是张敦小说没有“洁癖”。俗词俚句、污言秽语皆可入文。他很早有意识地摆脱了“文艺小清新”的写作风格,因而从他的小说中很难发现青年作家常见的书卷气和文艺腔;二是张敦小说呈现出一种未经驯化的“纯天然状态”:叙述单刀直入,结构不事雕琢,人物对白简洁干脆,情感关系混沌暧昧,散发出一股野蛮生长的原始冲动。阅读张敦的小说就像是在欣赏一首令人热血喷张的地下摇滚乐。
《兽性大发的兔子》就是这样一部具有典型“摇滚范儿”的作品集。这些小说都属于有感而发、不平之鸣。生活的窘迫以及精神的逼仄培植张敦敏感的艺术神经,同时也催生出他强烈的表达欲望,某种意义上讲,他的小说都是面向内心的自我告白、自我慰藉和自我宣泄。颓废、迷惘、孤独、绝望、愤怒、叛逆、狂野……这些冷峻、粗粝的词组构成其小说的主旋律。该书所收录的诸多小说在表达主题与精神气质上都与中国摇滚乐存在着某种家族相似性,以至于我不得不妄加揣测:张敦有可能是摇滚乐的忠实拥趸。比如小说《小丽的幸福花园》中“我”对幸福花园的执着找寻,让我不由得联想到窦唯在《高级动物》中反复吟唱那句副歌“幸福在那里啊”;小说《夜路》所传达的个人在大都市中的迷失感,让我瞬间想到了汪峰的《北京,北京》;小说《烂肉》中两个孤独生命的形影相吊,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还有小说《去街上抢点钱》《知足常乐的小姐》似乎分别对应着崔健的《快让我在这雪地里撒点野》和《花房姑娘》……
张敦小说的“摇滚”特质首先表现为“堕落与颓废”。他笔下的主人公都是一群正在/已经丧失行动能力的“多余人”,他们出身卑微、穷困潦倒、沉默寡言、性情乖张、百无聊赖、耽于幻想,就像是漂浮于城市海洋中的微生物一样自生自灭,无人为津。吃饭、睡觉、性爱,这些马斯洛意义上的“低级生理需求”,对于他们而言都成为了无力应对的难题。强烈的失败感与幻灭感导致张敦笔下的人物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自暴自弃、肆意妄为。对此表现最为深刻的当属《小丽,好久不见》。小说采用一种极端化的表现方式,通过“约泡”与“憋尿”的先后失败,隐晦地呈现出社会底层青年群体在生理与情感上所面临的双重困境。小丽对“我”的冷淡与提防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我”情感需求的受挫,而那股突如其来的尿意,以及最后时刻有失斯文的“开闸泄洪”,则更加凸显出“我”在生理需求的一败涂地。“堕落”、“颓废”在张敦小说中既是一种现实,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态度——宁可选择自我放纵,也不愿接受既定意识形态的规约与驯化;即便失意落迫,也不愿去追寻那些世俗成功学意义上的“自我价值实现”。

张敦,原名张东旭,生于1982年,河北枣强人,写小说,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兽性大发的兔子》,现为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
张敦小说的“摇滚”特质还表现为“愤怒与反抗”。读张敦的小说,能够从中感受到一股戾气、一腔怒火。长期来自生理与心理上的双重压抑,使得张敦笔下的人物都或多或少都患有迫害妄想症。如《带我去隔壁》中青年房客对房东老太的杀害;《食鬼猫》中人物对杀戮与死亡的强烈渴望;《烂肉》中两个天涯沦落人的自虐与施虐等等。不管自杀还是被杀,在张敦小说中都隐含着一种心理诉求,即对是生存现状以及既定现实秩序的极端不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毽客》和《暗园》,前者采用真实与虚构互嵌互渗的方式,通过一起惨绝人寰的校园杀人事件,强烈了表达出一位当代“侠客”(毽客谐音同“剑客”,窃以为,这里带有作者自诩之意)的摇滚最强音: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后者则是以中学往事为底本,凭借大胆、越轨的想象,抒发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人生信仰: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与那些(我个人认为是)真正的摇滚乐一样,张敦的小说着力表现的依旧是那个关于“眼前苟且”与“诗和远方”之间的思想悖论:他笔下的主人公不屑于眼前的苟且,但又对“远方寻诗”的行径深表怀疑。然而于此同时,他们还兼具着明知前方是“坟”,却依旧义无反顾奔向远方的勇气与胆魄。从这个意义上讲,张敦的小说多少带有一些存在主义的意味。这在其小说的空间设置上表现尤为明显。张敦的小说往往存在着一组反差极大的空间结构,如出租屋与戈壁沙漠(《烂肉》)、公司走廊与城市街头(《夜路》)、小区岗亭与野外坟场(《食鬼猫》)等等,前者狭窄逼仄,代表着当下的物质生活的困窘与匮乏;后者空旷混沌,意味着未来前景的昏暗与未知。在这种截然对立的空间设置下,作者切身的囚困之感被和盘托出。一如小说《兔子》中“我”的感慨那样:“当他们说炒股这两个字的时候,总让我想起‘被玩弄于股掌之间’这句话”。对于现实荒诞感的深刻体认,使得张敦笔下的人物沦为一群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他们厌弃故乡,因为那里赐予他们的只有贫穷与丑陋,然而,他们又无法真正融入他乡,因为这里没有为其预留任何生存空间。面对“被囚”与“自囚”的双重困境,他们只能无可奈何地从一个“远方”走向另一个“远方”。正如张敦在后记中所言:“我不热爱故乡,却深受其影响;我也无法融入城市,因为那里没有存放我理想的地方。生活就是一场无休止的宰杀。我既是一只急于啃食窝边青草的兔子,也是一只渴望进入笼中享受衣食无忧生活的兔子。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想要什么,我只是活下去,在气若游丝的写作中自得其乐罢了。”
张敦这种“兔子”式的写作一定程度上也为他带来了一系列视野盲点,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过分倚重第一人称叙事(即便有些小说采用了第三人称叙事,但“他”也带有明显“我”的印记),使其小说带有极强的主观情绪和个人化色彩。由于张敦多以底层视角来观照社会与现实,强烈的个人主观情绪会使其笔下人物呈现鲜明的二元对立关系——作者往往对那些“被侮辱被损害者”报以“理解之同情”,但对于底层之上的“立法者”与“执法者”缺少必要的“同情之理解”。从而,导致一些人物的形象过于简单化、脸谱化、概念化。
第二,空间结构过于封闭,叙事格局过于狭小,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张敦的发挥。对于大多数“80后”作家而言,张敦的生活经历是独特而丰富的,然而,对于张敦自己而言,这种单向度的底层生活经验反而是一种“贫瘠”的表现。由于他对其他社会阶层的生活没有切身的体验,致使他的小说视野始终打不开。在这本《兽性大发的兔子》中已经隐约可以感受到张敦的写作存在着自我重复的危险。
第三,从某种程度上讲,张敦的小说还存在着先天性营养不良的症状。这种症状一方面表现在作者叙事视野上,但更多体现在作者的写作野心上。张敦习惯于“在自己气若游丝的写作中自得其乐”,这并无可厚非,但这种写作方式从某个侧面却暴露出他对更为宽广、多元、驳杂的叙事缺乏写作自信。对此,我们可以拿张敦与格非的小说做一下对比。他们都热衷于表现那些正在/已经丧失行动能力的社会边缘人的生存现状与精神生态。但是张敦的写作更多只是借助人物身上的一点微光去窥探现实生活中的某个角落;而格非的写作却总能够凭借人物身上的微光去点燃更大的火焰,从而展现出现实生活中的更多角落。
当然,以如此严苛的方式来指摘张敦的小说创作多少有些吹毛求疵,但我的初衷在于提醒和鼓励张敦放开手脚,大胆尝试不同风格、不同类型的写作。毕竟,从他目前的创作来看,已经具备了驾驭更具挑战性写作类型的实力。假以时日,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张敦会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对此,我们将拭目以待。

赵振杰,80后,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从事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研究和评论。曾获《人民文学》“近作短评”金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