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从手工匠之子到思想“巨人”
http://www.newdu.com 2024/06/30 09:06:45 广州日报 佚名 参加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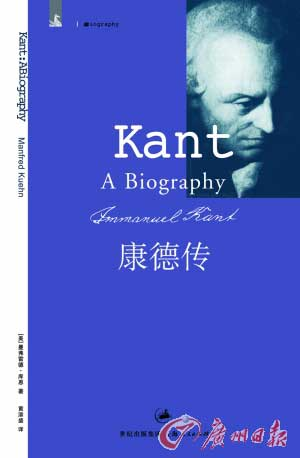 康德传(美)曼弗雷德·库恩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二○○八年四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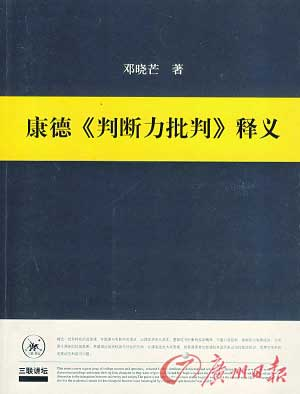 康德《判断力批判》释义 邓晓芒 著 哥尼斯堡是康德的家乡,但是哥尼斯堡却没有一条以康德命名的街道,听起来此事似乎非常奇怪。伊曼纽尔·康德,且不说他是哥尼斯堡和德国人的骄傲,全世界都得感激他。没有康德,启蒙运动将缺失其中撑起全局的一笔,“自由”概念的血肉将不完满,后世现实的政治考量都会失掉一种值得作为理想去追求的目标。在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之间屹立于史册的那个一米七五的小个子,小手工艺匠人的儿子,他阐述的道理,他写下的书,毫无疑问值得每个民族千秋万代都为之铭记。 然而康德的家乡已经不属于德国人,它现在已是俄罗斯的领土。1945年,第三帝国在战败之际失掉了这座波罗的海海滨城市,随后它被俄国化,名字也改为加里宁格勒。曼弗雷德·库恩教授在他的《康德传》中说,康德出生的那个时代,哥尼斯堡的社会环境提供了“从道德的角度而言最佳的教育背景”,这座城市作为东普鲁士首都,由于临近俄国和波兰,其国际化程度很高,但又在那个德意志民族刚开始形成的时代代表了一个超越其上的“普鲁士”概念;城市里有许多来自波罗的海地区的居民,有立陶宛人、荷兰人、法国受迫害的胡格诺派教徒。由于这些原因,康德认为它“可以被视为拓展对人的见识与世界视野的好地方,虽不远行亦能知天下事。”而他本人随同家庭成员住在城市的近郊,又是一个可供他大开眼界的交叉地带。 今天的加里宁格勒还会有多少居民经常想起她那伟大的儿子并为之自豪呢?半个多世纪前的一段国仇家恨或许已退出了年轻人的感情世界,但变化了的城市已经少去了许多本来铭于土石之间的历史记忆。二战期间,哥尼斯堡遭到了狂轰滥炸,许多地方被夷为平地,无辜的德国平民被迫为纳粹德国在别国造的孽偿债,死的死逃的逃,活下来的人中还有相当一部分被流放。“加里宁格勒”是以苏联前总理米哈伊尔·加里宁的名字命名的,此后进入了新一轮的民族混居时期,大批俄国和斯拉夫居民迁入并生根。在此后几十年改建的过程中,哥尼斯堡有着七百年历史的美丽的城堡也消失了,如果康德的在天之灵回到这里,恐怕只能认出自己的墓地。 历史就是这样充满吊桅。曼弗雷德·库恩的书中有一章写到1758~1762年间的哥尼斯堡,那时,作为七年战争的后果之一,初生不久的东普鲁士不得不眼睁睁看着它被俄国人夺走:1758年1月22日,俄罗斯将领费莫尔踏进普鲁士元帅刚刚离开不久的城堡,随后俄国总督也走马上任。俄国文化的到来,改变了这个虽然处于迅速成长期,但封建禁锢依然强硬、专制力量实力雄厚的城市。这段时期见证了文化交融的巨大成果,也记载下康德一生中最风姿绰约的一段岁月。年过而立的他,思想日深,襟抱渐大,他第二次向哥尼斯堡大学申请哲学教授之职。尽管这次申请又没有成功,但是库恩讲述了康德从俄国人那里获得的毕生之益:他是那么喜欢清新空气,社交生活丰富了,敬虔派宗教统治时期死板的社会风气打破了,偏见和旧俗逐渐解体。康德对一切“美好有礼”的事物的浓厚兴趣,喜欢他们的贵族与平民可以联欢的平等,喜欢他们对异民族精神财富的宽容接纳:有钱但尊重文化的贵族多了,法国饮食进来了,世俗化的生活方式得到了民众的拥护。 这段岁月深深地留在了康德这辈子最美好的记忆中。库恩引用了时人对他的评价:“康德的眼睛像是穹苍中的以太做的,心灵深处的凝视,仿佛穿透了薄云,温润地闪烁发光。我无法形容康德坐在我对面时,低垂的眼睛突然抬起来与我四目交视的片刻,他的神情多么使我着迷。我总觉得好像透过这个蓝色的以太之火瞥见了密涅瓦最神圣的内在。”只有一位未来的思想巨人才配得上这样的描述。 18世纪的俄国文化塑造了康德的人格,可惜冷战时期两大阵营一分,没什么人还记得那段美好的友谊,只是加里宁格勒大学辟出几个房间,做成了康德博物馆。冷战之后的加里宁格勒又重新对非俄人民开放,上了年纪的旅游者也开始到这里故地重游,但是战争之前和平年代的记忆无可挽回地要在德国人中慢慢消逝。年轻一代也遗忘了它,尽管在那里出生并长眠的伟人的名字依然如雷贯耳。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美好的政治、社会、人与道德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康德毕生都在追问这些,他那赤诚的、深邃的智慧,令多少后人从“康德会怎么想?”出发来思考眼前的伦理问题。然而伟人的家乡20世纪以来的历史丝毫经不起他的正义理论的度量,或许可以说,这是欧洲对康德的背叛。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史景迁私人记忆里的李约瑟
- 下一篇:婚姻从哪里来,向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