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比尔,或两个国度》:“盛世哀歌”
http://www.newdu.com 2025/11/08 07:11:21 澎湃新闻 杨靖 参加讨论
关键词:《西比尔,或两个国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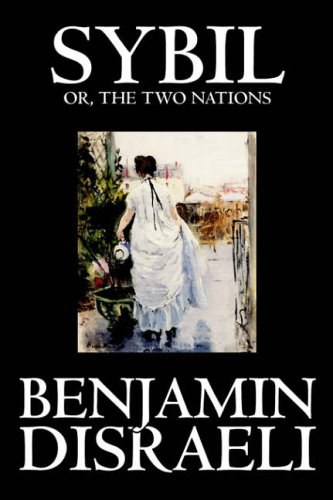 1845年,英国小说家本杰明·迪斯雷利(1804-1881)“青年英格兰”三部曲的第二部《西比尔:或两个国度》(Sybil, or the Two Nations)问世,风靡一时。小说描绘了十九世纪中期英格兰社会的真实状况,被誉为维多利亚时代最负盛名的“政治小说”之一。巧合的是,恩格斯在同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也认为随着贫富差距加大,英国事实上已分裂为“两个国度”——“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另一种宗教和政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彼此是这样地不同,就好像他们是属于不同的种族一样”。恩格斯本人显然注意到了他和迪斯雷利的相似之处——他在1892年德文版中加入一则注解:“大家知道,狄思累利在他的长篇小说《神巫,或两种民族》中,几乎和我同时说出了大工业把英国人分为两种不同的民族的见解。” 维多利亚女王治下的大英帝国外表光鲜,有太平盛世之美誉。事实上,早在迪斯雷利开始小说创作之前,英国就享有“世界工厂”的称号:它的工业生产总值约占全球三分之一,钢铁和煤炭产量占世界半数;此外,英国商船纵横全球,繁盛的殖民地“贸易”将世界各地财富源源不断运回母国,伦敦由此也成为世界唯一的金融中心;它的国土面积超过三千三百万平方公里,是当之无愧的“日不落帝国”。毫无疑问,英国率先发动的工业革命为本国经济注入了巨大活力,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但与此同时,这一场变革也深刻改变了英国的社会结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扩大了贫富差距,使得英国社会最终沦为贫富之间存在不可逾越鸿沟的“两个国度”。 日后曾两度出任英国首相(1868﹑1874-1880)的迪斯雷利政治嗅觉异常灵敏。1830年代后期宪章运动兴起之初,他便满怀忧虑,担心这场运动将会动摇英国君主制的根基。根据传记作家的看法,迪斯雷利选择以小说而非政论文形式探讨这一社会问题,乃是因为这是普通民众最喜闻乐见的方式,且影响深远——二十世纪初梁任公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倡言“欲新政治,必新小说”很大程度上便受此启发。正如小说副标题“两个国度”所示,《西比尔》旨在揭露“饥饿的四十年代”造成英国社会矛盾激化,一场暴力革命已迫在眉睫。基于议会社会调查委员会蓝皮书(Parliamentary Blue Books),加上作者本人在北方制造业城镇考察时的亲历亲见,迪斯雷利以1840年代欧洲革命和宪章运动为背景,着力描绘工人阶级、女性和童工等弱势群体所遭受的压迫和剥削(包括但不限于低薪、恶劣的住房和工作条件),以及工业城镇的肮脏环境和悲惨景象,并将这一英国社会病归结为英国社会整体的道德堕落,尤其是统治阶级的贪婪自私和底层民众的麻木不仁。 《西比尔》主要讲述贵族青年查尔斯·埃格雷蒙特(Charles Egremont)社会良知逐渐觉醒的故事。故事的女主西比尔是工人激进分子沃尔特·杰拉德(Walter Gerard)之女,深受工人阶级爱戴;男主外出进行社会调查,途经一座修道院废墟,与杰拉德父女邂逅,随后又结识宪章运动理论家斯蒂芬·莫利(Stephen Morley)。男主的哥哥马尼勋爵(Lord Marney)残酷压榨农场工人,激起劳工阶层强烈反抗——他们发布“人民宪章”,要求捍卫自身权利,消除社会不公。当宪章运动由和平请愿升级为暴力革命后,双方斗争趋于白热化。起义人群奋力攻打莫布雷(Mowbray)城堡,杰拉德试图阻止暴力升级,反被领兵前来解围的马尼伯爵杀害,马尼伯爵则被愤怒的群众用石块砸死。攻入城堡的暴民庆祝革命胜利,喝得大醉酩酊,随后点燃整座城堡,与之同归于尽。埃格雷蒙特在危急关头拯救了西比尔;婚后,他放弃贵族头衔,二人安享平静生活。小说的这一结局意味深长:原本分属“两个国度”的青年男女结为连理,合二为一,预示着分裂的英格兰最终走向和谐与安宁。这是迪斯雷利本人的政治抱负和社会理想——日后他也将余生奉献给了这一高远的理想。 小说最精彩之处是开篇不久埃格雷蒙特与斯蒂芬·莫利的一段对话:前者不无自豪地宣称“我们女王陛下统治的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度”,后者则反唇相讥,“哪一个国度?要知道,她统治的可是两个国度……两个泾渭分明、相互隔膜的国度。他们的习惯不同,想法各异,感受有差,对彼此的无知简直像不同地区的住民,甚至是来自不同星球的访客。他们养育各自的儿女,享用各自的食物,遵从各自的礼仪,并且遵循各自的法律”。——这也是维多利亚时代早期英格兰社会的真实面貌。 小说一开始,埃格雷蒙特便对小镇马尼做出了总体评判:“自诺曼征服后,现如今英国的农奴制体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完备,那些劳动者无力选择或更换他们的主人,仿佛他们是生而为奴”——在这位青年贵族看来,所谓“机械时代”(The Mechanical Age,卡莱尔语)的产业工人,其处境尚不及中世纪封建庄园的农奴。镇上根本没有任何公共建筑,没有教堂和市政厅,更没有剧院和图书馆,只有位于小镇主街道上一些破旧的小门店,肮脏而狭窄。这里充斥简陋而喧闹的作坊与工场,“锤子和锉刀的声音从未停歇,令人作呕的水沟、成堆的肥料和积水池的污秽,是麻风病和瘟疫的温床;这里散发的恶气足以污染整个王国,使得整个国家笼罩在热病和瘟疫之中”。 据埃格雷蒙特观察,小镇马尼不仅缺乏公共设施,连最基本的生活设施也得不到保障,个人住房条件尤为恶劣:“这些廉租房破烂不堪,通常最多只有两间屋,而无论一家有多少人,都不分男女老少,挤在一间屋里睡觉。”穷人的生存环境不仅拥挤逼仄,而且有碍健康,毫无人性化可言:“墙面不停淌水,屋顶破旧透光,即便在严冬也无壁炉取暖。贤良伟大的母亲忍受着分娩带来的神圣剧痛,为我们冷漠麻木的文明社会送来了新的牺牲品……比起分娩时的痛苦,她不得不承受三代人的注目,令人无比难堪;而她即将出世的孩子的父亲,正蜷缩在陋室的另一隅,饱受斑疹伤寒的折磨;或许正因他终日受困在这污秽不堪的住处,才使得疾病入侵血管,而他刚出世的孩子则已注定将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这些廉租房的墙上没有门窗——既不能遮风避雨,也无法通风采光;潮湿腐臭的茅草屋顶散发出一股植物腐败后的瘴气,“夏日里穷人若是想让微风换换屋内的浊气,敞开屋门只能闻到户外粪堆散发出来的各种臭味”。这些房屋地势低洼——通常低于门外的路面,而屋内全是未经铺砌的毛坯地面,由此导致屋内常年潮湿,一下雨房屋就会淹没,全家人只能手忙脚乱,“将门从铰链上卸下,以便给婴儿腾出容身之地”。 与恶劣的生活条件相比,他们的工作环境更为糟糕:迫于生活压力,连家中的妇孺也要外出劳动,“在矿工的队伍里——唉!有男有女,他们的穿着和言谈举止,让人根本无从分辨;而其中有一些将会是——或已经是——英格兰人的母亲!……一个小女孩,在黑暗、险峻又泥泞的地下隧道里,手脚不停,拖拽一筐又一筐煤炭,如此度过每日的十二小时,甚至十六小时:而这一切,似乎并未引起废奴协会的注意”。 在此,迪斯雷利满腔悲愤地指控英国政府:竟然任凭儿童在地下矿井这人间炼狱中慢慢长大。穷凶极恶的工场主采用了“最新”的发明——只有在煤车通过的时候,监工才会打开矿道风门,其余时候,这扇门始终紧闭,而“矿井的安全和井下工人的性命皆系于此”。根据工人领袖杰拉德的统计:当地井下矿工的平均寿命是十七岁;在新生儿中,五岁前夭折的超过半数——在和平盛世,这样的数据可谓触目惊心。瘟疫是贫民早夭的原因之一,但显然并非最主要的原因,正如杰拉德所说:“过去谁都有可能感染瘟疫。现在英格兰的瘟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只有穷人感染瘟疫……工匠和农民家中每年患斑疹伤寒的人数相当于整个威斯特摩兰郡的人口。” 迪斯雷利将造成人民苦难的根源主要归咎于统治阶级的自私贪婪——他们“鼓吹建立仅以财富和辛劳组成的乌托邦,并在哲学词藻的掩盖下压榨民众,攫取财物,积累资本,这就是过去十二年间历届英国政府所拼命追求的一切”。不仅如此,他们热衷于捞取政治资本(选票)并以之作交易,而对民生之多艰毫不在意,正如同时代小说家狄更斯笔下人物莱斯特·德洛克爵士——“以候选人的身份发表演说,就像一笔可观的订单立即执行”,而把另外两个属于他的议会席位当作“不太重要的零售订单,寄发给下面的人”。终其一生,迪斯雷利对“英式”民主制深恶痛绝,正是因为他早已洞悉其奸诈和虚伪——这也是他后来成为英国君主制坚定捍卫者的重要原因。 但与此同时,迪斯雷利对底层民众的冷漠愚昧更为痛心疾首——为参加热闹非凡的赛马会,赌民前一晚就早早来到赛马会馆,他们“一想到第二天的比赛就心跳不已,同时又为如何赢得赌注而绞尽脑汁”。像富商和议员一样,他们急匆匆地赶赴致富之路,幻想一夜暴富——在这一点上,无论是恶意延长工人劳动时间的小作坊主,还是变着戏法压低工资的马尼勋爵(他每周只付给农场工人八先令,理由是:“工人工资越高就越会变坏;他们只会把钱在啤酒店里挥霍掉”),他们的精神气质(即市侩气)可谓毫无二致。在迪斯雷利看来,这是英国长期片面奉行功利主义学说造成的必然后果:边沁、密尔等人鼓吹的功利主义既是英国社会的强心针,也是安慰剂——结果使得英国成为充满中庸和市侩习气的“小店主国家”。 赌博和炒股是当时社会流行的时尚。此外,不知从何时起,“放债欠债也成了国民习惯”;更糟的是,“赊购成了所有交易的主宰,而不是偶尔为之的辅助手段”,由此则助长了“不诚实之风”——在信贷原则的支配下,英国的“对外贸易无异于赌博,国内贸易则呈现出恶性竞争”。这一恶性竞争的结果是社会道德整体滑坡——超长的工时,微薄的酬劳,有碍健康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居高不下的新生儿死亡率,等等,种种因素的合力最终加剧了这种人性的退化和社会的分裂。 这是维多利亚盛世的阴暗面,也是卡莱尔所谓“英格兰现状问题”(The Question of the Condition of England)的真实写照。据官方统计数据,在《西比尔》发表三年前,即1842年,英国一千六百万人口中有一百万处于贫困线以下,依赖政府救济。利兹十五万人口中有两万人平均每周生活费用只有约十便士。在威尔士,每十一人中便有一名乞丐。诗人托马斯·胡德在《衬衫之歌》中所谓“面包昂贵,血肉低廉”显然并非夸大其辞。这一现状引发了大规模的宪章运动——恩格斯预言,只要“稍加推动”即能“引发雪崩”;而桂冠诗人丁尼生则仿佛看见“一个饥饿的民族缓缓走来,/犹如雄狮匍匐逼近……”。针对这一现状,卡莱尔本人在《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 1843)一书中提出了严厉的社会批判:“英国的状况——公正地说,是世界有史以来最危险也是最奇特的状况之一。英国充满各种各样的财富,劳动人民创造的成果绰绰有余,而且到处都非常充足……可是在过剩的充盈中,人民却死于饥饿。” 从某种意义上说,迪斯雷利的《西比尔》堪称是卡莱尔思想学说的文学呈现。在《宪章运动》(1839)一文中,卡莱尔写道:“当前工人阶级的状况已释放出不详的征兆”——具体而言,这是一种因工人大众困窘的生活状况、上层的漠然态度和社会整体信仰缺失所造成的民怨的聚集。“两个国度”中贫穷一方的生活状况不仅会在物质和生理层面造成恶果,更会对英国整体社会道德伦理构成威胁。借助于形象化的表现手法,迪斯雷利深刻地揭示出“英格兰的现状问题”不仅是经济层面的贫困问题,更是精神层面的道德危机——随着“社会传统建制的崩坏,一种具有毁灭力量的危险情绪正在酝酿”。 深受卡莱尔学说影响的《西比尔》“对维多利亚时代社会黑暗面的揭露,尤其是对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描写比狄更斯的《荒凉山庄》还要大胆、深刻和全面”。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它确实影响了一大批同时代(及稍后)的文学作品,如查理·金斯莱(Charles Kingsley)的《酵母》(Yeast,1848)和《奥尔顿·洛克》(1850),盖斯凯尔夫人的《玛丽·巴顿》(1850)和《南方与北方》(1855),以及狄更斯的《艰难时世》(1854)等,可谓“开英国政治小说之先河”。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西比尔》这一曲“盛世哀歌”,迪斯雷利一方面对劳动阶层的苦难深表同情,另一方面对宪章运动也提出质疑,认为宪章派领袖空有理论,但缺乏实践才能,根本无力领导人民取得社会改进;同时他也断言,“人民并不强大;人民永远不可能强大。他们维护自我的努力只会以苦难和混乱告终”。当然,纵观全书,迪斯雷利的矛头主要还是指向当时颟顸无能的统治阶级,正如他在小说结尾处所言:英国社会的现状是一个谜,“在这个巨大的谜团中,所有的思想和事物都以别样的方式和名称呈现,与它们实际的特质和作风截然相反。寡头政治号称自由;圣公会被奉为国教;主权不过虚有其表,滥用在毫无权利可言的地方;他们(统治者)自命为人民公仆,却掌握着绝对权力”。 1852年,迪斯雷利受命担任德比勋爵内阁的财政大臣,由此开启锐意进取的政治生涯,成为维多利亚时代与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齐名的政治领袖。在财长任内,当他发现皇家海军支出远超预算——甚至超过全民医疗费用总和时,迪斯雷利立即下令改弦更张。及至他两度出任首相期间(女王在他首次当选后曾由衷地感叹:“迪斯雷利先生成为新首相——这对于一个在人民中崛起的人来说,多么值得骄傲!”),更大力推进和完善法制建设,以此推动各项政治改革:比如,上任之初,他便设法降低麦芽和茶叶税,减轻劳工阶层负担;随后,《手工业者及劳工房屋法令》旨在通过提供低息贷款帮助劳工解决住房问题;《1875年公共健康法令》将全国公共卫生标准提升到现代水平;《食物及药物销售法令》和《教育法令》致力于解决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食品安全和公共教育问题。此外,迪斯雷利在任内还主持通过新《工厂法》保护劳工权益,通过《雇主及工人法令》保护工人有权在民事法庭起诉违约雇主,并通过一系列法令允许工人组织和平罢工,由此赢得工人阶级的广泛支持和拥戴。到他1880年卸任之时,国内一致评价:本届政府“在此五年间为工人阶级所做的一切,超过过去五十年的总和”。 当然,论及迪斯雷利政治生涯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功绩,首推1867年由他本人主导的《改革法案》顺利获得通过——该法案扩大了普通民众的选举权,阻止了可能发生的激进革命,并成功捍卫了英国君主立宪制。被迪斯雷利尊称为“仙后”(Sybil)的维多利亚女王由此满怀感激,赐予他贵族封号,并在他病逝(1881年)后亲临墓地悼唁,可谓哀荣备至。小说家伍尔夫之父、著名文学批评家莱斯利·斯蒂芬(Sir Leslie Stephen)曾经感叹,“迪斯雷利从政实在是英国文学的一大损失”——但这只是这位文学家的一家之言。上至维多利亚女王,下至英国平民百姓,恐怕未必作如是观。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马丁内斯:一切可能的序列
- 下一篇:萨莉·鲁尼旋风:一场感官和话语的喧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