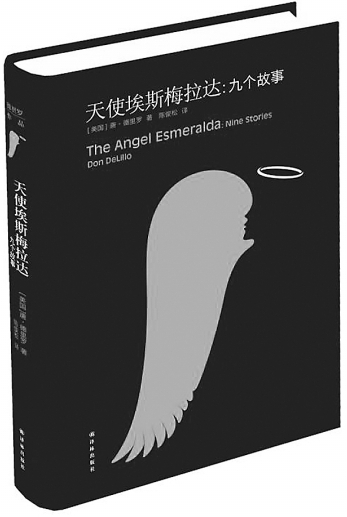
《天使埃斯梅拉达》 (美)唐·德里罗 著 译林出版社出版
阅读美国作家唐·德里罗的作品,感觉像在剥洋葱。德里罗的写作风格始终是为作品的主题服务的。也正因其复杂的艺术形式,才让我们通过《名字》、《地下世界》等一系列巨制,一窥其笔下如万花筒般光怪陆离的当代世界,以及作者对政治、文化、科技、艺术,尤其是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解构和思考。
《天使埃斯梅拉达》是德里罗迄今为止唯一一部短篇小说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短篇就很好对付,即使德里罗把他庞杂叙事中某些部分作为一个现成的切片提供给你,你仍然要像剥洋葱那样,一步步地将阅读的手术刀探至故事、叙事风格及其形式的肌理,最后,解读与体悟作者的用心与寓意。
为了说明慢读出真知的道理,我们不妨从集子中的首篇《创世》来展开讨论。这篇小说在故事层面上,是一出旅行途中男子背着妻子(或女友)跟别的女人偷情的狗血剧,但故事的风格,则是卡夫卡式的。德里罗将小说背景放置于加勒比海某岛国,异域的神秘情调混搭官僚主义的拖拉作风,让主人公在航班几度延误后,荒诞地享受起不知魏晋,也不需要计划什么,更没有必要赶着去上班的桃源生活。从时光意识中逸脱而出的男人,视觉、味觉、听觉、触觉,都是异常敏锐和丰富的。德里罗“慢笔”的意义——从香艳女人爆出闪电和火花的头发丝,到如旗舰般在低空飞过的浮云——就在于凸显在此“真空”状态中,我们就好像回到了创世之初,或者我们自己就是个刚睁开眼睛的婴儿,鲜活地体会到世界原有的本色。换言之,我们身处的e时代,才是一个限制、堵塞乃至取消了人类感官认知的荒诞世界。
《天使埃斯梅拉达》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午夜》则是两篇超现实主义作品。不过,它们的超现实并非一眼就能看出来,而是从现实的细微处着手,慢慢展现其超现实意象的。比如《天使埃斯梅拉达》,德里罗将城市贫民窟、流浪汉、亡命徒及其他社会边缘人群集中一隅,变成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曼哈顿的一块“飞地”,目力所及处,尽是垃圾、废品、尸骨、疾病、暴力,以及意外的死亡。这个自成一体的飞地也成为叙事上一个自成一体的空间,德里罗让老修女埃德加在这个如世界末日一样的空间中踟蹰徘徊,表达对上帝、人世、罪愆和救赎的探索。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午夜》则制造了一个平行世界。主人公“我”和好友是大学生,课堂上,他们的理工教授只为上课而上课,对他而言,学生都是匆匆过客,“唯一重要的法则是思维的法则”,他甚至连学生的名字都叫不上来。而这两个学生,为了表示对教授的不屑,共同虚构了一个他们偶遇的穿兜帽大衣的男子的生活。但问题是,他们从来没有上前招呼过这个男子,更别说了解他的生活与心灵了。小说的重大时刻在于,两个学生听说教授正在“昼夜不停地看陀思妥耶夫斯基”。注意,陀思妥耶夫斯基可是一个其人其作都充满血肉和人情味、灵魂透出挣扎和呻吟的作家啊。原来,理工教授、两个大学生以及穿兜帽大衣的老年男子,都是隔绝了彼此的孤岛,他们渴望别人理解,又害怕被人理解,更害怕去理解别人。
反讽的是,这篇小说的美学价值正在于我们对他人的想象让一切处于混沌暧昧的状态。“我”拒绝进一步去了解狂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教授,并且阻止好友跟兜帽男子搭话,就是为了营造这种真假难辨的平行生活。或许,知道事情的真相不仅会让美学想象失去存在的依托,同时,光裸毕现的现实还会让人觉得难以忍受——可能,世上还有比孤独更可怕的事情。毕竟,想象一个人是逃难而来的阿尔巴尼亚人,对我们的神经来说,要容易得多。同样,《天使埃斯梅拉达》中的老修女宁可笃信天使显灵而不愿相信真相,因为,她“需要一个神迹来对抗”内心丛生的怀疑,让自己相信“飞地”就如上帝降下天火的索多玛和蛾摩拉一样,可以涤荡它的罪孽。否则,生活真是太可怕、太空虚、太没有意义了。
德里罗的“慢笔”充满了对“物”的细节性描写,如科幻小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的人性时刻》,多是太空、军事、物理学上的术语(或伪术语)。相较之下,对人的刻画反而模糊、疏离、淡漠。常常,我们甚至连主人公的名字都不知道,如《跑步的人》中的主人公,通篇都叫“跑步的人”。这样的写法,自然是暗示人深陷“物”世界的渊薮之中,且越来越居于客体化的角色定位。好在,德里罗通过他巧手编织的层层镜像,迫使我们调动起所有感官,于“物”的喧嚣间,聆听人性深处微弱的呐喊与喘息。也许,这个过程是迂曲、艰难和痛苦的。因为要理解人与人性,总是迂曲、艰难和痛苦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