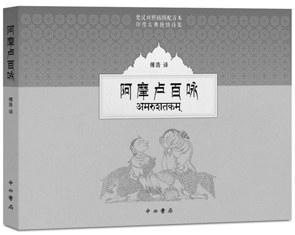
《阿摩卢百咏》(梵汉对照插图配音本),傅浩译,中西书局出版,45.00元
“艳情”是古典梵语诗歌最爱表现的情味。在印度古典文论“味论”中,“艳情味”居于“八味”之首。《阿摩卢百咏》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本身的主题即是艳情。整部诗集并没有连贯的情节,大部分内容为人物独白或对白。在读者看来,它们更像是“一幕幕戏剧小品场景”。
三年前,当得知傅浩先生有意翻译梵语艳情诗集《阿摩卢百咏》(以下简称《阿》)之后,我便开始期盼着这本书能早日面世。对这部作品寄予热望的原因在于,它在印度古典梵语诗歌史上一直矗立于艳情诗创作的顶峰。这部诗集大约成书于公元七或八世纪。作者据说是一位名叫阿摩卢的国王。传统中素有“诗人阿摩卢一颂诗抵百卷书”之说。其后,《阿》诗就不断出现在历代文论家和批评家的笔下,成为一把评判其它诗作的标尺。“前无古人,却开创风气,成为后世日趋下流的艳情诗之滥觞”(《阿》译者序)。“艳情”是古典梵语诗歌最爱表现的情味。在印度古典文论“味论”中,“艳情味”居于“八味”之首。七世纪的文论家檀丁把“艳情味”概括为“爱与许多形态结合”而产生的味——简而言之,即爱欲的种种表现。不过,在《阿》诗出现之前,诗歌中“艳情味”的体现往往要附着于一个有连续情节的故事,典型者莫过于古典梵诗大家迦梨陀娑的作品《云使》。《阿》诗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本身的主题即是艳情。整部诗集并没有连贯的情节,大部分内容为人物独白或对白。在读者看来,它们更像是“一幕幕戏剧小品场景”(《阿》译者序),所突出者既非人物也非情节,而在于弥漫其间的爱欲,即“艳情味”。
该书另有一个令人期待的原因在于,译者傅浩先生是一位诗歌翻译名家。据他在译后记中所说,他四十七岁才开始师从梵学大家黄宝生先生等研习梵文,历时三年半。按傅先生自己的说法,结束学业后承担这一梵诗研究和翻译课题属于“玩票”性质。然而,兴趣是一个人最好的老师。他把几十年所得的译诗心得运用到这门新掌握的语言上,对梵诗汉译提出了非常独到且极有说服力的观点。在附录的《梵语诗歌现代汉译形式初探》一文中,他提出,“诗是形式和内容结合得最为紧密的一种文体。……译诗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语言,一个是形式。语言最好用译者的当代语,形式则最好模拟原诗体式自创新体。”“梵语诗既然无一例外全都是格律诗,就理应以格律诗译出。”而汉语格律诗的和谐优美则有赖于每行中作为节奏单位的音组(顿)的数量要一致,其组合排列的格式(格)也要协调有序。傅先生对《阿》诗的翻译就严格遵循了他所提出的上述翻译原则。这里仅举书中第六十七首诗一例来略加说明。原诗格律是虎戏体,每行十九音,各行前半句占十二音,后半句占七音。而傅老师的译文为:“忽觉|如花|绽放,(六音三顿)/她远离|卧榻|而立。(七音三顿)/有情郎|嘴唇|颤抖,(七音三顿)/眼眉|挑动,偷偷(六音三顿)/求吻。窈窕女|满颊(七音三顿)/带笑,衣襟|遮面,(六音三顿)/摇着头,成串|耳饰(七音三顿)/随之|轻轻|晃悠。(六音三顿)”可见,这首译诗正是以有序的顿格安排模拟了原诗音数上的错落有致,实现了二者内在精神的呼应,令人过目难忘。
这本书的妙处不止于严谨的译文,其中几乎每首诗都还配有一至两幅相应的贝叶单色线描插图。它们出自十九世纪初叶的一位画师之手。这位画师“对诗意颇有创造性的理解,善于表现诗的戏剧性动态场景,故一颂诗往往不止配一帧图画,而是多帧情景连贯的画面,颇类我国的连环画。”(《阿》插图简介)甚至画师在完成诗中情境后,还会任由自己的想象力发挥,继续画出诗中未尽之意,把男贪女爱之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诗情画意”组合的效果,真是令人眼前一亮。
此外,这本书还有一个亮点,就是配有全文的梵语吟诵。梵语是一种表音文字。许多古老的文献,都是口口相传的。文字记录是相当晚近之事。故唯有吟诵,才最能体现梵诗音声之悠扬与格律之精妙。傅先生自学梵语以来,便对梵诗吟诵极为痴迷,勤学不缀。这次,他特地邀来自己的吟诵老师、尼泊尔梵语大学佛学系主任迦师那陀·袅跋匿教授,为本书吟诵了梵语全文,使汉语读者得以领略梵语诗歌不可译的音韵之美。
傅浩先生深谙梵诗的精华所在,才能有如此巧思,运用音、诗和画三种手段,立体表现出《阿摩卢百咏》这部梵语艳情诗歌史上扛鼎之作的面貌,在沉闷的梵学研究典籍和浮躁的印度文化通俗读物之间,为喜爱古印度文学和诗歌的读者打开了一条同时展示印度文化之绚丽多彩与深刻隽永的新通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