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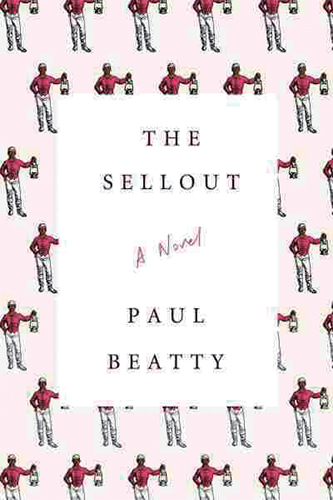
《叛徒》英文版
2016年,保罗·比蒂(Paul Beatty)成为布克奖历史上第一个获奖的美国作家,并不让文学界感到特别意外。事实上,《叛徒》不仅已经先期获得全美书评人奖这一美国国内的重要文学奖项,收获了许多国内外批评家的高度评价,英美主流批评界更将保罗·比蒂比作当代的马克·吐温、乔纳森·斯威夫特、拉尔夫·艾里森,将《叛徒》誉为世纪佳作。
《叛徒》大获肯定,首先与它对当代社会种族问题的揭示和作者辛辣老到的讽喻手法有关。小说开篇颇为精彩,既点明了主题也定下了反讽的基调:“说起来也许你都不信,我虽是黑人,却从没偷过任何东西。”简简单单一句话已经暴露了美国社会数百年来对黑人的歧视和刻板印象,当然,也内含了叙述者对这一刻板印象的挑战和解构。以下情节更是荒诞不经: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叙事者也就是故事的主人公,这位姓“我”(Me)的先生,这个被前女友称呼为“棒棒糖”(Bonbon)而被对手叫作“叛徒”(sellout)的黑人男子,正面临美国最高法院的审判,他的罪名是倡导在今天的美国重新恢复奴隶制,他甚至已经在自己居住的小镇上践行了奴隶制。他在公交车、医院、学校推行了种族隔离的制度,他还真的为自己“配备”了一名奴隶。小说的荒诞色彩浓厚,但叙述者一本正经的严肃态度加上缜密的思维却让读者不能简单地把他当作一位臆想症患者。他自己声称,推行奴隶制和种族隔离的初衷,是为了帮助自己的家乡——突然被从地图上抹去了踪迹的狄更斯(Dickens)小镇重获认可。
围绕在主人公身边的怪诞之事还有很多。接下来的叙述更像是在超现实主义的氛围下讲述了一个现实主义的故事:“我”出生在洛杉矶南郊的狄更斯小镇,这里是个黑人聚居的贫民区。父亲是颇有些名气的社会科学家,他是解放心理学的实践者,在他那一系列旨在研究受压迫者心理的实验中,“我”就是实验对象。为保证实验结果的准确性,父亲严格按照实验要求来教育和抚养我,“他并不爱我,我是在经过精确计算的适度的亲密环境中被养大的,担负着强烈的完成任务的使命感”。当众殴打、精神折磨、电击,这些都是父亲在“我”身上使用的试验手段。这样一个畸形的家庭形式也在父亲被警察误杀之后崩裂。“我”成为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以种植和出售大麻、柑橘、西瓜为生。
叙述者仍然不动声色,而读者却越来越感受到力透纸背的沉重感了。保罗·比蒂显然借用了荒诞的力量,通过将问题放大到夸张、变形的地步来让它显得滑稽可笑、不真实,让读者在识别出荒诞的同时触发对现实的思考。种族问题是美国社会的顽疾,却也是当代许多作家不太愿意触碰的话题。原因除了其本身的复杂性、政治敏感性之外,美国黑人群体的分化也多多少少冲淡了这一话题的严峻性。随着一些黑人跻身到美国社会阶层的顶部,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内成为领导者、决策者、标杆和楷模,一些言论认为美国当代种族问题已不再是凸显的社会问题,奥巴马当选美国第一任黑人总统,被当作美国摆脱了种族主义的历史性事件,标志着“后种族时代”的到来。然而叛徒中,保罗·比蒂戴着幽默和调侃的面具,撕开了后种族时代的温情面纱。 “我在 ‘后种族主义’时代低吟‘种族主义’颂歌”(“I’ve whispered ‘Racism’ in a post-racial world.”)。费蒂借 “我”之视角,展示了所谓后种族主义时代依然严峻的种族问题。美国现实社会中分区规划的制度造成了新的种族隔离,黑人贫民窟并未减少反而增加了,贫富差距并未消除反而扩大了,教育资源分布不均,黑人无法真正获得平等教育权利,警察针对黑人的暴力执法事件层出不穷……没有人去关注贫民窟里受虐待和折磨的穷苦少年,没有人在“我”的父亲无端被警察打死横尸街头时去帮助呼吁公平和正义。这个名叫狄更斯的美国当代小镇里仿佛正上演着英国作家狄更斯笔下19世纪英国底层小人物的苦难和悲哀。“棒棒糖”先生俨然是美国当代版的“雾都孤儿”。
然而相对于个人的不幸经历,“棒棒糖”先生“我”最不能忍受的还是故乡小镇的“被消失”、“被隐形”。为了让狄更斯小镇“复活”,“我”和非要死乞白赖做“我”的黑奴的邻居霍米尼(霍米尼另一个意思是“玉米片”)·詹金斯决定在当代复辟奴隶制。詹金斯是过气黑人演员,在表现种族歧视的系列电影《小无赖》里扮演刻板化的黑人形象。詹金斯支持奴隶制,或许是因为奴隶制下他至少还有个身份。“我”的复辟动机则显得更难理解,“我们实行种族隔离是为了给每棵树、每种植物、每个穷苦的墨西哥人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平等地获取阳光和水;我们是为了确保每一种生物都有呼吸的空间”。以不平等来换取平等,以种族主义来反种族主义,小说充满了矛盾和悖论,但正是这矛盾和悖论产生了讽刺和揭露的力量和效果。于是,“棒棒糖”和“玉米片”的搭档就组成了“堂吉诃德”和“桑丘”组合,他们俩同心协力为恢复小镇在地图上的名字而奔波:在高速公路口悬挂狄更斯小镇的指示牌;重新标记小镇的主要路标;写信到相关部门想为小镇找一个国际友好姊妹城;在公交车上贴上标语主张白人优先;说服当地的学校和医院推行种族隔离……吊诡的是,这种隔离马上收到良好效果:社区犯罪率下降了,学生的学习成绩提升了,人们之间友好了。种族主义好的颂歌就这样传颂起来。没有比这更尖酸的讽刺,没有比这更黑色的幽默了!
“堂吉诃德”和“桑吉”的最大敌人是当地著名黑人思想家福伊·柴什。柴什是黑人左翼知识分子中的领袖人物。他致力于修正名著中的种族主义思想和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用语,正在编辑出版没有“黑鬼”一词的洁本《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并将此书重新命名为《非裔美国人吉姆和他的被保护人年轻的白人兄弟哈克贝里·费恩在寻找失去的黑人家庭组织过程中含有贬义色彩的自由的心智历险记》。显然除了种族主义外,柴什就是作者保罗·比蒂讽刺的匕首要刺向的另一个目标:黑人内部“政治正确”派代表、伪善的功利主义学者。柴什是沽名钓誉的伪学者,他剽窃“我”父亲的学术思想、研究成果,取代他成为黑人民意领袖,但实际上则是住在白人区、享受同白人一般的财富和地位的已经“白化”了的功利主义者。他的“政治正确”是哗众取宠、为自己谋求利益和政治影响力的幌子。他在表面上代表黑人发声,实际上却根本不在乎穷苦黑人同胞的死活。相反,在“我”父亲死后,他一直怕“我”会继承到父亲的影响力,虽声称是父亲的朋友和追随者,却不但没给过“我”任何的帮助,反而处处打压和讥讽,甚至在“我”揭穿他之后恼羞成怒开枪将我重伤。他强烈反对“我”们的种族隔离计划,送“我”绰号“叛徒”,实际上他本人正是黑人平等和解放事业最可恶的“叛徒”。也正是因为柴什之流的控告,“我”被送到了美国高等法院的法庭接受审判。
接受审判的其实是美国现行的种族政策和人们对种族问题的僵化认识。保罗·比蒂是一位清醒的观者,他以马克·吐温式的辛辣讽刺、以斯威夫特式的睿智讽喻,怀揣狄更斯刺破现实的决绝勇气,借助后现代主义的荒诞背景,重演了一出堂吉诃德的救世“闹剧”。但闹剧背后,是对美国种族不平等现状的赤裸裸的揭露。它想提示我们的是尼日利亚裔美国作家克里斯·阿巴尼(Chris Abani)早已指出来的一个事实:“只要人们还在假装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奴隶制就不会真正结束。”在接受采访时,保罗·比蒂表示,他并不认为《叛徒》是讽刺文学,在他看来,这就是报告文学。他只期待这本书能开启一个严肃话题的讨论。
值得一提的是,贝蒂对种族问题的呼吁实际上超越了种族的界限。小说中有一个细节提到,一对白人夫妇不请自来观看“我”们黑人的聚会节目,却因总是不合时宜地大笑终被组织者强行赶走,“我”虽保持了沉默,但心中一直觉得这种做法冒犯了他们的自由。后种族主义的语境下,每一个人、每一种生物都应享有自由生活的权利、开心大笑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比蒂并非只为自己的族群发声,他为所有受歧视、被消声的弱势群体代言。
《叛徒》终归还是一部严肃的政治小说,它的诞生正逢其时,不仅是对后种族主义时代种种乐观论调的反驳,也是对种族问题上政治正确的伪善命题的揭露,当然,也许还能算作对当代美国国内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抬头这一现象的警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