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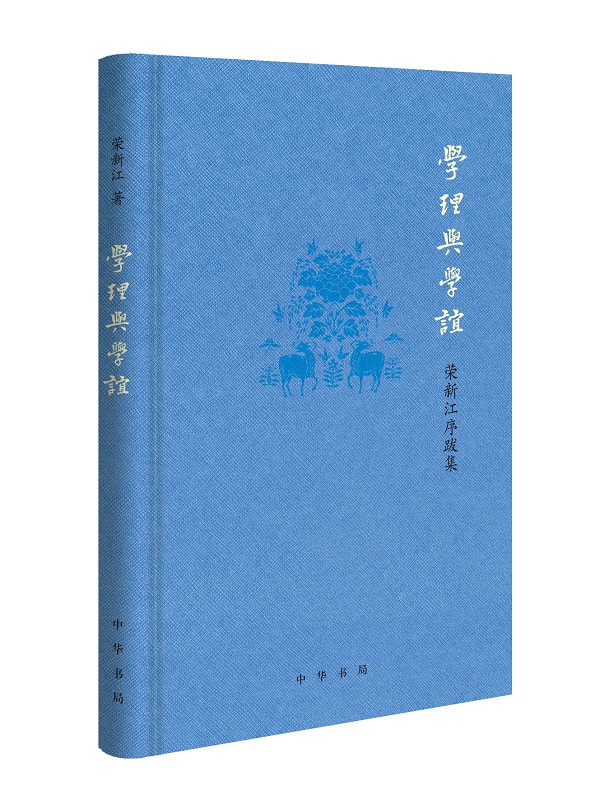
《学理与学谊:荣新江序跋集》,荣新江著,中华书局2018年6月出版,295页,56.00元
荣新江先生的新著《学理与学谊:荣新江序跋集》于今年6月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分为上下编,共收录作者近二十余年来所撰写的序跋类文章六十篇。是书甫一面世,即引起学界关注,已有评论性文字见诸报端(徐俊《序跋的意义》,《中华读书报》2018年10月10日第十版)。不同于一般书序的写法,在该书跋语中,荣先生明确表达了他写书序的主要初衷是“希望借助书序这种形式,按照不同书的内涵,阐述自己对一些学科门类的回顾和总结,并做一点前瞻和期望……从本学科的发展历程着眼,从学理上分析该学科的发展方向”(《学理与学谊》跋)。这实际上是在示来者以径路,其学术意义自不待言——这也是荣先生的书序与一般书序文字的最大区别。但事实上,这些书序的字里行间中,也无不贯穿着他的学术理念和学术思想,以及对学术方法的归纳、总结与反思。如果读者阅读此书时也能意识到这一点,则获益更大。因此,笔者以为,此书的内容,除了反映“学谊”外,更重要的是“学理”与“方法”的启示。
论及自己的治学,荣先生常常会用“庞杂”一词概括,说自己“平日治学,颇为庞杂”(《中国中古史研究十论》序言)。的确,他的研究领域涉及中外关系史、敦煌吐鲁番学、隋唐史、西域史等多个领域;就具体研究对象而言,除历史学之外,还涉及宗教、考古、艺术史、文献学(含出土文献)等。但这看似“庞杂”的背后,隐含着他一以贯之的学术理念,那就是“贯通”的思想,因此,“庞杂”可视为荣先生对自己的“贯通”理念的谦虚表达。他对陈寅恪先生“国人治学,罕具通识”的警示念念不忘,在不同场合经常提及(《敦煌讲座书系》总序),意即在于此。陈寅恪先生的“通识”观,蔡鸿生先生理解为“全景式的历史思维”(蔡鸿生《读史求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可谓确解。
 荣新江(澎湃新闻李媛 绘) 荣新江(澎湃新闻李媛 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