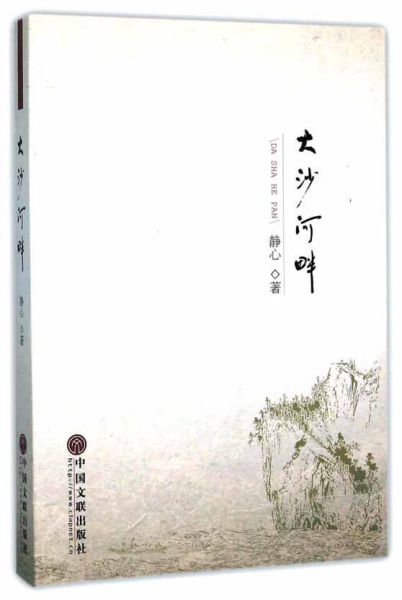
静心的写作呈现出一个特色,即有大量的生活细节在里面。我一直在想怎么将它表述出来。她的写作是一种“反理论”的写作。她自己是搞女性文学研究 的,但《大沙河畔》这部小说看不出是搞理论的人写的,作者完全放弃了自己教授的架子和所有专业的东西,变成了一个生活的观察者,一个贴近生活的细节呈现 者,而且细节没有经过刻意的裁剪。 小说家往往有一种习惯,要对生活细节进行剪裁加工,但这个剪裁加工的过程有时候会损害生活,因为他要把自己认为重要的细节留下来,把不重要的细 节省略,这样加工过之后实际上已经不再是生活的原生态了。但静心的写作几乎把所有的生活细节都交代出来了。这个时候作者似乎忘了她是一个有着专业理论修养 的女性主义者,她没有身份,只是一个生活的呈现者,这是充满了经验性、生活性和当下性的写作。比如小说里面写的人物——家明母亲,河南人读起来特别有感 觉,充满了方言土语,特别真实,人物不是空洞的,而是由生活细节堆积起来的,是鲜活的、有质感、有力度的,就像一口唾沫砸出一个坑儿。因此,这部小说在某 种程度上逃逸出了理论的束缚,也就是说,不能用哪一种理论去分析,而是有自己的一种写作法则。这是按照生活伦理展开的写作,而不是按照理论套写的作品。 作者在朴素的生活伦理中思考女人和男人,思考普通人的命运。可以看到,这部小说里有不同的声音和价值观,玉儿可能代表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有知 识、有学养的女性,而家明妈,包括老二媳妇,都是没有什么文化的妇女,代表另外一种女性的价值观。小说讲述了玉儿被老一辈的女性价值观说服的过程,玉儿总 是在反省,她被婆婆感动,被没文化的妯娌感动,她觉得这些看起来土气的女性身上怎么有这样一种自己没有的东西。她读过书,但很多时候不如人家有见识。玉儿 的这种感动,表明知识分子的声音被平民的声音说服了。 作者本人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大概是玉儿的原型,因此,这也表明一个有西方知识背景的作者被中国本土的生活伦理说服了。家明妈不是没有缺点,她有 很多毛病,比如爱虚荣,儿子出息了,开着车给她拉东西过来,她就跑到外面拖着调子喊“卸——车!”但这个有缺点的老太太很可爱、很真实。一个普通中国老太 太,含辛茹苦抚养了四个儿子,儿子有出息了,炫耀一下有什么不可以呢?按照西方主义女性理论来解释,家明妈是完全为男性、为家族、夫权牺牲了,是失败的, 没有主体性的,但按照中国的生活伦理来讲,这个女性太有价值了,太值得尊重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逻辑里面是说不通的,虽然玉儿受过大学教育,但她 婆婆的逻辑更强大。这使我觉得,平民伦理,中国的日常生活伦理,打败了或者说同化了一种精英主义的写作和叙述,小说里玉儿对自己知识精英的身份是有所警惕 的。因此,这部小说写的是生活中的女性,而不是理论中的女性,这是很难得的。 小说里面有一个细节,写家明妈年轻时结婚,别的可以不要,死活非要一对瓷瓶子。大家都觉得很奇怪。而在家明妈看来,新媳妇结婚抱瓶子,就是一辈 子平平安安、和和美美的意思,瓶子如果是租的,就不吉利。这对瓷瓶跟随了家明妈一辈子,无论多么艰苦,她也坚持保留着它。我们可以把这个瓶子看做是民间伦 理的象征。家明妈对瓶子的珍爱,也意味着对民间伦理的坚守,这种伦理的核心便是女性的奉献牺牲精神。看上去这对瓶子并不起眼,也不值多少钱,但恰恰是依靠 这对瓶子蕴含的精神力量,家明妈将四个孩子抚养成人。看到这些,作为知识分子的玉儿“忽然眼眶有些发热”。她理解到,中国的女性正是通过牺牲自己来实现自 身的主体性和人生价值,这种价值是以男性为核心的,但又是实实在在的,是延续了家族和民族生命力的,这恰恰是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所不能理解的。 小说中玉儿思想的变化,我们可以视为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命运的一种隐喻,也就是说,女性主义理论一定要有中国化的过程,一定要有一个跟本土生活 伦理相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谁被谁打败的问题,而是在哪一个立场上,认同谁的问题——究竟是认同中国的生活伦理,还是认同海外舶来的女性主义。所以, 我认为作者的思想应该属于现实主义的女性主义。一个人不可能对生活永远剑拔弩张,她最终要与生活和解,和解以后就是一种现实主义女性主义的态度。 静心对于生活伦理的尊重或者认同,使得她在形式上也呈现出生活化的特征。她的语言完全是口语化的,是一种贴近方言土语的表述方式,这与她对生活 伦理的认同和尊重是相适应的。她没有采用很西化、很先锋的精英主义的写作方法,如此,她就跟我们今天的一些女作家拉开了距离,形成了差异。如果静心写《伤 逝》,我想她不会让子君去死,而是不管用什么方法,哪怕当小姐卖身也要活下去,因为生存是第一位的,为了养育孩子,保存家庭,没有什么苦难是不能承受的, 没有什么是不能做的,活下来是第一位的,这就是最普通的中国人的生活伦理。 我觉得《大沙河畔》最大的一个贡献,便是作者通过玉儿这个人物的塑造,对作为女性知识分子的自我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其中既有来自西方女性主义理 论带来的启蒙和批判,也有来自生活经验的纠正与认同,从而使读者对中国女性的命运和历史处境有了更为深刻的同情与理解。这是与作家自己的生命体验分不开 的。她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在80年代早期大学毕业,既受过高等教育、长期从事学术工作,又经历过“文革”、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关切、熟 悉社会变迁中普通妇女的生活与思想。更重要的是,对于她笔下的那些普通女性,她采取了平视的、同等的、感同身受的态度,这就使她的作品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宽 厚阔大的现实主义品格和气度,跟今天一些女性作家那样居高临下、怨念深重地审视女性/男性的精英主义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