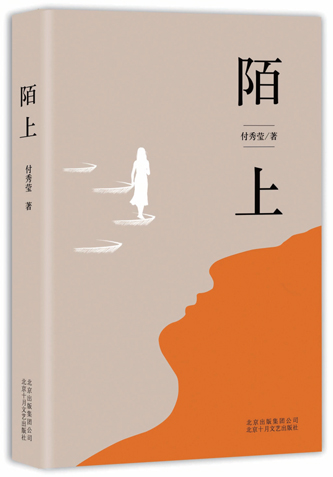
芳村培育了付秀莹的价值观、情感方式以及情感表达方式和美学趣味,也只有那块地方可以慷慨地、源源不断地向她无私地提供写作资源。
在付秀莹这里,文学性是至高无上的。在写的过程中,她会自觉不自觉地将“小说是一门艺术”的理念固执地坚持着。她会考虑结构的问题、语言的问题、语调的问题、意境的问题……一切小说要考虑的艺术问题。
有评论说,福克纳写来写去,只写了“邮票大”一块地方。这不免有点儿夸张。其实他笔下的那块地方并不算太小——付秀莹笔下的那块地方才小,与福克纳笔下的那块地方比较起来,她那块地方就只能说比“邮票还小”了。她写来写去,只写了一个小小的村庄——芳村。她的几乎所有作品,都是建立在芳村这块土地上的。
就空间的占有而言,这世上的作家分两路,一路是开放性的,东西南北,攻城略地,四处扩张,空间扯得很大。海明威便是这一路的。他这一辈子写美洲、写欧洲、写非洲,写了太多的地方,陆地不能满足他的“野心”,直写到了无边无际的大海。一路是收敛性的,有节制的,不跑马圈地,不扩张文学的领土,倒喜欢在一方小小的土地上做文章,有意的。在后者看来,与其海阔天空,不如就在一块小小地方踏踏实实、好好地做一番文章,细细地写、深深地写、彻彻底底地写,写它个不分男女老少皆原形毕露,将文章真正做到家,直到抵达圆满。如此这般,很有做实验的感觉,看看这封闭性的一隅,人性究竟是如何表现的。这块地方就是实验室——实验室自然不大,但它研究的却是全部人性,折射的却是无比大的空间。从这点而言,福克纳与海明威,只是写作的路数不一样而已,形而上的空间却并无大小之区分。
芳村不小,芳村很大。它几乎就是整个的中国农村,是中国农村的缩影,甚至更大,大到整个人类社会。只写比“邮票还小”的芳村,其实也是一个颇为艺术的构思和安排。
我想,付秀莹之所以如此“局限”自己,是因为她本就不是一个走南闯北、浪迹天涯、广泛涉猎不同疆域的人,她最熟悉的空间也就是生她养她的芳村。表面上看,她虽然已走出芳村,但实际上她永远也走不出芳村。那块地方培育了她的价值观、情感方式以及情感表达方式和美学趣味等。也只有那块地方可以慷慨地、源源不断地向她无私地提供写作资源。她也绝不嫌弃芳村的资源,因为她已经聪明地发现,芳村资源是优质的,并且是独一无二的。那些风土人情、乡村故事,定能够帮她在文坛占有一席之地。也许,她会终于不再写芳村,但至少现在还不是时候。因为在她觉得,其他的空间,还没有与她的肉体和灵魂完美融合,而芳村的资源也没有现出枯竭的先兆。
“风俗画”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经久不衰的传统。我们在《红楼梦》中——甚至是在更早的中国文学作品中就看到中国文学家们对风俗画的喜爱。而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对风俗画的描绘则已蔚然成风,并对风俗画的意义有了十分理性的认识。无论是在倾向于写风俗画的沈从文那里,还是在并不特别在乎写风俗画而另有意图的鲁迅那里,都有许多地道的风俗画描绘。进入上世纪80年代,风俗画的传统又再度续上,并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登峰造极,汪曾祺等人以及他们的书写一时成为批评家和文学硕士、博士们的热门论文题目。在此风尚之中,甚至还出现了一批伪风俗画的作品。
但到上世纪末,文学被其他种种心思所牵,更因时代气场的转移,这一风气式微,风俗画与我们的文学渐行渐远。恰在此时,付秀莹不声不响地出现了。她竟然又开始了与这一传统的悄然连接,并且更加专注与认真,也更加自然。我们在她的几乎全部作品中都看到了她的这一难以消退的兴趣。也许在她这里,这并非是一明确的意识,只不过是她觉得既然书写乡村,也就会自然而然地带入风俗画——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这些繁多的风俗。它不仅影响了乡下人的世界观和生活情趣,也是乡村生活的重要内容,许多乡村故事是与这些风俗纠缠在一起的。
生老病死、婚丧礼仪、民间宗教以及各种各样乡村节日——有些节日也许不仅仅属于乡村,但乡村有乡村的方式,一个乡村又有一个乡村的方式,这一切才使乡村生活成为与城市生活不一样的生活。它们既是乡村的符号,也是乡村与其无法剥离的现实生活。它们最终形成了具有一定稳定性的风俗画,一代一代延续着,常看常新。我们发现这些风俗又常常是与中国特有节气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节气便成为她的作品的重要元素,最终导致她不写节气就无法让她的人物出场、无法开始故事的叙述。这部长篇小说一开头,竟然用好几页文字,不慌不忙地按时序写了各种节气以及与节气相关的若干风俗。接下来的叙述与描写,风俗画无数次地镶嵌在她的行文之中。我们现在无法设想,若将全部风俗画从她的作品移除出去,她的小说是否还能存在。当然,我们也会这样发问:若无这些风俗画,乡村生活是否还存在?是否还是乡村生活?
就付秀莹而言,她沉浸于风俗画的书写,可能还因为这种书写满足了她的美学情趣。这种情趣含有诗性,含有远古的缥缈与神性。
世上小说无非两种,一种是写日常经验,一种是写震惊经验。
付秀莹的小说通常只写日常经验,而不写震惊经验。无论《爱情到处流传》等短篇小说还是这部长篇小说,写的都是一些日常琐事。这些事甚至连事件都谈不上,只能算作事情。这些事情平平常常,甚至平平淡淡,事情的发展很难说有什么高潮,更难说高潮迭起。她的作品经不起我们认知的小说情节设计的通常格式去衡量,因为它完全是按另样的小说理念写就的,搭不上。这些小说理念几乎就是她个人的,因为我们在以往的小说史上,还很少见到如此日常的小说。上世纪80年代,曾有新现实主义浪潮兴起,一批作家热衷于日常经验的写作,“一地鸡毛”成为那个时期得宠素材的象征。但现在回头去看,这些日常经验依然在情节上是有很用心的安排的。而付秀莹的小说,看上去在情节安排上是没有什么心机和计划的。我们甚至很难说她的作品有什么情节。面对她的小说,过去的那套小说艺术的条条框框,几乎没有任何解释能力。可是只要开始阅读,你又无法抗拒它的阅读魅力。就在比新写实主义的日常经验还要日常的经验之中,我们被她的看似平常的叙述无声地掌控,而不知不觉地失去自己。
当我们真正回到人类生活的本真状态时,也许我们会承认付秀莹是有理的:人的日常状态就是如此,并无大起大落的事情,也无看上去特别严重的事情,一切就是那么回事,并非如从前小说写的那样忽上忽下,波澜壮阔——波澜虽有,但弧度很小。小是小,却依然抓人,甚至比那些写震惊经验的小说还要抓人。究其道理,大概就是如此状态更切近实际存在之状态。
但付秀莹同时也看到了一个事实:这世界上并非没有震惊经验,但这些震惊经验,常常是日常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的突然爆发。付秀莹创造了付秀莹式的结尾:还是一副平平淡淡的样子,还是一种平平淡淡的叙述,最后事情忽然陡转,变得异常严重。看似突然,但细察,就觉得这般严重实是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必然的结果,人家是早有伏笔的,完全合乎逻辑。这些结尾往往只三言两语,并且在叙述上依然波澜不惊。这就是付秀莹的小说艺术。
在付秀莹这里,文学性是至高无上的。她的院校背景,我们似乎在她如此乡村的作品中不太能看得出来。我们似乎很难将如此风格的文字、情调和生活,与她高等院校的学习背景联系起来。新时期出来一批有院校背景的作家,但他们的腔调以及关注的生活领域,显然与她两样。即使写乡村,也一定不是这样的乡村。一看就是局外人。院校培养了一批这样的作家。那么,付秀莹的学院背景果真没有对她的写作产生影响吗?否。我们只要仔细追究,细心体会,就会很容易在她的文字背后看到一种文学态度,而这种态度一定是与院校背景有关的,这就是:十分看重作品的文学性——并且是十分纯粹的文学性。她的打着付秀莹烙印的文体本身,就是院校学习的产物。与她同时,写乡村的小说很多,我们可以比较一下,马上就能发现她的乡村小说与非院校背景的作家所写的乡村小说的明显差异。我们这里无意说两者高下,而只是说一个事实。
她写,肯定不只是一门心思地去写乡村生活,在写的过程中,她会自觉不自觉地将“小说是一门艺术”的理念固执地坚持着。她会考虑结构的问题、语言的问题、语调的问题、意境的问题……一切小说要考虑的艺术问题。大概也正是她如此在意小说的艺术问题,由她创造的这些文本才会成为我们今天文学批评的话题。关于她的小说,我们有许多话可说。比如风景描写。我们很少看到今天的小说家像她如此恋迷风景。这是一个失去风景的时代。而在她这里,若没有这些风景,文字活动简直无法进行。阅读她的作品,我们随时可以与风景相遇——一路风景。而她的风景又是别具一格、气象非凡的。她的风景背后,似有中国古典诗歌的风韵。世间万物,在她这里,都是有灵的。再比如她小说中的象声词。她的小说永远是有声音的,风声雨声,蝉鸣蛙鸣,这世上,就没有无声之事物。而她的象声词常常是她独创的。“远远地,谁家的鸡开始打鸣儿了。我——一声儿,我——一声儿,我——又一声儿。紧跟着,像是故意凑热闹,又有一只鸡叫起来。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雨丝细细的,一千簇一万簇银针似的,从半空里落下来。落在树木上,花草上,苏苏苏苏的乱响。” “骑上电动车,日日日日日就走了”……这些象声词,远比我们从前的词典里规范的象声词更形象更准确也更容易让人产生联想。她的作品似乎开创了一个象声词的新时代。再比如……
付秀莹的小说世界是极大丰富的。
“付秀莹文体”既是现代文学史的一脉相承,又是她富有灵性的个人创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