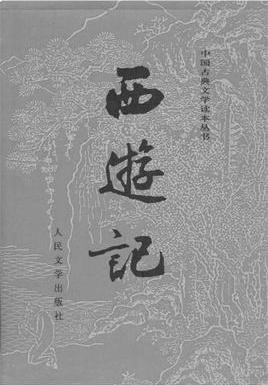
作为举世公认的神话艺术的翘楚,《西游记》及其开创的神话小说流派彻底打破了中国神话的贫乏局面。纵观世界文坛,没有一个古典神话形象能与孙悟空相媲美,在今天或许只有J.K.罗琳的《哈利·波特》可以与《西游记》相颉颃。
《西游记》打破了小说与文化关系的困境,开辟出一条既为主流文化认可,又能保持其艺术本体的途径:作为一部世代累积型巨著,在漫长的成书过程中,吸纳了不同时代的思想内容,儒释道三教杂处、融合,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包容性。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国际论坛评论小说名著《西游记》,并向国际社会、外国知名人士作热情的推荐、介绍。例如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中阐述丝绸之路与佛教的关系,指出《西游记》记叙唐僧取经“体现的是中国人学习域外文化的坚韧精神”;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又将《西游记》与《马可·波罗游记》并举,盛赞玄奘大师与马可·波罗对人类文明的贡献。(陈振凯 石磊《习近平访欧十一天 一路文化一路诗》,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4月3日)不仅引起国内外舆论普遍关注,而且还由此形成一个共识:《西游记》正是世界认识中国的一扇文学之窗,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光彩耀眼的新标杆。
从当下流行之“文学——政治”美学的立场看,习近平总书记的评价符合《西游记》的实际。众所周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同列中国小说四大名著,但唯有《西游记》最适合中国文化的域外传播,因而也最具有国际影响力。《三国演义》讲叙三国内战,《水浒传》以“造反”为主旨,《红楼梦》是一部“彻头彻尾之大悲剧”(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与当下世界发展大势似乎有着一些天然隔阂,《西游记》则以追求真理为主题,以中西文化交流为目标,以扫荡邪恶、战胜九九八十一难争取自由为主要内容,同时还具有佛教文化的纽带,与和平、发展的世界主题最为契合,也特别容易被外国大众所接受。现在东南亚各国掀起了《西游记》热,英美等西方国家也有许多《西游记》译本和影视作品问世,这一现象并非偶然。文化作为政治、经济的集中体现和羽翼,当然要紧贴时代步伐,传递“正能量”,顺应浩浩荡荡的世界大势。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推荐、介绍《西游记》,正逢其时,意义深远。
由此想及,对于《西游记》的价值评定,学界曾经严重滞后,亟需反思、探索,寻求突破。如钱锺书先生明确认为《西游记》是中国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因为迄今为止人类两大难以实现的梦想——飞天与入地——只有在神话小说《西游记》中得到完全的实现,孙悟空“腾云遁地的神通”正是这一人类理想的象征。(杨绛《钱锺书与〈围城〉》)林庚先生公然表示《西游记》是其“最爱”,称它的理想精神和“童心主义”鼓舞、陪伴自己“度过一生中最困难的日子”(《西游记漫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两位当代学术大师的论断即是一种宝贵的“重评《西游记》”的文学史新声。
对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文艺思想,可以对《西游记》的文化价值进行重新思考、探索,从而作出全新的评价,实现准确、合理的文学史定位。
那么,《西游记》具有哪些特殊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呢?
一、 开辟再生型神话,实现中国神话复兴
中国是文明古国,创造了独步世界的辉煌文化。但就神话艺术而言,成就和影响都不堪匹配。如与辉煌的古希腊神话比照,则难免逊色:我们虽有《盘古开辟》《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和《后羿射日》这样精彩的神话(传说),但相对凌乱芜杂,缺乏神谱和体系,“终不闻有荟萃熔铸为巨制如希腊史诗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早年日本学者盐谷温首提“中国神话贫乏”论,颇惹国人非议,总以为日本文化受中国文化哺育,日本人没有批评的资格,批评即是数典忘祖。但其时鲁迅、胡适等具有世界性文化胸襟的新文化大师对此均持相当的认同态度,并进一步分析、解释中国神话“不发达”的原因,印证、张扬其说。如鲁迅认为中国神话无法与古希腊神话媲美,究其缘由在于:一、中华先民“重实际而黜玄想”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二、儒家(孔子)疏远“太古荒唐之说”和“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思想文化规范。(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对此,胡适也指出:古代的中华民族是一种朴实而不富想象力的民族。中华先民的历史条件缺失培育、包容神话的“土壤和武库”(马克思语),也不利于神话精神的滋长和神话作品的保存。除此之外,还有其三:中国社会动乱频繁,导致文献(神话)散失,据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揭示,中国文献积累饱受动乱兵燹和外国强盗的祸害,在中国历史上遭受的文化劫难有15次之多,而在散失的文献中,一定会有大量的上古神话记载存在。
然而,我们看到,自《西游记》在16世纪横空出世,光芒四射,照亮了整个世界。英国著名东方文化研究家阿瑟·威利说:“《西游记》像一颗璀璨的彗星升上了中天,给西半球人民展出一个神奇的世界。”它不仅继承了《后羿射日》《盘古开辟》等上古神话宏伟绮丽的想象力,而且以再生态神话的艺术形态融合中华民族文明时代的情感、智慧,特别是对自然、社会、历史和人生的深刻认识,成为举世公认的神话艺术的翘楚。纵观世界文坛,没有一个古典神话形象能与孙悟空相媲美,在今天或许只有J.K.罗琳的《哈利·波特》可以与《西游记》相颉颃。正如我国小说史家杨义先生指出,《西游记》是我国神话文化的大器晚成之作,作为一部我国“神话文化的伟大杰构”,其划时代的文化意义是“以小说的形式把我国神话文化的形态面貌——不发达落后面貌——从根本上改变了”,在文化史上,则“代表着我国神话文化的一次划时代的转型”。(杨义《〈西游记〉:中国神话文化的大器晚成》,《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无可置疑,正是《西游记》以及它所开创的神话小说流派彻底打破了中国神话的贫乏局面。随着《西游记》这一中国神话新标杆的矗立,“中国神话贫乏”论宣告熄灭。
另外,童话是神话的孪生体裁,《西游记》也是一部深受历代儿童喜欢的童话作品,我国神话学奠基者袁珂先生明确说:“今观《西游记》纵恣谐谑,独逞胸臆,其调诙之所及,至于仙佛同仁,神魔一体,其他神话小说中固未见有此种格调也,故吾曰,谓之为世界的一部绝大童话小说,宁非尤宜。”(袁珂《〈西游记〉研究》,刊《台湾文化》1948年第3卷第1-2期)所以,《西游记》还在现代中国童话奠基与提供范本,培育、促进中国文学理想精神与浪漫文风方面,显示着独特的价值。
二、与中国主流文化深度契合,成为不可多得的文化典籍
现代文学理论将文学定义为文化的意义载体,极大地扩大了文学的价值疆域,文学研究也是一种“价值阅读”和价值认定,“试图尽可能和准确地描述出作品中所发现的价值”,洞察深藏其中的文化“底色”(理查德·霍加特《当代文化研究:文学与社会研究的一种途径》,《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从这种文学与文化的异质同构关系来说,《西游记》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契合,具有最为典范的文化载体功能,甚至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宝典。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主要特征是儒、释、道三教融合、互补,其中孔孟儒学构成整个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佛学与道家则从两翼以不同的方式向儒学不断渗透、夹击,从而激发一轮又一轮鼎立冲突和合流互补的文化潮流。由于小说长期被正统文化贬为“君子弗为”的稗官野史,不入流的残丛小语、小家珍说,与主体文化处于先天疏远或是背离的关系。至明清小说繁荣之际,两者关系抽象、畸形发展,小说具备了反映主体文化的权力,但并未寻找到合法而又合理的形式:反映儒学沦为枯燥的正统说教,反映释、道两家又陷入所谓宗教小说的泥淖,在加深“文化底色”的另一面则是丢失了小说的艺术本色。令人震惊的是,《西游记》以其得天独厚的艺术审美精神打破了小说与文化关系的困境,开辟出一条既为主流文化认可,又能保持其艺术本体的途径来:作为一部世代累积型巨著,在漫长的成书过程中,逐渐吸纳了不同时代的思想内容,所以作品儒、释、道三教杂处,思想十分繁富,它并不是以某一派、某一部特定的书(无论是儒家经典,还是佛、道典籍)来作为固有、单一的文化原型,而是三家并举、融合,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包容性;作为神魔小说,《西游记》笼罩着一层特有的炫目迷心的外衣,其间儒、释、道三教合一,神仙妖魔鬼魅九流驳杂,这赋予了作品涵盖其深奥玄妙之思想意蕴的无限空间,其抗击礼教束缚、弘扬感性生命力的浪漫精神,借此喻彼、假象见义的象征方法和放诞、神谕元素又保证了作品在诠释文化意义时避免陷于偏执、逼仄的境地。
在文学承载文化,特别是契合主流文化(文化精华)的艺术实践中,《西游记》不失为成功的典范。鲁迅曾经指出:“说到这书的宗旨,则有人说是劝学;有人说是谈禅;有人说是讲道;议论很纷纷。”(《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国小说史略》附录)把明清时期纷繁的《西游记》主题观归纳为释儒、谈禅、证道三派,应该说是符合作品的思想实际的。虽然在清代盛行的三家评本中依然存在着阉割传统文化,对各派思想篡改伪注的倾向,但这并不改变和否认作品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整体融合和准确反映。
仅以其儒学意蕴为例。《西游记》的本体是佛教故事,又因宗教上的佛道论衡而掺入大量道教内容,故有“仙佛之书”一说。但是,历代读者都惊奇于其中深邃的原儒精神。比如,孙悟空神通广大,唐僧愚昧无能,孙悟空为什么还要对唐僧如此忠心耿耿呢?
这个问题,貌似简单,其实似小实大,离开儒学背景是无法解释的。原来唐僧、孙悟空的师徒模式来自儒家祖师孔子和其弟子子路的故事。据文献记载,子路曾经误解孔子,而对孔子起谋害之心。孙悟空与子路一样,对自己的师父有一个从不服,甚至反叛、敌对,到最后心悦诚服、“至死靡它”的过程。其实质正是儒家“尊师重教、师道尊严”的伦理规范。在中国历史上“师道尊严”已成儒家道统,《西游记》中唐僧、孙悟空的师徒关系也形象地反映出这种道统。
翻检《西游记》,这一类儒家表征俯拾即是。对此,我们不禁要感叹:谁又能够想到在我国近古的“三教归心”的文化思潮中,《西游记》的作者竟能如此合理地撷取千年中华文化的智慧而又能超越儒、释、道等具体宗教的偏执,突破其各自疆域而融合之、光大之,从而为后世小说提供科学反映文化的范式呢?在汗牛充栋的历代小说中,以反映文化的广度和深度而论,又有哪一部作品能与《西游记》相携手相颉颃呢?《西游记》与中国文化思想的深度契合,借用鲁迅评价《金瓶梅》的说法,即是:“纵观同时说部,无以上之。”
三、 科学未来意识,提升民族理性思维
神话原本与理性思维无关。马克思说,神话是原始先民运用天真的情感和想象力“征服自然力”、将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的结果,而现代神话批评则认为远古神话作为“集体无意识”,“既不是虚构的谎话,也不是任意的幻想,而是人类在达到理论思维之前的一种普遍的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思维方式”。《西游记》是再生态神话,继承了中国远古神话的艺术精神,但在“情感——想象”的性质与书写的形式上已经发生质变。它在形式上“文备众体”,集神话、童话和小说于一体,构成与上古原始神话完全不同的再生型神话体裁。从征服、支配自然力的理想而言,它并非朦胧的原始思维的产物,而是自觉的艺术思维的结晶,它的大旨其实不在“表现中国古代对自然与社会现象的天真解释”,因为人类对这些现象的解释已趋于成熟(科学解释),而是在神话这一艺术载体里渗透了文明时代中华民族的情感精神和理性智慧。其中最能体现这种理性思维成果的是:在对人类社会进行美好遐想中传递出宝贵的科学未来意识。
如果从现代未来科学的角度来看,《西游记》在四百年前虚构、遐想的许多奇妙景象已被现代科学技术所证实,有的正在被列为世界尖端科技项目进行研究攻关。如“千里眼”之于望远镜和空间探测技术,“顺风耳”之于电话、电报等通讯技术,“风火轮”之于现代轨道交通,“上天入地”之于飞机和地下交通设施,“水遁土遁”之于潜艇和地铁、隧道,“腾云驾雾”之于宇宙飞船等航天技术,“日行千里”之于汽车、火车等交通技术,“照妖镜”之于镭射激光技术,“杏黄旗”之于导弹、氢弹等原子能科学技术,“招魂幡”之于现代特异功能,“口吐白沫、散豆成兵”之类法术则令人想起人工降雨和飞行播种技术……当我们看到日本海啸和上海11·15大火给人类造成的巨大灾害,不禁要呼唤定海神针和芭蕉扇你在哪里?当我们饱受沙尘暴、雾霾之苦,面临纱巾裹脸、透气不便的尴尬,便不禁遐想:定风丹你又在哪里?……
欣赏一下“金猴出世”故事。他本是花果山上一块巨石,“每受天真地透,日精月华,感之既久,遂有通灵之意”,“内育仙胞,一日迸裂,产一石卵,因见风化作一个石猴”。这个故事恰恰蕴涵着关于宇宙生命起源的伟大构想,顶得上一部漫长的生命起源史。根据自然辩证法和生命科学原理,宇宙和地球原本没有生命,它是由天体运行规律,地壳变动,地形特征的世纪性变化,以及各种自然力包括光、空气、水、电、雷、风的共同作用,而逐渐孕育出来的,在50亿年前开始产生了生命的源头大分子有机物,10亿年前诞生了完整的生命雏形细胞。而人类的起源则仅仅是生命起源的一个“类”。“金猴出世”不正是这50亿年生命孕育、诞生的缩影么!而与上古神话中的同类作品《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比较,《西游记》的理性意识和科学精神是十分显著的,面对远古神话的虚无缥缈,屈原就在其《天问》中诘问“女娲有体,孰制匠之”?我们也可以发出同样的诘问:盘古有体,孰制匠之?然而面对《西游记》对生命起源的大胆构想(现代科学最后真切揭开生命起源之谜的细胞学说发现于19世纪,德国科学家施莱登和施旺的细胞学说被称为19世纪三大科学发现之一),我们却唯有惊叹不已。
检视近年间突飞猛进的科学发展,《西游记》的科学未来意识和高科技想象又可以在定颜珠与冰冻休眠术、唐僧和猪八戒怀孕与男性无宫分娩、孙悟空毫毛术与克隆等三组对应关系中得到最新的印证。众所周知,冰冻手术、男性无宫分娩、克隆,都是造福人类的高科技新发现、新成就。
需要指出的是,中华民族素以勤劳勇敢之称享誉全球,理性思维并不发达。李泽厚先生把中华民族的思维特征概括为“实践理性”,实践性的掺入导致理性思维并非纯正。(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那么,在中华民族的理性思维培育中,具有充分的理性思维和未来意识的《西游记》就显示着一种宝贵的启迪意义,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站在科学理性思维立场曾高度评价、由衷感谢《西游记》。他们在诺奖答奖辞中说:“科学上的许多成果正是孙行者式的理性思维模式的结晶!”科学研究的神髓就是“要从艺术中汲取营养,寻求创新的思路,科学与艺术携手追求真理。”(李政道:《携手追求真理普遍性》,《文汇报》2000年1月4日)
结语
经典属于过去和未来,既具有历史的凝重感,也具有无限的生长力。一方面,《西游记》作为伟大的文化经典具有包容性、开放性,提供后人价值发现的余地(学界特称“空白结构”),它固有的文本价值被不断地发现和发掘出来,正所谓“说不尽的《西游记》”、“说不尽的吴承恩”。另一方面,《西游记》艺术结构的强大张力表现为一种在文化上的物化和物态化功能,在当代社会不断孵化和催生出新的文化产品,诸如影视、图像(卡通)、邮政、游戏、商标注册、网络游戏(软件)、儿童玩具等一类西游文化产品早成铺天盖地之势,甚至连《西游记》主题乐园、《西游记》文化节等重大的西游文化经济建设项目也在全国各地不断涌现。这对于《西游记》,固然是新的文化价值的延伸,对于中国社会,也不失为一种宝贵的文化创新的源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