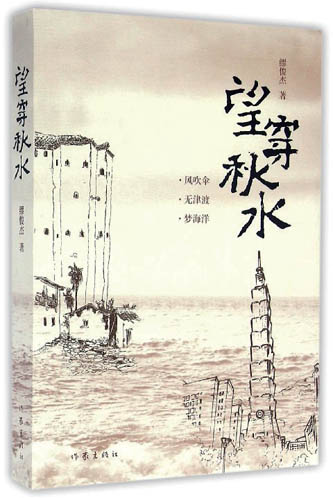
小说虽是虚构艺术,不像散文、诗歌那么直接,但终究会暴露作家的生活底色、情感底色和价值底色。发掘这些底色,其实是评论的一大乐趣。对于新作《望穿秋水》,尽管缪俊杰再三强调“这不是自传,个人色彩很少,人物没有原型”,但缪公的一些底色,通过这部《望穿秋水》以及之前的《烟雨东江》,已然约略托出。
《望穿秋水》是作者前一部长篇小说《烟雨东江》的姐妹篇。这两本书共同结构出一个客家书写系列,前者或可称“颂”——关于“脊梁”的书写,后者或可称“风”——关于“基础”的书写。
地理的迁徙产生文化的迁徙、精神的迁徙,在离乱中迁徙、漂泊和择地扎根的中原汉人后裔,凭借坚韧执著的生存意志以及对汉儒文化不遗余力的承传,形成了独特的客家群落和文化气质。在今天,客家文化也在不断地被改造、被消解。用一句流行的话叫“故乡在沦陷”,关于客家的文字书写一直不多,将要沦陷的故乡需要怎样的书写?
缪俊杰是赣州定南客家人,赣南是他的第一生活现场,在《望穿秋水》中占据了基本笔墨。表面上,长篇小说《望穿秋水》圈出了赣南和台湾两大生活地点,当然还延展到武汉、香港甚至海外,但这些都是配料。对于刘求福流寓了30年的台湾,作家通过一个人的足迹,还原国民党底层官兵辗转来台后的“荣民”生活。小说中描写的生活细节和情感形式,基本是赣南客家生活的台湾版。这种虚构逻辑是符合当时人物的身份和经历,“盐米古道”上的挑脚佬、文化程度不高的刘求福,被国民党抓壮丁到台湾之后,在拮据的经济条件下长期保持着简朴的赣南乡下的生活方式和姿态。因此,小说看起来写了两大场域,其实还是以赣南为主体。在历史变迁的潮流裹挟下,一对微如草芥的青春恋人音信不通30年,一个在乡,一个去乡,在乡者在命运的百般播弄中坚守,去乡者在辗转不定的流徙中执著还乡,“乡”是贯穿始终的叙事依据。
小说写出多舛多变的命途遭际,写出变迁中的不变的人心,写出了安营扎寨的客家文化本质。对于赣南客家文化的自觉传播,作家这种显而易见的自觉,一方面源于客家知识分子的自觉,一方面源于“记忆自觉”。客家知识分子的自觉相当于“族群自觉”,是文化层面的自觉。“记忆自觉”是先天的,是一个作家的写作密码。写作中的这种“记忆自觉”,确证了写作这种精神活动的表达、宣泄和记录功能。“记忆自觉”沉淀为DNA,如影随形地潜伏,被誉为写作的“根性”。根性可以分解为很多可以溯源、延展和探研的底色。
小说写作有两种,一种是“私”小说——只写写作者本人以及与其有关的生活,一种是“公”小说——对他人生活的张望和想象。虽然写小说之前的缪公,“元身份”是理论家和评论家,但沉潜的文化DNA,看来无法改变。作为“公”小说的《望穿秋水》不像“私”小说那样直接,但作家对于他者生活的各种想象、虚构的依据仍然来自于其客家生活经验,比如对于饮食起居、婚丧嫁娶、生产教育的铺陈,不厌其详,津津有味。但小说不是风俗史志,文化的大幕拉开后,要写出人际关系中人物的行动逻辑、性格气质、命运遭际。坎坷际遇和生存压力形成了客家人性格中的坚韧和耐受力,比较起普通汉族人,他们生存危机感强烈,能吃苦,有开疆辟土意识,常年流徙的生活也使他们对故土和故园异常眷恋。比如刘求福,在台湾漂泊30年期间,始终不曾婚配,不愿定居,望穿秋水也要回到家乡,从大的心理动机看是客家文化“原乡”集体意识的驱动,从具体的情感对象看,是对母亲罗草花和初恋姚玉珍的牵挂。刘求福的还乡也是对伦理和道德原则的回应——回应作为儿子、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为了突出这种情感取向,小说有意从外部环境“制造”了诸多困难和矛盾,包括男女双方遭遇的各种物质和精神的困难、诱惑。这是文学的“曲折”。
在刘求福的还乡中,我最欣赏最后一笔。经历种种曲折回到家乡的刘求福,看到年老色衰的姚玉珍,第一眼是意外和失望。这种情感经验的表达,忠实于现实生活,是贴切的。30年不见,对女方的记忆还停留在青年时期,用记忆咀嚼时光的刘求福,掺入了强烈的主体愿望,对于人物的形象和双方关系产生了特殊的美感。留在家乡的姚玉珍既串联了30年的历史动荡,又串联了客家具体而丰富的日常生活。但时间本是无情物,加上遭遇各种生活动荡,姚玉珍的容颜体态必然“惨不忍睹”。刘求福情感发生起伏是一个正常人的正常反应,能够看到并表现这种起伏,是作家现实主义写作精神的锐利和高明。怎么处理这种起伏,故事走向哪里,是作家的价值立场的体现。小说的结局是,一家三口认亲并团聚,这种处理基本上符合人物性格逻辑、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克服种种困难最终还乡的刘求福,其儒家文化底色驱使他在义利之择中选择义。这个底色也是作者的价值底色。
刘求福二弟刘求禄身上的无情、冷酷、自私,寄托了作家对人性中恶之极致一面的批判。饶是这样,小说还是写到了刘求禄和妻子高盼枝之间的温情。作家这么写,源于对现实人生的深刻认知:再恶的人也有自己的生活,也有爱人,他们甚至会被传统意义上的好人爱上。不过,抛弃母子情谊和兄弟情谊的刘求禄,折腾来折腾去,最终也没有从生活中格外攫取到什么,晚年依然踉踉跄跄地生活。在刘求福的另一个弟弟、知识分子温求寿身上,作家寄托的是坚忍、善良和责任的道德高点。通过兄弟三人最终结局的描写,作家动用文字表达了价值判断——善恶有报。
很多作家的短板是生活积累不够,而对缪俊杰来说,庞大的经验库存也部分地伤害了小说的叙事节奏,如果能够删减掉一些枝蔓人物的篇幅,在主要人物的细节描写上多花费一些笔墨,小说的结构会更加清晰突出。至于小说中关于客家历史和文化的种种描写,看似闲笔,却妙在丰厚,是我所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