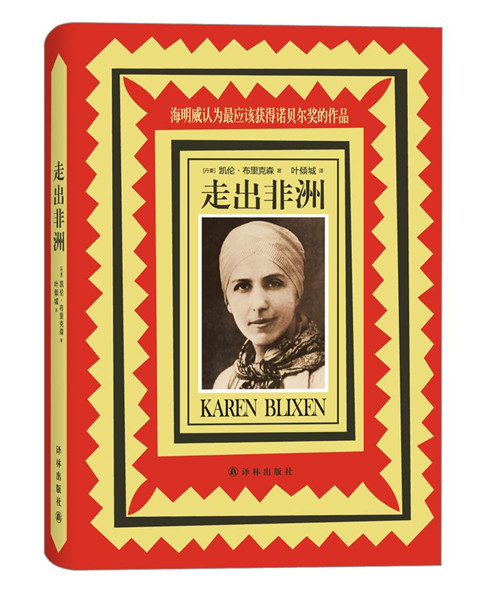
《走出非洲》
当上帝之手在地球上划出海沟,当气候、植被、走兽昆虫分置于每块大陆,当火焰、文字、神话传说产生于各个族群,当文明、社会、工业科技日益发展直到今天,你能说哪一片土地里没有古老的根须、人类的骨骼、永恒的苍凉与庄严?若你只是过客,它们展示给你的便只有浮光掠影。若你把身体俯下去,脚印踏进去,心灵完全融入其中,自会知晓那每一片土地都浩瀚如星空和海洋。就像一百年前,凯伦·布里克森的非洲生涯。
初至非洲,凯伦·布里克森带来的是花花世界里精致的水晶、瓷器,以及对奢华的追求,对男爵夫人头衔的热衷,对殖民地贵族生活的憧憬。走出非洲时,她却是孑然一身,丈夫离去,情人已逝,咖啡园付之一炬,丈夫传染的梅毒导致她不能生育——此后独自生活在丹麦庄园里的凯伦·布里克森,直到古稀,直到老死,都处于中国古代故事里杞梁妻所哀叹的状况:“上则无父(凯伦十岁时父亲即去世),中则无夫,下则无子,生人之苦至矣。”然而她并没有杞梁妻的怨艾痛哭,三十多年间,她安静地回忆,写作,出版,《走出非洲》更是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名著。
是非洲大地,是壮美的山川、广袤的草原、恩贡农场上的风,是黑肤黑眸的非洲人和他们可爱的孩子,是狮子、瞪羚、野牛、大象、长颈鹿、犀牛……这浩瀚的一切,须臾未曾远离,长久陪在她身边,抚慰着她的心,一如彼年内罗毕城外她的青春岁月。“如果我通晓一首非洲的歌,一首长颈鹿之歌,新月之光落满它的背;一首田地犁铧之歌,咖啡收割工们汗湿满脸;那么,非洲知道关于我的歌吗?当风掠过,旷野是否因为一抹我穿过衣服的颜色而颤抖;孩子们能否发明一种新游戏,用我的名字命名;满月可会将一个酷似我的身影投在车道的鹅卵石上;而恩贡山上的鹰,是否会四处将我打寻?”
《走出非洲》一向被认为是凯伦的自传体小说,我更愿意称之为自传体长篇散文。因它太散文化,节奏缓慢,不以情节为主,不以塑造人物贯穿始终,笔触更多的是落在非洲景观和风俗人情上,若非译者代序及译后记的交代,读者甚至未必了然文中人物关系的起承转合。各个篇章散落开来,一头瞪羚即可独立成篇,一场舞会也可曲尽其致,一次散漫的出行狩猎都可以成就讲述,记忆在吉光片羽里温厚存贮,人性在交际遇合间磨洗闪亮。读来不会失望,反倒常常不知不觉就流连其间,沉醉不知归路,蒙昧与文明的界限并非以为的那么明显,他者与我者的相知相惜远比预料的来得快,而爱与不爱、婚与否、生与死也终于释然。
这样的文字,适合女性来读,适合能读懂它们的女性来翻译,还必得是一个善于表达、体察入微、妥帖尽情的女性。叶倾城就是这样一个译者,凯伦·布里克森遇见了合适的转述者。叶倾城的译文,语言干净、清新、明澈,无有赘疣,不落俗套,表现原住民对话的俏皮处也便俏皮,表现非洲生活的朴实处也便朴实,表现狩猎冒险的奇崛处也便奇崛,偶或还有一些极为符合原著情境的古典语词自然跳脱出来,并无违和感。
中国读者阅读外文译著,常会觉得不足:要么是翻译功底不够,如北方人听客家话一般,明明是中国话却越听越不知所云;要么是写作功底不够,译文语言生硬,如隔夜的凉粉块搁在胃里不消化。既能译得准,又能转化得好,让中国人读之如读本土著作,且不失异国写作风格的,在国内恐怕只有寥寥数位翻译家能做到吧。叶倾城是一位作家,有得天独厚的写作优势,此前未曾见过她的译著,若这是第一本的话,可以说是开了个好头,中国读者大可以放心购买阅读。
如果凑巧,读者还看过根据这部书改编的电影《走出非洲》,1986年奥斯卡金像奖中一举捧走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配乐、最佳摄影、最佳美工、最佳音响七项大奖的大赢家,那就更好了。当然,现在去看也不迟。在优美舒缓的音乐声中,红日晕染下的浩瀚非洲渐渐拉近,“一切你眼中所见,都生而庄严自由,有着难以想象的尊贵意味”。这时候,一个苍老的女声开始了悠悠的讲述:
在非洲的恩贡山脚下,我曾经有一座农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