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我说出了中国老百姓的肺腑之言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4:11:46 青年作家杂志社(微信公众 刘震云 宋宇 参加讨论
 刘震云,著名作家、编剧;1958年5月生于河南延津县;1973年入伍服兵役,1978年复员,在家乡当中学教师,同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 年开始文学创作,曾为“新写实主义”代表作家;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塔铺》《新兵连》《一地鸡毛》《官人》,“故乡”系列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故乡到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以及长篇小说《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等;《塔铺》获1987-1988 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一句顶一万句》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8 年,被法国文化部授予“法兰西共和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生活停滞的地方,文学出现了 宋宇:在《吃瓜时代的儿女们》里,您写到了“吃瓜”这件事的正面和负面影响。您自己对“吃瓜”有没有一个基本的态度? 刘震云:首先我觉得它当然非常好。互联网出现,微博、微信出现,最大的一个时代进步是把发言的权利还到了每个人手上。没有互联网的话,可能报纸说什么、电视台播什么你才知道什么。现在明显可以发现报纸、电视台的语言和互联网的语言是两个语言系统。就好像宋朝有官方的语言,但是林冲见了鲁智深,或者是武松见了孙二娘开的那个饭馆,他们之间说的是江湖语言。互联网有点像江湖语言,所以老说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低头族”,要他们把头抬起来。但我老是想说,既然那么多人都在低头,几亿人都在低头,手机里边一定有比报纸更有趣、更真实的东西,这是其一。其二,更重要的是,他有自己的发言权,不单是围观。你看那些留言,好多纯粹出于情感,就是一时的感慨。还有很多理性的分析,让每一个人发言,我觉得这是上帝通过互联网,把微信、微博包括朋友圈送给世界的最好礼物。 但这其实不是我写这部小说最主要的初始点。初始点的话,是我觉得“吃瓜时代”能够把不相干的事——它其实是相干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事是不相干的——之间这种特别微妙、不可言说的逻辑呈现出来。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怎么打着的,这比只是幸灾乐祸和乐不可支重要得多。 宋宇:有没有一件具体的事情让您突然发现“吃瓜”这件事,或者“吃瓜群众”的作用? 刘震云:其实故事对我创作的初衷不起任何作用,而且我对这些故事的形成没有太多兴趣。我写作的初始心和出发点、兴趣点仅仅是人物关系,这个人物关系是我过去的作品和别人的作品里没有出现的。新的人物关系一定会说出人类没有思考过的道理。比如我写《温故一九四二》,1942 年因为一场旱灾,河南饿死很多人。但是这件事如果让我写一部作品,我没有太大的兴趣,这样的作品太多了。 但是翻资料之后我发现,饿死人这件事有那么多出发点。有灾民的观点、国民政府的观点,还有美国人、苏联人和英国人的认识,还有新闻界及宗教界的认识。不同的认识聚焦到一件事上,反射出来的是什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这更重要的,是发生了饿死这件事。 像《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四个不同阶级的人,一个农村姑娘、一个省长、一个县公路局局长、一个市环保局局长。四个人不是一个村,也不是一个县,不是一个市,也不是一个省,就他们的阶级而言,可能这辈子不会有任何联系。省长到村里视察,顶多问问你家里几口人,今年收入如何,无法跟你发生特别紧密的联系。那么紧密、性命攸关、非常可笑的联系,在“吃瓜的时代”突然形成了。 恰好这种人物关系是我过去的作品里没有写到的。过去我作品里的人物关系,是相互紧密的这些人,比如说小林说过一句话,人要想活好,把身边的几个人对付好就可以了。身边的人都是认识的人嘛。像《温故一九四二》是灾民之间的关系,包括跟国民政府的关系,都是可见的。《一句顶一万句》里也是牛爱国和杨百顺与身边人的关系,《我不是潘金莲》也是跟不同关联的人打交道,她怎么告状,这些官员怎么不让她告状。这些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是显性的。而隐性的关系我过去的作品里没有写过,这对我有吸引力。 宋宇:这种吸引力是怎样产生的呢? 刘震云:有可能在生活中它是存在的,比如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新闻,一个人怎么成了一个从事某种行业的人,一个贪官怎么会突然就下台了。它并不构成文学作品,因为它只是一个现象、一个事实、一个单独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这些人物背后形成的逻辑,包括一件事跟另外一件事的“蝴蝶效应”,反过来就是对这些人物包括灵魂的触及,这是文学作品所关注的。 文学作品把生活中孤立事件背后的联系,那些逻辑和逻辑背后隐藏的,大家感觉到而没有说出来的那些道理和肺腑之言给说出来了。生活停滞的地方,文学出现了。不然的话,你只是写了一个反复出现的题材。我特别不赞成说一个作品是揭露黑暗的,这是媒体、报纸的事,跟文学作品是完全不一样的。好多人说,《吃瓜时代的儿女们》里边的贪官写得特别有人性、特别感人,说我是不是对他们也怀着慈悲之心。我说,现实中的人和文学作品里的人是两回事。现实中的人,你有时候看到的只是他的一个侧面。哪个贪官一岁时会是贪官呢?他也有父母、姐妹,也是在人的温暖、愤怒、排斥、打击、责骂中长大的。  《温故一九四二》 作者: 刘震云 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品方: 长江新世纪 出版年: 2016-8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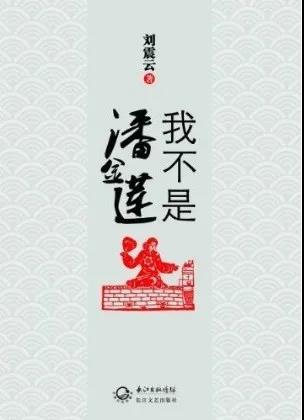 《我不是潘金莲》 作者: 刘震云 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品方: 长江新世纪 出版年: 2012-8 一部文学作品最好的效果,就是越读越厚 宋宇:您最早什么时候真正地关注这样的现象呢?比如,一个人受了这么多的外力,形成了他未来的命运。 刘震云:其实这样的小说我原来写过单个的人物,比如像《塔铺》就是一个手无寸铁的人,生活突然开了一个小窗户。但不是一个人,是成千上万的人、成千上万的蝴蝶想通过这个窗户飞到光亮中去。整个向往光亮的过程,就是他们特别复杂的兴趣和过程,而且是在非常贫穷的一个环境中。像《新兵连》就是一帮原来还在睡打麦场的农村孩子,突然进到了部队和集体。这种环境的改变,对他们的心灵产生了极大震撼和冲击,特别是人物关系的分化。过去在村里大家都是好朋友,但到部队之后它牵扯到一个班十来个战士,不可能大家都入党、都提干。那你怎么表现比别人积极和好?这个“好”引起了人性恶,大家都抢着做好事显示自己,其实那些好事是完全没必要的。你起得早,替宋宇挤了牙膏,这叫好事,他不会挤牙膏吗?都抢着擦宿舍的地,抢着掏厕所,抢着到炊事班里帮厨。班里边不是要定人事骨干吗?骨干得睡到灯绳的下边,谁能睡到那个铺头?分化、仇恨马上就出来了。 作品中四个主人公素不相识,人物关系的这种空白怎么通过一个作品写出来?这是我特别想尝试的,然后就开始写。 主人公过去都是显性的,严守一就是严守一,小林就是小林,李雪莲就是李雪莲,牛爱国就是牛爱国,杨百顺就是杨百顺,但这部作品的主人公并没有出场,它的主人公就是吃瓜的群众,比吃瓜的群众更隐性的主人公是谁呢?就是读了这本书的读者朋友。读者朋友参与了小说的创作,把里边的空白给填补了。吃瓜群众填补了第一阶段,读者填补了第二阶段。 因为书要宣传,所以我接受了一些采访。《北京晚报》的一个小姑娘拿到书的时候,说“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一定写的是吃瓜和围观的事,但是没有这条线。她从下午看到第二天凌晨看完了,她说看着看着就想笑,最后又特别想哭。这证明她已经参加到这个创作里边,把空白给填补起来一部分。到底能填补多少?这就是书要经得起读,也可能读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时会填充一些。 宋宇:我虽然觉得有很幽默的地方,但一直觉得比较沉重,不至于想哭,一直很难过。 刘震云:那证明你可能读出了事情背后的道理,道理背后的道理,所以你感到有些啼笑皆非、笑中有泪,幽默中有特别悲伤和沉痛的值得思考的地方。一部文学作品最好的效果,也是我特别想追求的,但我未必能达到,就是这本书越读越厚。如果你只是讲一个单纯的故事,读完就完了,但是他读完这本书之后突然发现,好像书的内容比这本书要多得多,那就证明它空白处很多。 有一个词我也特别赞成,就是“掩卷叹息”,就是接着会有很多思考。我未必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我还是想这么做。因为这本书出版,我的出版社为了宣传,把国内外对我作品的评价收集了好多,包括美国的一些报纸,以及俄罗斯的、阿拉伯的。我看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书评家叫丰崎由美,她说了一句话,我稍有些触动。她说,刘震云说出了中国老百姓的肺腑之言,这是赛珍珠永远写不出来的。后半段跟我无关,人家赛珍珠得过诺贝尔奖,写过《大地》,但她是一个美国人。她说,我说出了中国老百姓的肺腑之言,我确实想这么做,不知道我做到了没有。 宋宇:我觉得牛小丽不应该受到这么严重的惩罚。她在乡村应该是个很能干的女人,她犯的错也不是那么严重,后面让我很难过。 刘震云:好,回头我给她打个电话,告诉她,宋宇老师同情她。但她做一件事,她的选择,包括由一个特别质朴的农村姑娘,最后走到从事那样一种行业,整个渐变过程跟她心理的结合,此情此景下是由偶然到必然的过程。这个过程我觉得不但是发生在牛小丽这样的人身上,也发生在李安邦这样的人心上,他对每一件事情做的选择。他一开始是乡里修理农机的大学生,怎么一步步到达常务副省长,最后到达省长的位置。如果把你放到那样的环境,你经过这样的台阶,能否做到清正廉洁?我觉得它是一个问题。 宋宇:问题在哪呢? 刘震云: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环境。说《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是描写现实的,对不对?也对。但里边有一个极大的空白是它跟中国历史的联系,这个根的话,特别是写到第二部分,写到李安邦,他的所作所为、讲话的方式不是从现在开始的,可能是从秦朝开始的。总是一个人说话,其他都在附和、在鼓掌。 宋宇:您连续出版的两部小说都是以女性角度来写的,也许不能说是主角,但她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线索。是否意味着您对女性有一种特别的关怀? 刘震云:没这么严重,因为我原来的小说,像小林、严守一、杨百顺和牛爱国不都是男的嘛。其实主角是男是女不重要,仅仅因为这个人物关系适应。但是它跟《我不是潘金莲》还是有很大区别,《我不是潘金莲》就一个主角李雪莲,但这部她是四个主人公中的一个。另外,“潘金莲”跟这些人物的关系是可见的、显性的,而这里是隐性的,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宋宇:您自己呢?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她们会承受更多的压力,您会有这种触动吗?她们的命运,或者她们受到不该受的压力等等。 刘震云:男性的压力就不大吗?性别本身会是有的作家的创作出发点,但是我觉得局限在这个层面,是不是稍微浅了一些? 宋宇:当然,因为我们提到作家的同理心。比如说她们犯罪,这属于法律调整;但是作家就是要看到人性,而不对她们做一些评判。 刘震云:审判一个人是法院的事,不是作者的事。审判一个人是生活中的事,不是文学作品的事。就像你说的《安娜·卡列尼娜》,包括玛丝洛娃,她们的人物形象、人物内心,一定比现实中一个卧轨的妇女、富婆里边一个从事“第三产业”的妇女要丰厚和丰满得多。这是一个作者把生活深处蕴含的复杂性给写出来了,是他应该做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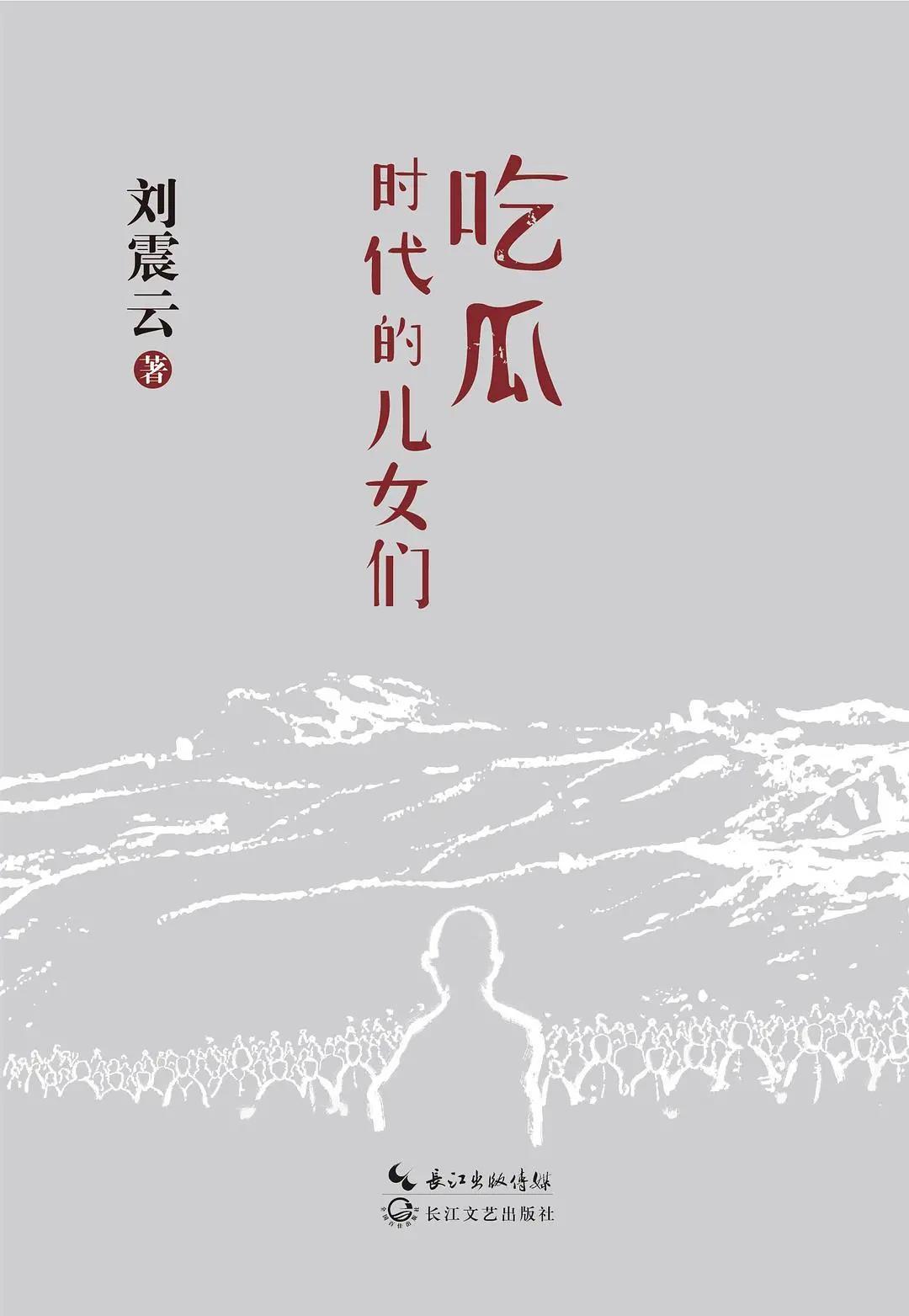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作者: 刘震云 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品方: 长江新世纪 出版年: 2017-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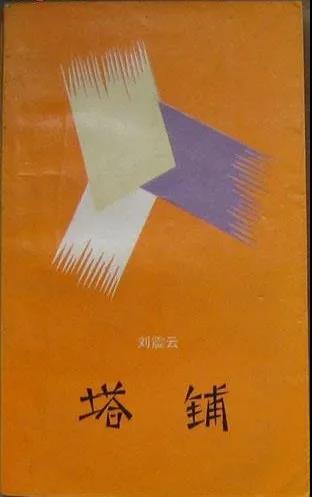 《塔铺》 作者: 刘震云 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 出版年: 1989 用泪眼来看这个世界 宋宇:有意思的是,您作为作家、作者,相比只能看照片或听流言蜚语的“吃瓜群众”有种好处,就是上帝视角。您的写法又比报纸更加丰富,这可能是您的一项“特权”吧? 刘震云:没有,我从来没有用过上帝视角来写自己的作品和看待自己作品里的人物。我的视角只有一个,没有作者视角。有谁的视角呢?人物的视角。包括语言的运用,因为它写了四个不同阶级的人物。牛小丽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写牛小丽时基本上用的是乡村语言,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是以一个朴实农村姑娘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这里边捎带的叙述语言必须跟她贴合。当你写到一个省长,语言环境马上变了,他们老开省长的办公会,老下去视察,一到市的边界,市长、市委书记都在那儿等着。他下去跟人握握手,到了县界又有一帮人在那儿等着。他们说的好多话确实有政治含量、社会含量,当然也有知识含量。当然,写到一个县的公路局长,他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又跟省长不一样,他是县级干部的语言环境,市环保局局长又是另外一种语言环境,把握必须要准确。 宋宇:您需要对此做功课吗? 刘震云:功课应该在日常,你要写一部作品,临急再抱佛脚,急病乱投医,我觉得早已经晚了。我有一个笨习惯,口袋里总有一张纸和一支笔,别人讲的话,我见到一个对我特别有触动的细节,就把它记下来。自己突然有一个想法,我要把它给记下来;宋宇说了一句对我有启发的话,我还记下来,宋宇并不知道。夫子说过一句话,一开始我理解得不是特别深,“三人行,必有我师。”你在日常生活中会突然发现这些知识点、思索点、哲学点,有时是一个细节,成了你的触动点和感动点。 宋宇:这部小说您有没有一个具体的触动点? 刘震云:真正面对作品,个别的触动点一点都不管用,没用。只是说这个人物关系,我觉得四个不同阶级的人,八竿子打不着的事,越过大半个中国打着了,我觉得这个特别新,不是“吃瓜时代”不可能产生。这个“新”也特别“旧”,人物关系的根可以搭到中国长远的历史里边。人物的这种架构,现实跟历史的架构,这样一个整体轮廓吸引我。好多作者或者编剧会说一句话——“桥段”“有几个桥段”。这些都是傻话,你会按照故事的走向安排你的人物的行动足迹、思想脉络、人物关系之间的逻辑。 所以有时我们看一些作品,这事它不可能发生啊,但是它就发生了。谁让它发生的?作者或者导演。他冲功利性的桥段,有几个这样的桥段。我觉得这种创作方式特别落后也特别浅显,特别傻。真正的还是人物想干什么,你必须尊重他。一个作者要尊重自己的读者,首先要尊重作品里的人物。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哪怕是一个贪官,不可能生下来就是贪官,他有非常复杂的经历,有非常复杂的情感。像牛小丽由一个纯朴的农村姑娘到从事“第三产业”,你能说她是坏人吗? 宋宇:当然不能了。 刘震云:可能从生活和社会、法律的层面是,但文学作品已经透过了这些层面,到达了人性的包括灵魂的、自我挣扎的层面。 宋宇:牛小丽从乡村到省城到邻省,又到了更大的城市,遇到那些比她阶级更高的人就束手无策了。她做判断、做选择时感觉很惶恐。 刘震云:她没有选择。她回去还可以当纺织工人,一个月一千八百块钱,那什么时候能够还这笔高利贷呢?另外,就是社会的挤压感,挤压感是各种阶层给的。包括说中国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是从哪来的?就是牛小丽这样的人。总不是像很多商人做概念,卷走几十个亿做出来的吧。 宋宇:在小说里,几位重要官员、一些事件,像“微笑哥”“表哥”我都可能跟现实生活联系上,但还是牛小丽最让我牵挂,这个人物是否有一个稍微具体的原型? 刘震云:里边的这些事件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一些影子,但我是有意引用这些影子。为什么要引用它?因为它不重要。它只是作品里的一个细节,并不起主干和结构的作用。如果它起主干和结构的作用,我就不用了,那证明我很没有想象力。只是细节,而且它俯拾皆是。我借着顺手牵羊用上,因为这几头“羊”大家都见过,会增加这个作品的真实感。其实增不增加真实感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事件背后的道理。就好像《温故一九四二》全是真人真事,但我不是冲着真人真事去的,而是最后提出来比真实更残酷的一个问题。 包括《红楼梦》,乾隆看完之后想到,这不是明珠家里的事吗?它是不是明珠家里的事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写《红楼梦》的时候,它已经变成一块石头和一株草的故事,而不是说明珠家有多么衰落。重要的是,这块石头和这株草来到人间,是什么样的命运变化。我猜想,曹先生写作的出发点是当初女娲补天剩下的一块石头,就从这儿过。那草就有点像《温故一九四二》里发生干旱,快死了,他不是给它浇了点儿水,它不就活了嘛。接着草就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是整个《红楼梦》特别重要的一个出发点。谁对我好,我一般说怎么报答你们呢?下辈子做牛做马报答你们。这株草说,下辈子我用眼泪来报答你,这是非常重要的。用泪眼来看这个世界,我估计这是曹先生写作时突然有电流触发的一个感觉,不是说有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在《红楼梦》中,这个草的眼泪从来没有停止,而且她是介入者,并不是四大家族的人。爹娘早亡,来到姥姥家,寄存了一株草。它是作者的思维,也是伟大作者的思维,并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四大家族的衰落史。 他们做的事都是情有可原的 宋宇:写这样一个故事,您会不会有一瞬觉得于心不忍? 刘震云:于心不忍的话,除非你用特别卑劣的心态写这个作品。 宋宇:“卑劣”该怎么解释? 刘震云:用卑劣的心态,作为一个作者我从来没有产生过。我特别尊重作品里的人物,甚至超过了尊重作者本身。举一个例子,《红楼梦》唯有一点我读得稍微不舒服,就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也是一个介入者,因为她一个农村老太太没吃过好东西,所以茄子经过那么多的过程,油炸接着蒸,接着又是压渍,又是煨。在她眼里,这不是茄子,村里的茄子不是这样子的。她是一个老太太,为了讨另一个贵族老太太的欢心,贾母嘛,王熙凤、鸳鸯这些人给她插了满头的花,而且把她给灌醉了。接着让她作一首诗,吃多了、吃撑了,她起来就说了一句话:“老牛,老牛,食量大如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这时候所有丫鬟、小姐笑得都直不起腰来。他在写这个场面的时候,是抱着一种欣赏的态度。我看着是有点于心不忍,一个农村老太太,关键还姓刘,我们刘家被你们这么嘲笑。 但《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没有出现一个这样的,对人物抱着调侃、挑衅、嘲讽或者欣赏的态度,没有。他们做的事都是情有可原的。 宋宇:牛小丽离婚找的是老古,《我不是潘金莲》的李雪莲也找了一位老古。这两个老古,我们可不可以认为是一个人呢? 刘震云:这可能是人物结构跨越作品的一个调皮的表达。因为那里边管离婚的是老古,老古说我不但管离婚,还管结婚呢,全镇的离婚、结婚都是我管的。都是一个作者写的嘛,所以借用他一下,我觉得是一种向老古的致敬吧。在《我不是潘金莲》的正文第三部分,我还写过一个县长最后变成了开饭馆的小老板。他到北京来,春节回不了家,找不到票。他用了李雪莲的办法,就是要告状。所以有两个辅警,用警察把他送回老家,一个是老董,一个是老薛。我这是向施耐庵先生致敬,押送林冲的一个是老董,一个是老薛,我借用他们两个一下。我给他们俩打了一个电话:最近有时间吗?再押送一个人如何呢?所以他俩就去了。我觉得这是一种闲笔,谁看出来了呢?像你比较细心,你看出来就看出来了,看不出来也无所谓。能够看出来的人还不多。 宋宇:牛小丽遇见苏爽时,我心想千万别是个人贩子,怕您一狠心故事就不可收拾了。 刘震云:我不是那种人,是故事里人物的走向,而不是作者让她干什么。还有整个时间跨度牵扯小说的结构。这一章就这一句话,说一年过去了。那是因为上一章疾风暴雨、波澜壮阔,突然出现“一年过去了”,一是给读者喘口气,还会显示结构的力量。这一句话一页白纸,一页白纸里就这一句话的力量,还有起承转合的力量。 宋宇:说到结构,有一点特别好玩,办案人员审省长、副省长。后来牛小丽审问她老公,我就突然联想到之前的那个办案,两件事对应上了。 刘震云:它是结构上的另外一个映照,一个场面是这样,另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事物和不同类型的人物关系又出现了同样的场面。我还特别有意的,好多段落的句子是一样的。杨开拓干渴的程度,头发马上像干草一样要着火;牛小丽审她丈夫的时候,也是她丈夫干渴的程度,像有好多虫子在吸吮他身体里最后一点水分。这是另外一种结构,有时候对作者的挑战和考验是非常非常大的,结构最考验作者对人物关系的理解能力。把故事写好,把“桥段”写好其实都特别容易,但就像有的人长相似的,要说他眼睛长得也不错,鼻子、嘴也行,腿、上身也行,但组在一块他不行,松松垮垮。有的人写的东西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整体的整合能力比较差。其实整合能力对各行各业都特别重要,最考验一个人对这个事情的理解深度以及把握能力。 还有一种,你看到他虽然想这么做,但很吃力,就证明他还是干点别的好。有的作者也想幽默,但你一看,他的幽默挺费劲的,你都替他着急。其实真正的幽默是不幽默的,是事情背后道理的幽默,是事情背后道理的联系的幽默。 宋宇:用文学的眼光看,抛弃了不同的阶层、具体的情境,作为人来讲,他们的命运可能是非常类似的。不管因为什么,都会遭受那种干渴、那种诀别。 刘震云:在时间的长河里边,这种阶层、阶级的分别确实是短暂的。有一句诗写得特别好,“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平遥那种一个院落套一个院落,就像牛小丽在作品中那个郊区似的,现在都改成旅馆了。你以后还可能感到在月亮下边,当初这个大家族的笑语欢声。阶层、阶级是一时的,时间还是公平的。不管是谁反正总得死,说人年轻,这个概念很短暂,年轻也很短暂。我平常说他们老是用这个来划分族群,什么00后、90 后。好像他们引领和代表一个新的时代,我觉得这话都特别扯淡。比如清朝有一个人特别新潮,那就是曹雪芹,他的智慧已经穿越了时光。多少00 后的想象力能比上曹雪芹、李商隐,比上孔子、庄子?拿这个说事,拿这个划分,我觉得是一个违反真正常识的“常识”。 宋宇:提到时间,作为读者,我就特别害怕小说或文艺作品里一年过去,甚至发狠十年过去。我非常害怕这样的描写,这一句话里藏了多少事情。 刘震云:它里边会有好多空白。 宋宇:您提到干渴,我印象很深的是牛小丽跟丈夫临别时候的接吻,一嘴血,特别悲壮,真是要离开了。 刘震云:你看得很深入,我一定打电话告诉牛小丽,一定转达。 宋宇:一定要告诉她,让她好好改造。她确实是个令人牵挂的人物。 刘震云:我写这个作品,其实最主要的用意就是读者的介入感。一些看过的朋友的介入感,确实比我以前的小说要深。为什么呢?因为主角就是他们,我特别怕写出来大家漠不关心。现在看,读过这本书的朋友确实有主角感,主角跟里边人物命运的联系感,他们的思索超出了我的想象。 宋宇:还有一点,为什么比较大的地名您都用XX,而不是虚构一个省名? 刘震云:确实会有现实困扰。在我写《温故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的时候,我不想让文学作品特别受现实生活干扰甚至困扰,被另外的因素介入。比如牛小丽是哪一个村的,是真实的县就很麻烦。所以凡是XX的,我觉得还是请读者的创造性把它填补起来。我写《一句顶一万句》用的是真实的延津,好多喜欢这部作品的朋友,其他省的都会到延津去看一看。我写过延津的两条河,一个说县城的河浩浩荡荡,由西向东流去,有一座《清明上河图》那样的桥,上头有好多做买卖的。去了的人一看,这县城里根本没有河。我还写了我们村庄后边也有浩浩荡荡一条大河,河两边长的是两人才能搂抱过来的那种柳树,百十株大柳树。在那下边摆一张桌子,大家吃过饭、喝过酒,凉风一吹酒性又起。可是到我们村一看,后边就一河沟,水还污染了。他们跺着脚说骗人。当然,这可能有点玩笑性,就是说文学跟生活的区别。像写《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这样的人物,还是让他属于全民族比较好,XX 代表全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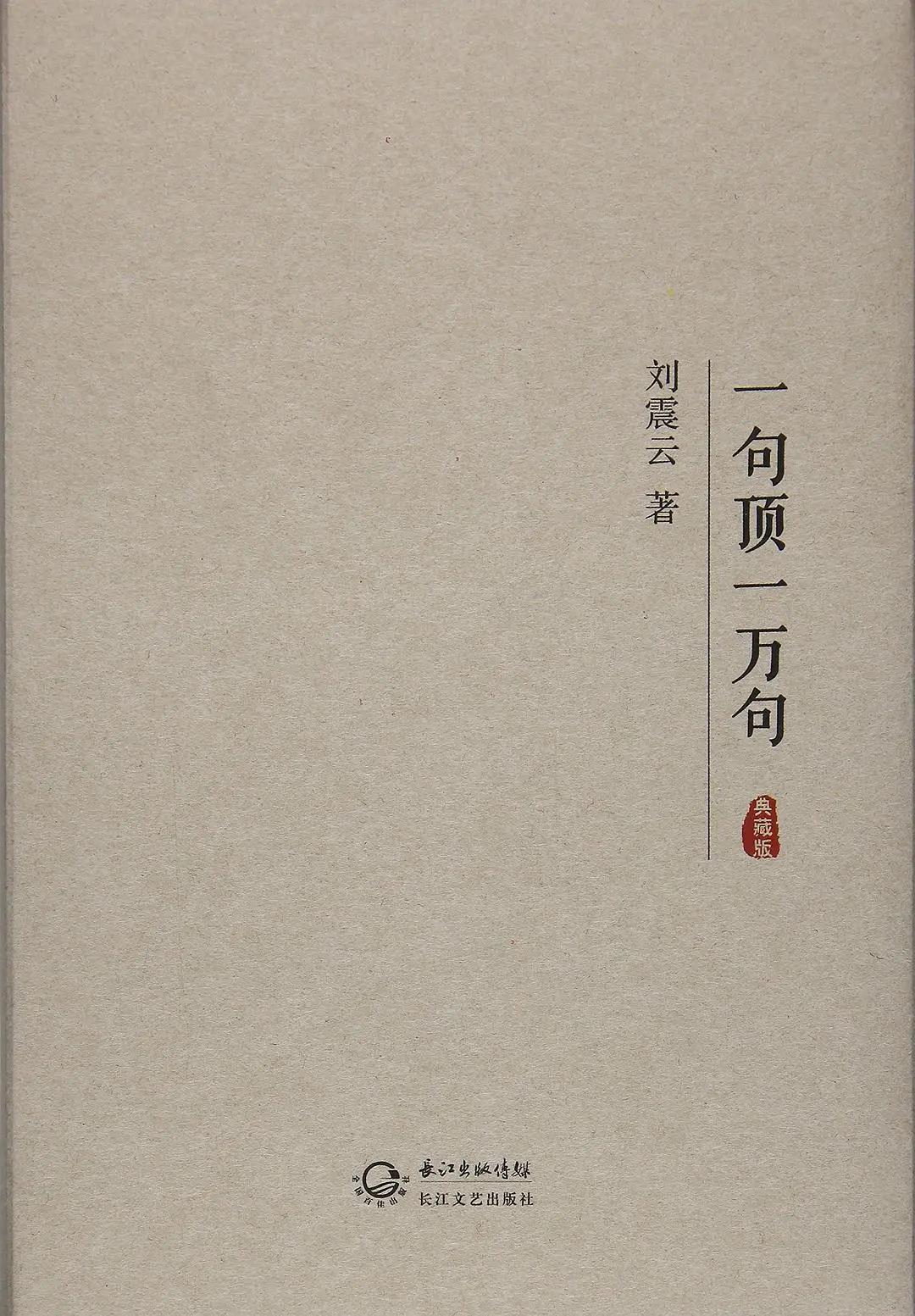 《一句顶一万句》 作者: 刘震云 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品方: 长江新世纪 出版年: 2016-8 宋宇:那我从头来问,您近来读一些什么作品? 刘震云:我开始重新读一些经典,这些经典我上大学时都读过,当然后来也读过,我最近写东西之余也在读。一个是文学方面的,最近我重新读了福克纳,还有莎士比亚,还有一些哲学经典,康德的、尼采的,还有维特根斯坦的。除了文学,我喜欢读哲学,哲学里面是在讲道理。有的讲得不一定对,起码证明他是这么想的。 宋宇:您主要读的就是这种西方的大家吗? 刘震云:没有,前一段时间我集中又读了一遍唐诗宋词。像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确实是特别大的文学家,像苏轼、李清照都特别好。像苏轼写过“大江东去”,还有一首词是看到一条小溪,他发了一下感慨,说一条河由东往西,为什么人的青春非要说直至衰老呢?包括李商隐,有一首诗我觉得别说是中国文学史上,放到世界范围内都是超类绝伦的。“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四句诗里有三个结构,一是他在蜀地,洛阳的妻子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说不知道。巴山夜雨的状况是秋雨连绵,池水不断往上涨,特别期待在洛阳跟他妻子一夜一夜说话,过去是剪这个蜡烛。说的是什么呢?正是现在“我”在巴山夜雨这种生活的境况和心情。一个是现在时,一个是将来时,将来时说的是现在时,这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这时候他妻子已经去世了。这是三个结构,想象妻子还在洛阳,想象妻子还问他什么时候回来。我觉得这二十八个字,从文学结构上讲是非常伟大的诗。 宋宇:小时候读的书,有没有哪本一直留在您心里? 刘震云:我老学不会,因为我出生在一个特别小的村子里。过去村子都没有学校,突然来了一个孟老师。你看《一句顶一万句》里面有一个孟老师,他带着老婆在这里创办一个小学,把村里所有的孩子聚拢来上学,有的都十五六岁了,我当时五岁,你不赶上这拨就没了,所以开始上一年级了。他们都能学会,但我确实学不会,我坐在第一排,因为个矮。我回家以后老问外祖母这个字怎么认,我外祖母也不识字,所以我们俩在那共同看着字为难。然后外祖母说,咱俩研究一晚上,也研究不出来这个字姓张还是姓李,要不然你睡吧,当时我为难得老哭。第二天,鸡叫的时候外祖母就起来纺棉花。她把我叫起来,说你早上试一试,看能不能把这个字想起来。我觉得挺管用,有时候就想起来了,这是给我最大的印象。 我记得村里的月亮特别亮,有时我在院里面直接拿书看都没问题。三四年级开始,我数学特别好,我特别喜欢看数学书。数学对于我日后成为作者有特别大的好处,因为数学特别讲究严密,你算了三页纸,这个小数点点错了,那就全错了。对于写作,一字一句都要写得特别准确,细致和严密是非常重要的。我考学是文科,当时要考理科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数学我占特别大的便宜,因为1978 年,我数学80 多分,百分制。别人都在社会上颠沛流离,能考十分八分就不错了。所以好多人说当时你作文肯定写得特别好,所以你是河南的状元。我说,不是的,那时候我的数学特别好,结果上了中文系。大家都在写作,中文系的人可不都在写作嘛,我就跟着写了。最后大家都不写了,把我留下了,现在我还在写,就这么简单。我当时要是理科也应该没有问题,现在可能在普林斯顿大学某个研究室领着一帮研究生,这也不错。 宋宇:之前读写您太太的报道,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处细节是,您遇到农民工扛大包经过,您跟太太说,这是您的兄弟,如果当初你们没有从农村考上大学,也许生活就是另一条路,既不像现在,也没有去普林斯顿。我很好奇,你现在对乡村的根有怎样的情感? 刘震云:你把这事说大了,不扯到根上和乡土上。你从小是一个苦孩子,从小就在村里长大,遇到同类会有一种天然的心境。考不上大学的话,我在建筑工地也挺好,因为我数学好,墙怎么砌,木工怎么做,可能也能琢磨出一些小门道。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我从来不认为哪个职业别人觉得高贵,我就觉得高贵。比如说这个人的身价几千万,别人觉得他牛,我不一定觉得他牛。也可能他就是一个骗子,骗子有很多的。建筑工地的人没什么不好的,你觉得他每天很累,他不累,最累的是什么呢?在街上蹲着找不到活的人,想出卖劳动力而不得的人。像老舍先生写《骆驼祥子》,我觉得这一点他体会得特别好。一开始祥子拉包月,收入是稳定的。你上个班,接着是下班,路程也不远,他把灯擦得特别亮,每天要铺一个毯子。最后他变成了在街上像出租车司机一样找活的人,一开始能找到活,祥子还能喝个二锅头,还能吃酱牛肉。可是他的腿脚渐渐不麻利了,就找不到活了。他开始抢活,被同行看不起,写了一个车夫堕落的过程。我有时候想,我会开车,其实我还有一个职业可以干,开滴滴打车。你觉得滴滴司机累吗?只要拉着活就不累,你让我每天上下班接你,弄一个包月,我觉得那也挺好。趁你上班了,我出来再拉个私活。 我的车肯定特别干净,放瓶水,也问候。我觉得没有什么,挺好的。 ……(节选) 刊于《青年作家》2020年第10期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玉珍:我脑袋里有个模糊的宇宙
- 下一篇:陈春成:虚构是我最接近自由与狂欢的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