蕾切尔·卡斯克:赢得好评却失去了自我的女作家
http://www.newdu.com 2025/10/29 04:10:18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 关键词:自我 英国作家 自传体
英国作家蕾切尔·卡斯克算是一位功成名就的女作家了。她已经出版了十部小说和四部非虚构作品,文学杂志《格兰塔》对她青睐有加,称她为20位“最优秀的英国青年小说家”之一,她本人还曾三次入围金史密斯奖终选名单。 但获得荣誉的同时,她也因为在两部自传体作品《成为母亲》和《余波》的言论而遭致猛烈抨击和抗议。其时,她每天早上要骑十分钟的自行车送女儿上学,但为了躲避人行道上吵吵嚷嚷的抗议者,她只得把自行车拐上行车道。  英国作家蕾切尔·卡斯克。资料图 如今出现在公共视野里的卡斯克偶尔开怀大笑,回答观众的质疑还能幽默面对——很难让人想象她几年之前遭受过舆论重创。 那么如今的她如何看待那个处在舆论暴力下的“灵感枯竭期”,无法写出任何作品的自己?又如何看待作家作品和大众目光的关系? 一位女作家想要书写自己眼中的“真实”又要面对多大的阻力? 哥伦比亚大学创意写作副教授海蒂·杰拉维茨(Heidi Julavits)归纳了卡斯克起起伏伏的写作生涯:第一阶段,她的作品语言优雅,思想睿智,包含着英式小说惯有的幽默和讽刺,她开始在文学界崭露头角。 第二阶段是更多的自传体作品。大女儿诞生后,她开始记录养育子女的最初体验,写了回忆录《成为母亲》。在这之后,她相继写了四部小说和一部旅行游记。这其中,有些作品给她带来了争议甚至是诉讼。 2012年出版的《余波》是她写作生涯的分水岭。这部关于离婚、夫妻矛盾、争夺子女养育权的作品出版后,有诋毁者开始抨击卡斯克的人格,称她“自我沉醉”、“自恋”,也批评她把家务事抖进公共视线。 在《余波》之后,她进入写作真空期,因为她无法找到合适的文学体裁,能在表达观点的同时,免于舆论伤害。 而第三阶段由《边界》的出版为起点,卡斯克创作了带有自传体性质的小说。她摒弃了以往使用的小说和自传体裁,开始了新的尝试,作品也收获好评。 《成为母亲》带来耻辱 面对《卫报》的采访,她曾说“创造面向大众目光的东西,总会带来耻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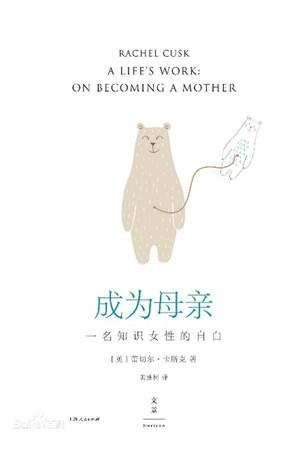 《成为母亲》便是一个例子。初为人母,卡斯克在书中讲述了生育给她带来的身心变化,也通过生活点滴来反映养育孩子的琐碎劳作和巨大责任。《成为母亲》的确如实描绘了卡斯克在“成为母亲”过程中的第一手体验,但这份诚实打碎了大众眼中理想化的母亲形象。 生育猝不及防地让她认清了生活的真相,让她看到过往生活中虚假和多余的东西。她把精力让给了女儿,不再能够自由地支配时间,也照着社会的要求悉心照料着孩子。 一旦偏离了完美的母亲形象,她就会听到他人的贬低。她仿佛被困在一个未开化的世界,她的自我就这样被磨平了。 这其实不是她个人的孤立的体验,数以万计的母亲们也有类似的感受。这是母亲身份带给女性的桎梏,她们有着同样的命运,却没有人将其书写下来。于是,她觉得自己要站出来,为母亲们发声。 然而,《成为母亲》出版后,读者的误解接踵而至,其他母亲也抛来了批评。人们开始对她指指点点,她一时无法接受,她在写作中曾得到了缺失的平等和共情,如今她的作品却招来众人的攻击。她经历了“人生中最糟的事情之一”。 卡斯克忍不住发问,这么多女性明明遭受着同样的煎熬,为什么没有人把自己的心路历程记录下来?为什么完美的母亲形象其实是女人的牢笼,而其他女性一直都在迎合、延续这样的形象? 为什么没有人尝试挑战社会的刻板认知,没有人试图解放母亲?! 她把自己受到的指责归因于大众心理,对约定俗成的异议是不受欢迎的,对刻板印象的质询是被忽视的,所以女性们选择三缄其口。她们看到了多数人的暴政——把个体经历作为证据来讨论母亲形象,只会让个体暴露在聚光灯下,让个体变成被攻击的靶子。 她认为,批评她作品的同为母亲的读者,她们只想在既有的性别框架中生存下去。她们照顾着自己的子女,只是想要得到社会的认可。而卡斯克对于母亲形象的反思中,母亲有着独立的人格,不再屈服于社会的要求,不愿一味地牺牲自我。她们认为卡斯克在污名化母亲形象,因为她笔下的母亲不再是完美的,那她们所做的努力就前功尽弃了,社会不会再继续褒扬母亲的无私精神了。 卡斯克认为,为了维持自己的完美形象,她们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开始漠视自己和其他女性遭受的磨难。她们开始说谎话:成为母亲是一种荣幸,母亲的角色让她们完全满足。 她们把不同的声音看作是玷污自己完美形象的危机,继而开始对卡斯克进行人身攻击,批评她的体验是异常的,是她自己的人格有问题,是她不够有爱心,她厌恶儿童。 就这样,本来能代表全体母亲体验的控诉沦为个人的抱怨,卡斯克作为发声的个体开始被妖魔化。同为母亲的人们忘记了自己也曾经历过同样的痛苦,她们的倒戈让“母亲的解放”失去了可能。 个体经历与社会运作之间有很大的摩擦,社会的运作赋予了母亲养儿育女的集体责任,它要大于女性对于自我的个体追求。正是由于群体高于个人的社会文化才带来了人们对于真相的逃避,在集体责任的重压下,女性很难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 “我已经没有了自我” 《成为母亲》和《余波》之后,卡斯克的生活和工作被混为一谈,对她作品的评论成为了对她生活的指指点点。她的婚姻和家庭生活登上了报纸,成了广播节目。她不再能把自己的个人生活撇开,专注于写作。 这些书评中也有显而易见的矛盾。比如,它们一边斥责她为何要把自己的私人生活公之于众,一边又批评她没有给出足够的细节来体现真实。 她一直遭受着外界炮轰,作品被政治化的点评淹没。英国的文学环境厌女、老派、传统,对她的支持不够。她一边要面对外界的挑战,一边要照顾她年幼的孩子。 一开始,她还能斗志昂扬契而不舍地尝试书写自己的生活体验,而读者和评论家也继续他们的批评。 但是渐渐地,她开始厌烦这些评论,也开始更加小心地发言。她只是感到不解,很多时候作家只想要对一个问题发表一点不同的看法,但他人却会把它看成对于自己的侵犯,是对他们个人的攻击。 卡斯克不理解,为什么仅仅因为她的“真实书写”与人们对于女性的期望不符,外界就把她的写作看成是一种对于社会的批判,深深的无力感包围了她。 究竟如何通过个体的写作去代表群体?她陷入了长久的困惑和矛盾之中。 她很想把个人经验和公共知识连接起来,也做了许多尝试,发表了多部自传体作品。但是,她意识到这两者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异,无法互相越界。私人体验得到的知识,一旦进入社会空间就不再是私人的,也被期待要能代表群体体验。 卡斯克把自己当作样本,尝试延伸出集体的真相。她“不留情面地进行着自我审查”,但同时对自己又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只是把自己看成是茫茫大众中的一个例子,通过反思自我来揣摩群体的问题。 她甚至说,相比爱自己,她觉得自己更爱他人。她把写作的快乐归于对他人的共情,在创作时,她能体会他人,了解人们的真实生活,她认为这是写作对她的馈赠。 卡斯克在当代小说中看到了类似的矛盾。很多作家的作品大多脱胎于私人体验,却不可避免地触及更加公共的话题,或是议论社会问题,或是谈论作者之外的其他人物,谎称了解公共知识,装作能代表大众。 卡斯克意识到社会的言论空间是很有限的,她质疑,话语权不能集中于白人男性,甚至白人女性。当作家习惯于借自己的体验为他人发声时,其他人可能就永远没有机会说话。 认识到这点后,卡斯克开始寻找挖掘社会真实和尊重他人体验的写作方式。三部曲的第一部作品《边界》就是她长久努力的结果,得益于作品特殊的体裁,她终于能放心地在个体写作中描绘和演绎他人,探讨社会现象。  《荣誉》里主人公的出版商认为小说读者异常肤浅,都是“没事找事,在寻求打发时间的方式”。满足这样的读者,作品“好笑就行”,无需引人深思,提醒读者看清自己的问题,只需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生活的荒谬。 小说中的这位出版商远非愚昧之人,他早已看穿出版行业的资本主义逻辑,知晓问题的根本。他将资本主义的运作比喻成燃尽时间积累的一场大火,不光消耗着存储的自然资源,也在榨取人类历史中累积下来的知识和文化,用尽一切牟取经济收益。他旗下成功的作家,都在消耗着文化积淀得来的“文学”这一概念,把庸俗标榜成艺术,换取钱财。 既不想局限于自我,又不愿臣服于市场而改变写作,卡斯克的写作严格地扎根于自己的体验,忠于自己认识到的真实。 她确信自己的作品中没有编撰的虚假成分,没有谎称自己了解着陌生的领域。同时,她选择“当只有我的体验和经历能带来不可或缺的社会贡献时,我才会发声”。 卡斯克认为作家和叙述者应该是生活在类似的环境里,这样写作时她能忠于自身经历的真实,不需要过分地捏造叙述者的视角。但是,她和叙述者必须是不同的个体,这样她才不会局限于自己的世界。 我们可以说,卡斯克没有被《成为母亲》的批评击垮,现在的她没有任何畏惧,她意识到自己的写作有着意义,她碰到了大众的痛处,迫使人们面对他们一直以来逃避的问题。 有意思的是,她的三部曲小说里的叙述者是一个没有自我的人。 她透过主人公说道,一个对父母和伴侣言听计从、服从外界约束的人,只有一个虚假的自我,在生活中也仅仅是进行着表演。这样的人并没有活着,而是平静地面对着周遭发生的一切,随波逐流。 最近,卡斯克在路易斯安那当代美术馆YouTube频道(Louisiana Channel)的采访中说道,“我曾受的诘难,都源于我潜意识的流露。我发现自己不经意间就写出了惹恼、侵犯他人的作品,触及人们不愿谈论的话题”。 卡斯克继续说,她发现,个人与集体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两方在争夺如何去书写真实。而她仍然想毫无保留地书写真实,同时诘问他人对于真相的掩盖。 新作得到好评,她也不再是媒体抨击的对象,但曾经的创伤是不可挽回的。 这位女作家说,“我已经没有了自我,我也不想要有一个自我。做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总是会遭受他人的非议”。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沙漠里的作家
- 下一篇:经典重读的价值引领:怎样再读高尔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