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心怡:我就是特别“创意写作”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3:11:38 澎湃新闻 方晓燕 参加讨论
1993年出生的张心怡本科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而后进入复旦大学创意写作专业继续攻读了三年研究生。在90后作家群体中,她可谓是典型的学院派。 近日,她的第一本小说集《骑楼上的六小姐》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澎湃新闻就该书作品的诸多话题采访了张心怡。采访中,当聊到记者曾经按照小说的发表顺序重读过集中作品,她忙问:“那你有没有看出我在进步?”而后,自己叹说,“我就是会很有意识地去训练很多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是特别创意写作”。 以下为采访全文。  张心怡 澎湃新闻:您目前是全职写作还是有一份另外的固定职业?您觉得对于作家来说,全职是一种更纯粹更有利的写作状态还是会比较有压力? 张心怡:我是业余时间写的,毕业以来是在培训机构里面编写写作教材。 全职写作有自己的利弊吧。能有更多的时间思考和写作,这个是很诱人的。但弊端可能是,会缺少对于实际生活面的接触与扩充。我一直觉得但凡涉及“叙事”,里面最为宝贵和困难的东西是对于生活和人的具体理解,而这是阅读经验没有办法替代掉生活经验的地方。就是说有的东西,坐在那里想是想不清楚的,只有去做、去经历、去感受。 我自己是一个很容易自我封闭的人,所以目前从经济上和精神上来说我都需要一份另外的固定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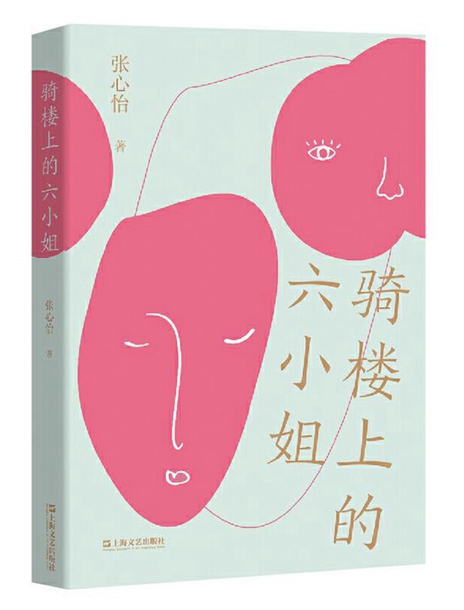 张心怡的第一本小说集《骑楼上的六小姐》(上海文艺出版社) 澎湃新闻:《骑楼上的六小姐》是您的第一本小说集,您在扉页上写:“这是她们彼此知晓的,未曾流出的眼泪。”是否可以理解为,这是对小说里女性之间复杂又深刻的共情的形容?故事里那些母女以及有内心竞争关系的女友彼此之间有疏离、争夺、伤害,同时又在“携手共抗命运”,您是怎样理解女性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在写作上处理这种关系的难点在哪里? 张心怡:集子里的《骑楼》这篇是我的硕士毕业作品,它最开始的名字叫《女性联盟》,听起来有点像个美剧,或者一款游戏。我们课上还讨论过一个题目,叫“女性友谊”。那个时候讲的是友情小说。实际上,我觉得很多女性之间的关系都可以在这个词里面找到激发点,有的时候是某些利益的交换,更多的时候是短暂的理解或者共情,带有很多冲动和感性的成分,很多自我经验的投射。 很感动我的地方在于它有着惊人的生命力。遇到了外部性的挑战和伤害,这种共情就会变成一个稳固型的付出,越是感性,就越活泼而有人情味。会流露出本性中的强大,我觉得类似于一种天赋。《孔雀东南飞》里有一句叫“蒲苇韧如丝”,我觉得是个很贴切的喻体。是在现实生活本身中习得的,以一种缓慢而执着的方式抵达目标,看起来柔弱,其实是在被遮蔽状态下一种生命力的表达和言说。 不过现在大家生活都很辛苦。我如果说女性很辛苦,可能会有失偏颇。你很难用理性的表达来解释这种性别的特殊性。是相对而言的吧,更多的还是一种感性的认知。 困难的话,一个是跨越自己经验的部分,我处理起来会觉得很困难。写作的时候,我比较擅长以小女孩的视角来看老年妇人,我曾经以第一人称写过骑楼三代女性,发现了很大的困难。最后还是换成了小女孩的视角。 我觉得写小说中最难的部分其实是对于人的理解。因为每个人都太复杂了。有时候你和一个人认识了很久很久,突然有某一个时刻你仿佛觉得从来没有认识过她,这都是挺平常的事情。 第二个是要求自己一定要规避掉窠臼的东西。比方说,两个女性在恋爱关系中争夺一个男性这种桥段,是我个人非常讨厌的情节。这让我想起一个写女性友谊的很流行的小说,叫《那不勒斯四部曲》。这小说的叙事很棒,但就是这个点——两个女主人公都和尼诺有感情纠葛,并且还是很激烈的剧情,让我读的时候觉得过于戏剧性,从而失去了生活本身那种很粗粝的真实感。 澎湃新闻:与女性相比,小说里的男性形象好像质感和密度都弱一些,多半在性格上比较孱弱或者自私甚至猥琐,这是小说叙事的需要,还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您对男性的看法? 张心怡:都有吧。我承认我是个对于男性有偏见的人。可能是由于成长经历的影响,偏见已经形成了,并且还挺稳固的,一时半会也改不了,不自觉地会投射在小说人物身上。但这种偏见在小说中是一种观看角度,主要还是存在于叙事时人物的关系中,就不太是一种二元对立了,男性其实有点像某种叙事符号,代表的含义会更大一些,外部世界的某些不确定性,人与人之间的猜忌、隔阂和伤害。 小说中的女性主人公也往往都在花挺大的力气来克服这种偏见,实际上也是一种对于外部世界的不信任感。需要处理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澎湃新闻:之前看您新书的材料,书写福建女性是作为一个标签出现的,看完作品,我觉得女性书写确实是核心,而虽然小说中是写到了包括寺院求签、梨园剧团、客家人、方言、土楼等等,但是小说中的清濛和上海更像是一对并置的意象,我倒不觉得您有书写地方特殊性的野心,对此,您自己是怎样想的? 张心怡:我不会在写作之初给自己设定写什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野心。我写作的动机其实是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奇怪,但我是通过写作的过程来使得问题得以被推进的。 这个小说集里面的几篇,女性人物的名字都有点像,但不完全是同一个人。在出版之前我排过一次小说间的次序,其实是按照人物的状态和对某些问题的认知程度排的。不是聚焦于同一个问题,而是某个生命时期的问题,关于女性自我认知道路上的很多困惑,与他人的关系,与世界的关系,内心的冲突、紧张与恐惧安放的方式,女性之间相互理解和表达爱的方式。就题材而言,当然不会被阅读者认为是青春文学。但是我觉得对于创作者本身,是一个不是生理意义上的青春期创作。 最后的《骑楼》这一篇,第三代女性林裴蕾其实是从前两代的经历与挣扎之中获得了感悟和力量。最开始取名《女性联盟》的时候,我其实是在想,死去的外婆在冥冥之中也能给予外孙女力量,像“幽灵”一样,所谓“幽灵”是中性的,有点像一个贯穿性的意象。她们的经历和性格完全不同,但要完成的道路,总有着某些殊途同归之处。 当然最终也没有被完成。并且,我一直觉得每一篇小说都有它自己的命运。在我的理解里,被发表了、被出版了,就文本本身,也不意味着一个完成了的状态。一方面是读者的阐释会丰富它,另一方面是作者本身的理解也会是一个变量吧。 新书的标签是小说的一种理解和观看方式吧。可能会提醒我,以后是不是可以有意识地去写写这方面的故事。但我觉得还是取决于自己的状态和认识程度。 澎湃新闻:这本小说集里对于继亲家庭的摹写非常集中,而着力点似乎不在于与继亲的关系,而是因为这种家庭结构的变化对于血亲之间关系的影响,能聊聊这个话题吗? 张心怡:可能更多还是因为生活经验。之前有很好的朋友跟我说过,我可以写写我继父。我很认真地去考虑过,才发现我从来没有谈得上了解我继父,因为我一直怀着强烈的偏见来看他这可能也是血亲关系的投射。 这大概是我现阶段看待世界的方式吧,仔细去想想的话其实利弊都有。好处是我能够以自己的视角来划归对于很多事和人的阐释和认知,那种感受很强烈,很容易形成一个虚构层面上的想象和观看。也有弊端,其实我失去了其他的视角,不过,能否获得其他层面的视角,又是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了。 澎湃新闻:您小说有一些空间的问题我也比较感兴趣,比如《幽灵》里面那个储藏室,比如骑楼的门廊和二楼空间,再比如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山魈》里那个母亲每每在上楼去娘家下楼去夫家总要站一站的平台,这些空间是有专门设计过吗? 张心怡:没有专门设计。但是这些空间都有多多少少的原型。写作的时候,它们会从记忆中脱颖而出,来成为被赋予意义的对象,可能也是因为对于当时处境的一种感知方式。至于它们能够被赋予的意义,我想更多的是指向小说人物具体的生存问题和困境。同时空间似乎能够暗含某些转换的可能性,毕竟这些空间都更多地存在于回忆中。 不过我还是很喜欢写“空间”的,似乎空间能够包含很多阐释的可能性。有亲戚读了小说之后对我说,看到我写了很多小时候彼此都很熟悉的空间意象,让她回忆起了曾经的生活。因为情节都是虚构的,空间反而变得很真实,并且能够在一个更大的经验里面“生长”。 澎湃新闻:在《幽灵》《骑楼》等篇中都有一点影影绰绰的鬼魂书写,这一点倒是让人想到福建丰富又强大的民间信仰基础,这在作品中更多地是为了渲染一种情绪气氛还是说有想要隐喻的东西? 张心怡:我想插一点题外话,就是其实福建的民间信仰是特别有趣的。我生活的闽南地区,看到佛就都会拜,不论什么佛一律叫佛祖。我的家乡是泉州,本身就有着浓厚的宗教氛围,奇特的是所有宗教和谐共处,只要“佛祖”这么一个统一的称呼就可以统筹全部了,没有矛盾,大家心里也不觉得隔阂。因为在宗教活动里面的表现其实很淳朴,所以我觉得与其说是对宗教的信仰,不如说是对生活的信仰的一种体现方式。 小说中的这部分内容,一方面,我觉得是作为“环境”的一部分而出现的。另一方面,背后的隐喻内涵可能更多在心理层面上。“幽灵”是一个能够统筹全书的意象,它是在清濛与上海、过去与未来的对照中去引发问题、抵达路径,并且始终在变化之中。《骑楼》里面,死去的外婆仿佛永远生活在骑楼里,这其实是女性之间一种精神力量和生活智慧的传递和支持。我觉得是很温暖的。 澎湃新闻:还有就是您的小说中常常出现一些跟古典文学相关的符号,比如直接用陶渊明、卢照邻为人物命名,然后《骑楼》里庄庄研究庄子,章节名叫“逍遥游”,海风跟林孔英谈王维,再比如《温温恭人》的篇目取自《诗经》,还有一些对传统戏文的使用等等,您个人对古典文学有特别兴趣吗?这些频繁使用的符号有特定的文学意图吗? 张心怡:我比较抑郁的时候,精神上有一些想不明白的地方的时候,古典文学会给我很大的力量。当然,我对古典的了解是很有限的,所以文中的这些相关符号的使用,还是要放在具体的语境中来理解。 毕业后我在一个古典文学氛围很浓厚的地方工作,接触了很多古典文学出身的人。我发现其实他们是共享同一个精神世界的。对于当下的生活,与所阅读的东西,我体会到很大的断裂感。所以对古典文学我很感兴趣。但具体到小说里面,似乎只能提供一种很具体的理解方式。 澎湃新闻:这本小说集的同名篇目《骑楼》,书写骑楼三代女性的命运,尤其是第一代“六小姐”扑朔迷离的故事相当具有传奇色彩,这个故事有否原型?您怎么看待纯文学创作中的传奇性情节,似乎有些创作者会刻意排斥故事的传奇性以作为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某种分野,对此,您怎么想? 张心怡:没有,六小姐的故事是完全虚构的。我对“传奇性”也没什么研究,我更多地可能会把它放到叙事当中来理解。如果要谈谈自己的理解的话,我不觉得是分野,古典小说里面的传奇,现在读起来可能很难被人喜爱,因为要放在一个特定的文化背景与价值体系中来理解。如果用“通俗”来指认的话,我会不太认同。张爱玲最精彩的小说集,重新演绎了“传奇”这个概念,是站在新与旧之间的沟通,还是为现代文学贡献了很美很真实的东西。当代的很多作家,比如说金宇澄、王安忆、苏童、格非等等,都写过很好的带有“传奇”元素的小说。一个是叙事上的美感。另一个我觉得也是对于传统的某种溯源和回应吧。  张心怡(左三)在创意写作课堂讨论中 澎湃新闻:您是毕业于复旦大学创意写作专业,对于一直以来大家关于写作可不可教的讨论,作为科班出身的专业写作者,您怎么看?您觉得在复旦的学习对于您的写作有怎样的影响? 张心怡:写作可不可教,看怎么来定义“写作”吧。如果这个问题的含义是,作家能不能够通过某一个专业培养,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没啥意义的。写出来的文字,和作者本身的生命状态有着非常深刻的联系。一个人的完成,肯定不完全是学校教育的结果。 如果“写作”指的是一种对于自我的抒发和表达,当然是可教的,并且有着很大的空间。一个是表达的方式,任何文体都是一种容器,在这方面当然有创造,但我觉得更多的是学习和承继。二是有效的交流,例如说在古典文体写作里面其实很强调师承,更多的是一种思维的启发、视角的借鉴。 大家都很推崇天赋型写作,但其实这是存在着某些误解的。天赋更多的是你感受这个世界的方式,具体到操作层面,它就和许多工作一样,有自己的路径和实现方式,只不过有的比较容易被言说出来,有的可能无法被言说。 在创意写作专业的学习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复旦能够提供最好的人文教育。具体到专业领域,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进入一个自觉的写作训练过程。我研一上完王安忆老师的“小说写作实践”后就开始训练自己写短篇小说,后来一些作品放到了这个小说集子里,在叙述技巧层面,我有挺多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感悟。二是在看待世界的方式上,我经历了既有认知被打破的过程,也许现在还在经历着。就是你意识到自己失去了语言。你说出来的话不是你自己的话,是对于他人话语的重复。那么,属于你的语言在哪里?更大范围来说,究竟你自己本来的样子是什么样?能不能够寻找得到? 经历了打破就很希望能重建,即使只是寻找到一些新的资源。这些是在复旦的学习经历带给我本身的启发,改变很困难,但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契机。 澎湃新闻:据我所知,复旦在写作教育上很强调阅读、细读,想问下,哪些作家作品对您的创作影响比较深? 张心怡:我们有很多经典阅读课。有小说和散文,涉及到古典、现当代还有西方,在课上需要读很多文本,也基本上都是以比较灵活的讨论方式来展开。我很难说我被谁影响比较深,总觉得自己是个书读得太少的人。并且到目前为止,还是比较经验性的写作。如果说有比较直接的影响的,一是在技巧上,门罗的小说我读得很熟,很仔细地学习过。王安忆老师在课堂上曾反复推荐过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在早期进行短篇写作训练的时候,我是把它当教材来看的。我们班也有其他同学,把它当床头书,或者随身携带的那种,真的是反复读,理解得不够也没有关系。 在女性写作意识上,受到过一些作家的感染和启发。伍尔夫、张爱玲、向田邦子、王安忆、林白。还有就是苏童的小说,里面女性的生命力很感染我。共鸣感最强的作家是门罗,喜欢她小说里那种慈祥而温柔的刀锋。 澎湃新闻:我看到除了小说方面的奖项,您之前还拿到过首届“嘉润·复旦全球华语大学生文学奖”散文组的主奖,想问下,您后续在小说和散文、非虚构方面各有什么写作和出版计划? 张心怡:在小说方面,我想写一些不合时宜的人。在散文方面,我一直想做的,但目前可能只做了一点点些微的尝试。就是去写一些朴素的、日常的食物。写出食物里面的生活和回忆。 90后作家的系列访谈同题问答 1.你如何定义“90后”? 不好定义,我只能提供一个视角。接受过比较完整的学校教育,中规中矩,懂礼貌守规矩,但普遍的不安全感和迷茫感都很强烈。良好的教育背景和局促的生活环境所带来的,可能是要在世界上找到安放自我的方式,似乎比前辈更加困难一些。 2.你最近关注的一个社会事件/新闻是什么?为什么会关注? 李星星的事情。这不完全是一个性别对立的问题。这背后涉及到很多更复杂的问题。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那种受害者的自救方式,这也会让人想到林奕含所写下的故事。有个挺有名的电影叫《四百击》,里面那个小男孩的眼睛和做出来的一些傻事让我很难忘,大概就是一种对于世界又迷茫又无助,并尝试着艰难反抗的生命状态。 3.你如今最想尝试的写作题材/类型是哪种? 之前有提到《那不勒斯四部曲》,包括日本的角田光代的很多小说,在叙事层面,这些小说会引发我的思考。曾经想过,能不能尝试着去写好读的小说,是叙事上的训练和试验。 4.有没有写作上的“小怪癖”? 有点自虐倾向。觉得身体上的疼痛其实有助于写作(虽然我身体还行,病痛也不是太多)。不过对于曾经身体的病痛都记忆很深。 然后就是写不出来就喝很多咖啡,导致失眠。失眠之后又只好喝更多的咖啡…… 5.你比较关注的同辈作家? 对于同辈作家其实读得并不多,因为我觉得大家都还小,这是指创作年龄上的小。不过对于与自己非常不同的人,会很感兴趣。 6.你比较关注哪些导演? 李沧东、是枝裕和、小津安二郎、杨德昌、许鞍华。 7.你经常上的网站有哪些? 下厨房。各种美食公众号。 8.社交媒体上最常用的表情? 嗯嗯(常常不知道说什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