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每个人,对于自己身处的大世界与微环境,都有自己的态度,也都有自己态度的表达方式。我的表达方式,是文学,是把方块字,文学地写出来。有时候适合用小说表达,有时候适合用散文,有时候适合用诗歌,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写诗。
另外,由于在我小时候,文学率先以诗歌的形式,进入我的文化意识,写诗就成了一辈子的习惯,就像那些从小就偷吸香烟的老烟枪,一直都会吸,戒不掉,也不想戒——不就是人生的一点私人乐趣嘛。写诗对于我来说,可不是一点而是一桩极大的乐趣和无比的快乐,更因为没打算出版,多年来都是偷着乐,自由率性,无约稿羁绊,无名利困扰,不存在反复构思打腹稿,一般总是:诗句乘预感而来,随预感而去,有时候三言两语,有时候洋洋洒洒不可遏止,文字的排列组合,全凭天赐。我们楚地自古以来巫风盛行,不免让我在狂热写诗之时,常常感觉有魂附体,这是一种十分奇妙的体验和感受,却又是可遇不可求,不是可以依靠勤劳勇敢批量生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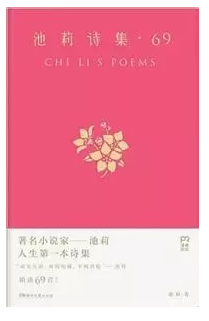
因此,《池莉诗集·69》(上海浦睿文化/湖南文艺出版社)很可能就是我唯一的诗集了。毕竟诗的直逼自我、直逼灵魂与狂热燃烧,若要公开面世,很难豁出去。我想,这本诗集以后,新的诗句,我还是会回到抽屉或者内心。
内心之河是水面以下更加汹涌的激流。有时候,几句诗,虽说是闪电般横空出世,但是其念头的缘起与形成,却已经默默旋流激荡几年或十几年乃至穷尽一生生命。这本诗集里有一首诗,叫做《爱是终身的事》,近年新作。我的出版人,第一时间阅读被感动,说他读得都想谈恋爱。出版后,好几个记者,看着我的眼神和语气透出一种微妙。他们转弯抹角提问,显然是很想提涉及我个人恋情的问题,又怕过于唐突。其实,这首诗缘起于一支鸡毛掸子引发的血案。
30年前,我在一家大医院做实习医生,经常去病案室查阅病案。病案室两个女管理员是死敌。敌对情绪是由鸡毛掸子引起的。她们每天打扫档案架,都是用鸡毛掸子扫灰尘。两人都认为对方把灰尘掸向了自己管辖的这边空间。敌对长年累月积累,慢慢变成仇恨,最后爆发惨案:二女互殴,导致一人流产,一人被戳瞎眼睛,凶器就是鸡毛掸子。悲剧轰动全院,好长一段时间大家议论纷纷,主要议论两个女人的性格、素质和脾气,批评则集中在道德层面。由于热爱文学写作而喜欢观察事物琢磨人性的我,突然跳出一个新思维:工具!方式!假设:病案室不是用鸡毛掸子掸灰尘,而是吸尘器;灰尘不只是被驱赶,而是完全彻底被打扫干净,至少由鸡毛掸子引起的仇恨,客观上就已经不存在。

人性都是有缺陷的。人的美德靠提倡与自我完善,都是很困难的。法律多是事后惩戒。教育又多是软性培养。唯有工具与方式,才是比较刚性的规范。然而问题在于,更为文明的先进的发明和创造,还是首先需要有爱的情怀与思维。三十年前一滴水珠,溅起了浪花,然后波浪拍打波浪,层层推进,在思想中循环往复,直至今天都无法止息。这个漫长的琢磨与思考,忽然在2014年秋季的美国艾奥瓦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我坐在书桌前,脑子一个空灵,眼睛一片光明,诗句火焰燃起“……我不单是用手指/更用我独有的指纹/不但是用心/更是用心里的热血/我还不止于指纹和热血/更是:/用爱的食材喂养爱/用天堂的材质构建天堂/……”《爱是终身的事》这首诗,就这样一气呵成。当我写完最后一个字,眺望远方,与美国相隔半个地球的中国,我的祖国,神奇地展现眼前。我清晰地看见,我脑子里,那些起于青萍之末的震惊与念头,在祖国广袤土地上和丰富的现实生活中,一再获得思考能量,不停地回旋、充实、上升,最终诗句一跃而出,呼应我的心声,表达我多年思考中的一缕思绪。
爱是什么?爱首先应该是一种懂得互利的思维方式。爱的食材是什么?是将这种思维方式融化在血液中,变成红血球的本质,当大脑细胞支配个人举止行为的时候,你会思考、质疑并放下手中的那支鸡毛掸子,因为鸡毛掸子是互害模式。停下互害,渴望互利,于是发明吸尘器的冲动出现了。构建天堂的材质,在爱的催生下,出现了。人类社会与每个人自己的生活中,除了吸尘器,还有很多,其他,无数。
回到读者最普遍的好奇:“爱是终身的事”指你自己吗?“用爱的食材喂养爱”指你自己吗?“我从来没有失恋过”指你自己吗?在有了上文的前提下,我可以坦诚相告:是的,指我自己。我会终其一生,努力坚持善念,用爱的食材喂养爱。我相信,人的一生,任何时候,学会互利的爱的思维方式,都为时不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