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品成是当代聚焦红军题材小说写作的专业作家。《陌生地带》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而创作。小说打破了主旋律作品的常见模式,呈现出不一样的叙事品相,是“一帮小人物凝聚了一个大时代”。千千万万个有血有肉的小人物,像历史的触手一样,让我们感知到了宏大的历史中那些真实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让历史有了温度。
红军这个主题,打我大学毕业一直是我关注的,并占据了我很多的笔墨。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倾注于这个题材。很多朋友不理解,但在我,红军不是某个政党赖以成功的武装基础,它是一种现实和现象。既然是一种现实和现象,就一定会有文学表现的空间。
二十世纪的上半个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劳苦大众,在探索一条追求民主自由之路。当然,我不对此后的结果作评点,历史交由历史自己评说,我只注重那些现象,我只注重当年那些参与者的心路历程和他们自身的感受,只重精神层面的东西。我想说,那些朴实的情怀和惨烈的经历,一直让我牵肠挂肚耿耿于怀。
我也曾对某些党史教科书和所谓红色“经典”产生怀疑,并且至今依然对其保持缄默,我想,历史上的一些东西,虽然我们不能重新经历,但可以通过各种侧面接近真相。
我小时在江西赣南宁都一个叫石上的地方生活过五年,虽身处“文革”,但与乡民的接触是直接的。母亲亡故,父亲进“牛棚”,两兄弟几乎算是辍学,辍学有辍学的好处,就不会过早的接触相关的书,属于一张白纸。所接触的那段历史的印象,皆来自乡亲的口中。那里的村庄,当年几乎所有的男性都加入了红军。一九三三年的“扩红”,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决战前面党的紧急任务决议”,号召苏区各地紧急动员起来,“在全中国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队作战”。其实当时的情况是“全中国苏区”总共约三千万人口。但各根据地是相互独立的。要与“围剿”之敌决战的中央苏区,只有二百五十万人口。要短时间扩大红军一百万,六十岁以下十二岁以上都在“扩红”的范围内。
少共国际师成立誓师大会就是在离我家下放的村子二十里地的地方召开的,我想说的是,当时我下放的那个小小的村子,当年就有十几个少年加入了那支队伍。我在那呆的时候,他们正好六十上下。而整个村子,涉红的男女就有三十多人,在我们落户的那个村子里,有五人还活着,也不过七八十岁年纪。这于我后来的写作有两点便利,一是我零距离接触过真正的红军;二是他们的口述历史使我得到另一种“真实”。他们曾经参加那场战争,但从不是既得利益者,所以他们无所顾忌。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和他们一起生活在那个村庄的日日夜夜,让我对他们有了深刻的了解和深厚的情感。
我想到了“民间视角”这个词,当然,这无关身份。据我所知,关于红军,国内很多人士在自发甚至自费进行探访和研究,无论是体制内的专家,还是民间独立的史学“自由撰稿人”,我很佩服他们。成都的一个叫周军的与我同龄的人,这些年已经翻越了红军走过的五十多座雪山,最高的海拔四千八百米且荒无人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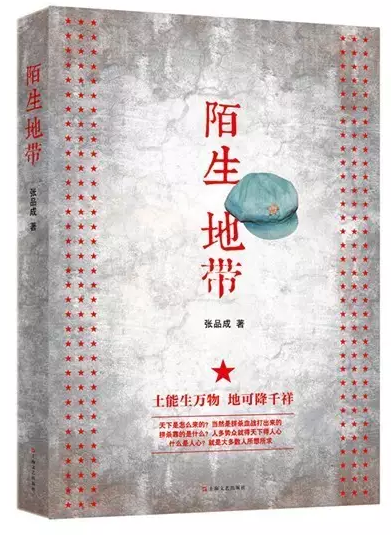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现在,我一直用“民间视角”来看待这段历史,再用独立思考来进行我的红军题材的写作,我觉得这两点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八十年代,我寂寞着且执拗着独自一人重走长征路的根本原因。尽管此后,我多次重走长征路,但从没有第一次那么壮怀激烈刻骨铭心。当然,阅读也是非常重要的,许多党史的珍贵资料和研究成果是几代史学家心血凝聚所在,应当尊重且虚心领会和消化。但文学家的历史和历史学家的历史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在文学行为中,僵硬的史料性的写作是要不得的。这是我一直提醒自己要警惕的所在。
《陌生地带》与我曾经的作品比较,不是一部颠覆性的小说,却也算得上相对“独具特色”的一部作品。
《红色中华》这份当年中央苏区的报纸,也是我一直查阅的主要史料依据。某年某日这张报纸上报道了一则消息,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全国招聘了三个种棉高手。虽然只是百余字的一则小消息,但我感觉其后面的空间很大。这是红军的高层从打破敌人经济围剿策略上的考虑,我们有大片的土地,既然能解决粮食问题,为什么不能解决穿衣问题?这三个对共产主义完全陌生的“种棉高手”在那个地方的经历和生活状态,我是有所考虑的。尤其是他们对那个“陌生地带”的认识和适应过程。
红白两军,据河而守。军官们在忙碌自己的事情,政治的经济的,可是士兵们呢?无论红还是白,士兵原本都是地道的中国农民。他们也许迫于生计,入了队伍,但具体要追求什么,大多人并不明了,只知道拿了枪能有饭吃能打天下。当然,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但他们并没有想到将来。他们都是平民,他们都不喜欢战争。
崔工胜和崔工利两兄弟,是我着力刻画的两个人物。哥哥的最后一枪和弟弟的最后悲剧,其实是我一直纠结想呈现和批判的一段历史真实。我前面说到的少共国际师,成立不到一年,在训练不足装备有限的情况下投入石城保卫战,仅此一仗,近万人的队伍损失一半。过了几月,湘江之战,少共国际师几乎全军覆没。著名的遵义会议召开不久,少共国际师番号就此撤销。至此,“少共国际师”成为历史名词。我当年那些关于这支队伍的采访手记,一直是我内心的痛,每想起,万箭穿心。
船山并不是一个完全虚构的地方,当年,红白交界的赣县,有过一个叫江口的小镇,那里,曾是红白间的缓冲地带,那地方红的白的都共处一地,相安无事。并不因为什么,只是各方都需要这么一个地方,贸易、情报、交通,甚至战事,都需要这么一个地方。在很多人看来,那是个陌生的地带,但却是他们都向往的地方。有一天江左和江右的“弟兄”彼此发现,原来他们以命相搏的目标,也不过就是他们眼前的那么个世界。
我笔下的船山,确实充满了安祥和谐,事实上,我所有的战争题材的小说,几乎没有涉及战争和打仗。
无论是围剿还是反围剿,无论是追剿还是长征,不一定全是打仗。我没说战争和打仗不重要,但几十年来作家的笔墨仅仅放在那几场战役或战斗上,写的人不怕烦腻无味,也不想想读者是否审美疲劳至倒胃?士兵们有各种各样的生活状态,我们后人在反映他们当年的历史时,为什么不可以视野放得更宽阔些,从一些琐碎和生活细节中,反映出的历史更为真实。涉及红军题材,不要动不动就冲锋陷阵战火焇烟,还有更丰富的内涵更丰富的生活情境,那些琐碎,才能真正的表现那一代人的情怀和那个时代的真实。
这正是我所追求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