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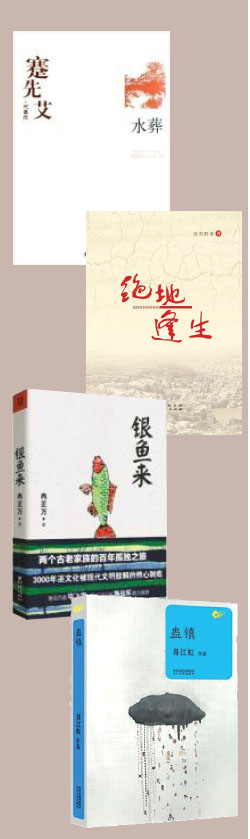
贵州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形象是鲁迅提出的“古远的贵州”。蹇先艾在《水葬》等小说中揭露了古远大地上的原始民俗和野蛮人性,鲁迅认为这种带有浓厚乡土气息的小说塑造了“古远的贵州”。此后,虽然历经何士光在20世纪80年代对贵州形象的重新塑造,但“古远的贵州”在小说中的形象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进入新世纪以后,以欧阳黔森、冉正万、王华、肖江虹等为代表的贵州作家相继在国内小说界崭露头角,他们把贵州形象推向了新层面,但小说贵州呈现的乡村问题并没有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消逝,反而暴露了乡村现代性发展的种种悖论。
欧阳黔森是新世纪贵州作家的重要代表,尤其是他对人性悖论的发掘,展示了新世纪贵州小说发展的深度。蹇先艾和何士光不仅代表了20世纪贵州小说发展的两座高峰,也代表了20世纪贵州小说的两种人性表现,如果说蹇先艾揭示了20世纪上半叶乡土贵州的人性丑恶,那么何士光表现了改革开放初期乡土贵州的人性美和精神觉醒。欧阳黔森发扬了蹇先艾和何士光的优秀传统,他把对人性恶的揭示和对人性美的追求完美统一起来,充分展现了乡土变迁中的人性复杂与矛盾。马克思认为现代性最直观的结果是“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中国在经历近40年的飞速发展以后,现代性也使中国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甚至可以说,中国乡村的“一切坚固的东西”所遭受的冲击远超过以往任何历史阶段,物质利益在乡村世界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道德失范、人性缺失和精神困厄俨然演变成不可忽视的乡村问题。欧阳黔森对当下中国的乡村现实有着清醒认识,“美丽,但却极度贫瘠”代表了欧阳黔森对当下乡村的基本看法,也代表了他对当代社会的思考,在他看来,当下乡村的精神贫瘠和人性缺失是阻碍乡村发展的重要障碍,因此,欧阳黔森一方面以人性和谐召唤理想主义;另一方面,他以人性温情召唤人道主义。在《绝地逢生》中,蒙幺爸大公无私、舍己为民,带领村民战胜了不适合人类生存的绝地,蒙幺爸成为时代英雄的典型形象,盘江支书正直、果断,盘江村民团结、勤奋、和谐相处,可以说盘江村民能够绝地逢生依靠的是一股闯劲和一团和气。在《敲狗》中,欧阳黔森巧妙地把敲狗当作是对人性的拷问,从工艺角度来说,敲狗毫无疑问是一桩残忍的手艺,狗大都忠诚于主人,狗也一直被人类视为忠实的朋友,但为了满足口福,人类又创造了敲狗这种残忍的技艺。因此,《敲狗》中的徒弟从一开始就身陷这种残忍的道德境遇,徒弟有充足理由依照师傅的嘱托敲掉大黄狗,因为敲狗是他们谋生的手段,但是他内心的人性并没有泯灭,他对狗的命运怀有同情和怜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敲狗都是作恶的重要表现,但徒弟也有充足理由放走黄狗,因为放狗是他们行善的方式。也就是说,从普遍的道德原则来说,敲狗和放狗都是符合道德、符合理性的,敲狗和放狗也就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矛盾冲突,徒弟在放狗前后的内心挣扎就是这种二律背反的表现。徒弟处于这种二律背反的道德困境,他必须作出抉择,人性的温情在道德抉择时发挥了关键作用。正如康德所说,道德领域的二律背反只有在“至善”中才能得以解决,徒弟选择把狗放走,最后还离开了狗肉馆,徒弟在矛盾冲突中最终选择了“至善”,从而表现了人性的升华。欧阳黔森把徒弟置于善恶冲突的漩涡中,最终又作出了道德选择,这也就体现了他对人性美的期待。小说结尾写黄狗回家以后,狗主人给厨子送来了200块钱,并将之引申到“信任”问题,这种信任给小说带来了浓厚的温情,信任匮乏不仅切中了当今时代弊端,而且表现了欧阳黔森对美好人性的呼唤。在乡村现代化的滚滚洪流中,人的价值观念不断发生变化,人性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欧阳黔森清醒地看到了乡村的人性问题和精神困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交换价值在现代社会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人类就会出现价值观念的变形,从而发展成现代虚无主义。《敲狗》中的师傅是一个视交换价值至上的人,他把物质利益看作最高追求,可以说,师傅是当下乡村人性缺失和价值观念变形的典型形象,师傅与徒弟的冲突也是当下乡村人性冲突的重要表现。
冉正万、王华和肖江虹代表了贵州小说在文化表现方面的重要成就。贵州处于边远山区,山高路远,贵州文化是典型的山地文化,尤其是巫蛊文化成为贵州小说发展的深厚源泉,冉正万《银鱼来》、王华《傩赐》和肖江虹《蛊镇》等小说是表现巫蛊文化的代表性作品。《银鱼来》描写四牙坝、银鱼和蟒蛇时,都表现了鲜明的巫文化色彩。四牙坝位于黔北群山丛中,“莽莽苍苍,豺狼出没,草木循四时而生,鸟雀为春光而鸣,是一片人迹罕至的世外仙景”,范孙两家的祖先为了躲避战乱而隐居于此,建构了独特的巫文化传统,《银鱼来》中一年一度的拉银鱼活动是四牙坝村民收获的节日,每年到了这个时节,四牙坝人都会无比紧张和兴奋,银鱼不仅成为四牙坝村民的生活需要,也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傩赐》中的傩赐庄位于封闭大山,傩赐人的祖先也是因为躲避战乱而迁居于此,小说中的桐花节起源于古老传说,桐花姑姑为拯救苦难的村庄,自愿成为3个男人的妻子,并为他们生儿育女。桐花被称为神娘,每年4月12日桐花开得最灿烂的时候,傩赐人都要举行仪式来祭奠她。祭奠仪式包括集体焚香唱戏撒黄豆,唱戏是其中最精彩的环节。《蛊镇》中的蛊文化在蛊镇代代相传,一直都是蛊镇村民的精神寄托。冉正万、王华和肖江虹把这些文化活动都当作狂欢节进行描绘,这种狂欢活动给村民带来短暂的快乐和生命的激情,让他们可以暂时忘却生活的艰难。众所周知,现代性的发展是伴随着巨大破坏力量的增长而出现的,现代性不仅无情地摧毁前现代世界,而且把自身也推入了分崩离析的境地。巫蛊文化可以说是前现代世界的重要代表,冉正万、王华和肖江虹倾力表现贵州丰富的巫文化资源复现了前现代世界的魅力,尤其表现了村民在巫蛊文化中保存下来的生命激情与活力,然而,现代性的发展又使巫蛊文化陷入了严峻的生存困境。在《蛊镇》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蛊师王昌林很难找到传人,悬棺也曾是蛊镇的文化传统,但随着青壮年劳动力都进了城,悬棺也就无法实行下去了,正如王华在《傩赐》中写到:“美丽的传说给我们留下了这么美丽的节日,却又给我们遗传下了一个严酷的现实”,巫蛊文化的无穷魅力仍然无法挽回它的消逝命运,这也成为现代性的内在悖论。冉正万、王华和肖江虹身处现代生活的大漩涡中,痛心于前现代乐园的消失,他们指责现代性的破坏力量,却对巫蛊文化缺乏必要的反思,表现出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色彩。
正如伯曼所说,现代生活是一种充满矛盾和悖论的生活,从这个意义来看,新世纪是一个产生悖论的时代。现代性是革命的也是保守的,它已经深入到现代生活的各个方面,乡村世界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形式都在发生着剧烈变动,每一次躁动都有可能使人们面临价值虚无主义的恐吓和文化保守主义的焦虑。现代性既是悖论的综合,又是辩证法的综合,现代性是包含了批判现代性和追求现代性的综合,因此,现代性一直在召唤人们思考“现代性的过去、今天和未来”。现代人对自我及时代的感觉是一种本能,但是,现代人有没有必要单向度地沉溺于仿造过去?有没有必要单向度地悲叹当下现实?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欧阳黔森、冉正万、王华和肖江虹默默地在乡村土地上耕耘,体验了现代性发展的各种经验,表现了现代性发展的种种悖论,但也有可能掩盖了列斐伏尔提出的一个核心问题:“我们要去向何处?”现代社会与各种各样的危机纠缠在一起,有人性的危机,有文化的危机,而其中最根本的危机却是“我们要去向何处?”乡村收藏了中国的过去和今天,但乡村是中国的未来吗?何处可以安放美好的人性?何处又可以安放文化的沉重?从这个角度来说,五四启蒙知识分子对乡村的思考在当下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