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婧:我愿意给小说的人与事预留一份“天真”
http://www.newdu.com 2024/12/05 12:12:55 文学报 何晶 参加讨论
 朱婧 2017年,朱婧在《花城》杂志重新发表小说,阔别这个写作场域十年,让她看起来仿若一个新来者。事实上,她与许多“80后”作家的起点相似——于《萌芽》成名,2004至2007年间几乎每月都有作品发表。这次回归,于她而言,是一次复苏。因为即使退场,她也没有停止写作的生长性,蛰伏而再发。 朱婧偏好写一些心理、一些情绪、一些无用和它们背后的那些人,这些人坚持着内心的某一部分,这些部分如其所言“充斥着无用,却又不能丢弃”,小说家苏童称之为“日常生活世界那些不能释怀的”。而切点都颇为细小,朱婧提供的关键词是“不惧微芥”。“世界愈大,个体就愈微茫渺小。人,尤其是写作者必须接受这种微渺,那在这个维度上,如何处理小与大的问题,是我想关注的。” “微芥”之中,是朱婧敏感于世的那个“点”——人性的软弱和天真,这在她的小说里被放大、强调,因而她的小说向人的心理深处走。她自知这将导致的结果,“在小说的形貌和气质上,或者在一般的小说大道之外,我通向了花草漫径的岔路,这条岔路可能是荒芜的,但也可能自带生机。”但在世道人心上,她更在意人心,“即便世道,也是人心之上慢慢浸渗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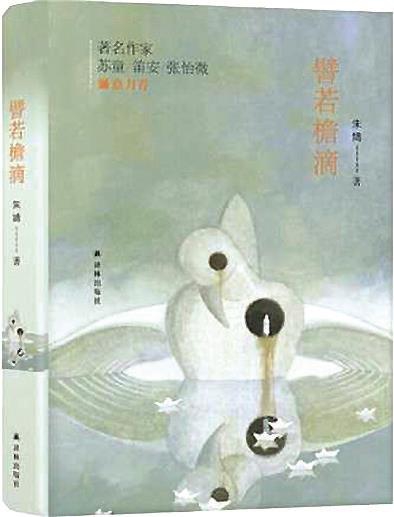 记者:首先关注到的问题是,不写作或者说很少写作的十年,当你重新回到这个场域时,它们为你的重新写作是不是提供了些什么?或者说,2007至2017年,无论在生活亦是写作轨迹上,于“80后”一代写作者而言其实是个重要阶段,你恰恰在此间退场,重新回来后评论者说你小说风格发生了很大改变,这应该不是陡然发生的吧? 朱婧:如果真存在这样一个文学场域,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大概因为年纪不大的原因,其实进场的时候是无知无觉的。那时,我写作小说,投递给杂志,获得发表,获得出版的机会,参加杂志的活动,认识写作的同龄人,认识读者,一切自然而然发生并未细想;而我不写的这些年,和文学界疏于交流,并未更深入地介入这个场域,甚至中断了以前的联系。所以,我2017年在《花城》重新发表小说,有人以为我是一个新入场的写作者。最近几年,我涉及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才注意到有的研究者把我归类在“80后”或者“萌芽系”,也才刚刚开始对于这个场域有一点整体性的认识。 对于我个人而言,在不在场,有没有被归类,是以前没有认识到,没有思考过的问题。这么多年的创作感受,我所能在意的部分是我说过的写作的生长性。这种生长性并不意味着更阔大或者更深刻,它有时更像是一种选择。正是正视并接受作为写作者的局限,但亦有不能放下的愿望。选择可以选择的,完成在有限空间的自我生长。在这个世界上,写作者的自我生长,很多时候是在黑暗中的,即使这么多年,我所谓“中断写作”,但不为人所知所见的生长出来没有停止过。评论者看到的往往是他们所能看到的。 而且,世俗的力量如此强大,我看到过写作者在写作这件事情上的艰难。写作由无法克制的自我陈述开始。体会创造之喜悦,写作似乎给人极大力量,也让人更能反观到自身的软弱。我觉得自己只是在复苏和经历的过程中。 记者:其实探究这十年的目的,或许正是因为对你当下写作解析的一种倒推。你在《譬若檐滴》一书后记中自陈现在的小说变化的因由:把力量和愿望写进去了;由此带来的小说面貌是:处理故事时不会再用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情节以及预设的情境,只要把一切推至圆融动人足矣。事实上,两者之间具体如何发生连结的? 朱婧:也许把力量和愿望理解成一种自我觉悟吧。恢复写作以后的最初几篇文章《譬若檐滴》和《那只狗它要去安徽》都有一种去戏剧化倾向。《譬若檐滴》写了一个独身带着孩子生活的女性因为依附于贵人而免受滋扰,获得庇护。这个由世俗流言而得来的故事可以有很多种书写方式,它最终成为现在的形貌,呈现了作为叙述者的“我”和窦氏生命交错里的几瞥。小说里有我的困惑和发问。到了《水中的奥菲利亚》,对于美的侵害者和施暴者发问在持续。小说借用高校性侵事件,书写师生“忘年恋”的复杂关系,进而推演至代际之间盘根纠错的命运。我曾经的学生缪一帆给我写的评论文章中说,“《水中的奥菲利亚》的追问力度更强,近乎蛮横的执着,悲哀的情绪往往呼之欲出。”诚然如他精妙概括,“再一次,我们回到了水滴的隐喻,从眼泪,到眼神,再到檐滴,都是无所作为的柔弱,却是美之奥义的恒久庇护”。这些是我带着力量和愿望想到达的地方。 记者:《譬若檐滴》中的十三个故事,甚至是此外你的另一些小说,你所聚焦的一点,似乎都是在写一些心理、一些情绪、一些无用和它们背后的那些人,这些人坚持着内心的某一部分,这些部分如你所说“充斥着无用,却又不能丢弃”,也即小说家苏童评你小说的“日常生活世界那些不能释怀的”。为什么一再描摹他们以及它们? 朱婧:2008年,我回到母校中文系,做了一名大学老师。我从“读中文系的人”的手里,窃取的能量,让我成为了“读中文系的人”,后来又成为了“教中文系的人”。 我所写的人们“内心的某一部分”,那一部分“充斥着无用,却又不能丢弃”,是“日常生活世界那些不能释怀的”。如张大春《小说稗类》所说的“不被视为有意义或有价值的、无结局亦无解决的生活细节”,正是生活中的那部分内容,可能是微暗的火,是无法知晓和具体言说的,却对我的生活和写作产生意义。这两年开始做当代文学研究,我一直关注青年作家张怡微的写作,也写过几篇评论。她以成长中变化的理解力书写世情小说中的生活力。她说:“我只能就我个人的观察和体验,来展现我所看到的这个城市的细部、这个城市的人的关系的细部。它可能是有代表性的,可能也没有。它可能只对我个人有意义,对很少一部分人有意义。” 从这个意味上说,我是在书写对于我有意义的那一部分吧。我的小说中盘恒反复的部分既是我的提问也是我想试图解答的。《那般良夜》里“我”多年后回想母亲出走的事情,在成长时岁里理解母亲。《危险的妻子》里“我”处于婚姻的危墙之下,可是,“我”总是记得自己和丈夫是“一起长大的人”。 记者:评论家何平说你热衷“那些犹可爱惜的细小物事”,“她的小说是慢的,细小的。……不浓不烈,无大欣喜也不大悲恸。在她,慢与细小,不是技术,而是世界观。说到世界观,其实没有那么多微言大义,就是一个人如何去计量世界,用什么单位去计量世界。慢的和细小的,是朱婧计量她的世界的单位。”确乎如此吗?细小意味着什么?它事实上的外延和意味是“细”、“小”的人生解剖吗? 朱婧:交通和资讯的铺张,个人可以连接到的世界越来越广阔,物质和精神可以探索的疆域都变得更浩渺了,可与之相较却是个人生活反而呈现越加闭锁、谢绝访问的趋向。世界愈大,个体就愈微茫渺小。人,尤其是写作者必须接受这种微渺,那在这个维度上,如何处理小与大的问题,是我想关注的。若提炼一个关键词,我觉得是“不惧微芥”。 我这里说的“不惧微芥”,想到的是元稹的悼亡诗《遣悲怀三首》。这首诗语言很平实,写的场景也非常普通,无非是一个男性思念亡妻的细小的场景,比如没有送完旧的衣服、未做完的针线活,但读起来感同切肤,而且这种认识随时间和经历会愈加深厚,不仅仅是在文学生活中启发我。诗中有一句“邓攸无子寻知命”,这句诗单提出来没有任何意义与效果,放在全诗中则成为“一句小说”,这句小说包含了古典与今典,几百年前的邓攸与元稹同在其中。多年前我真的把这句话写成一篇小说。我在《世说新语》里找了有关“邓攸”的条目,写成了一篇将近三万字的小说,但是所起的效果未必如书中这一句。我觉得可能那些容易表达的和理解的反而有点难以相信,道不出、讲不明的,一旦能呈现,所谓的神矣圣矣,而我在文学生活中所遭遇的和被吸引的正是这样一种不惧微芥,神矣圣矣的时刻,它们也无不在影响我的创作。 记者:“人性的软弱和天真是让我觉得迷人的地方。不管世俗的教条如何规训我们,总有偏离的时刻,带着对自己的怀疑,亦希望得到在现世的理想安置,但亦有不能泯灭的‘我’在若隐若现。写那些,似乎发生又似乎未有发生,并不激烈,却是人心的波动的过程,可能是我在逐渐偏离和放弃戏剧化的瞬间后转向去书写的内容。”你自己在《那只狗要去安徽》创作谈里的解读,以我看来能代表你的乐趣所在:人心波动,但又无有激烈、决绝,只是选择了另一条岔路罢了,失落时连叹息都轻微。是否如此?其间隐含着你自身对于外部世界和内心坚持的什么看法? 朱婧:每一个作家应该都有敏感于世的那个“点”,那是写作者所认为的世界和文学相遇遭逢的瞬间。文学的丰富性其实是这种敏感的个体有差。世界何其大,写作者的“文学时刻”是有限的。世界只有些微的被自己经验到,然后还要被恰如其分的语言和秩序所接纳。对于我而言,特别念念不忘的可能就是“人性的软弱和天真”。而且,也因为“不惧微芥”,对世界的计量单位自然也以“微芥”计,“人性的软弱和天真”在我的小说里被放大和强调,成为我与生俱来的“文学时刻”。也许是心性使然,我的小说向内走,向人的心理深处走,这和我理解的“人性的软弱和天真”休戚相关。这样的结果在小说的形貌和气质上,或者在一般的小说大道之外,我通向了花草漫径的岔路,这条岔路可能是荒芜的,但也可能自带生机。世道人心上,我更在意人心,即便世道,也是人心之上慢慢浸渗出来的。 记者:不难看出,你的语言风格是早已形成的,尤其在述说语体、文字意味上。可能有一些冒昧,我所好奇的是,这其间的“青春”意味,即使你写那些老年的、中年的男性,某些行为模式、情绪心理似乎仍是“青春”式的。这样的解读是否有所偏颇?那么,你和笔下人物各自的生长性究竟在于何处? 朱婧:虽然文学理论里有所谓的零度介入,但真正的零度是不可能存在的,所有的文学都是“有我”的。而且,在我们的文学想象,往往希望作家渐老渐熟,与子偕老。事实上可能是复杂的,比如汪曾祺写《受戒》已经六十岁了,但《受戒》却有一种清澈的少年气。你说的“青春”,我愿意看成是对世界的“纯真心”。虽然,我的小说无论是从写作到现在的生长,还是每一篇小说人物的生长,都是时间上的“不青春”,但因为我对世界褒有的纯真心,我愿意给小说的人与事预留一份“天真”。 记者: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你接下来的写作会去往何方?是否仍然在做着某种探索? 朱婧:就像我小说的“细小”,如果“纯真”和“天真”也可以是审美意义上的,其实是值得努力去做的,至于,会不会“老道”是很难刻意为之的。这一年在东京早稻田大学访学,日常是照顾幼儿,写作论文和小说。《譬若檐滴》作为恢复写作以后第一书,希望是一个好的开始。去年到今年的写作,小说写作,基本上还是按计划的两个序列在完成。一是家庭观察,观察新世代的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变化,探讨亲密关系的种种,这个序列去年写作了小说《那般良夜》《危险的妻子》《影》,并有《此时晴那时雨》《葛西》在完成中;另一个序列是“高校书写”序列,也就是我在之前所说的,回到熟悉的世界作另一种打开。这个序列有小说《水中的奥菲莉亚》《先生,先生》完成。此外,因为在东京访学一年的缘故,我系统读了一些日本民艺相关的书籍,搜集相关资料,并且去了不少美术馆和店铺实勘,想写一系列关于日本传统民艺并现代工艺美学,美感生活的传统和现代消费世代结合作用下的东京“美的生活”的散文。这是正在进行的工作。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路内:写自己喜欢的就行了
- 下一篇:冯骥才:艺术的本质是在任何地方都让美成为胜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