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珉琦 新书出版讲述人类学田野里的“花絮”
http://www.newdu.com 2025/10/21 11:10:41 中国科学报 胡珉琦 参加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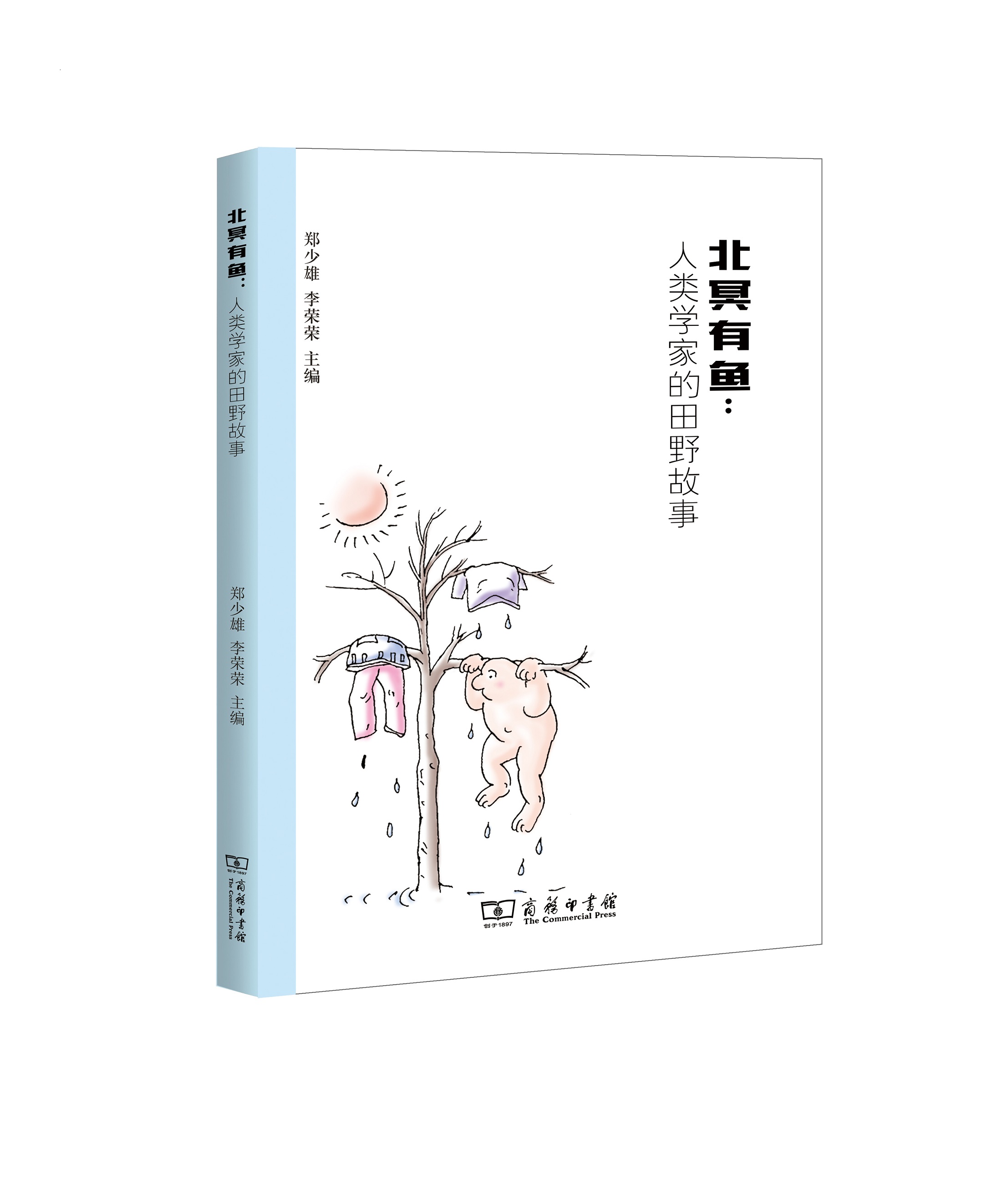 《北冥有鱼:人类学家的田野故事》 在这个内容为王的时代,写手的身份不重要,故事好就是本事。这不,最近,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潘蛟讲的一个田野小故事——《成为问题的“少数民族”与作为“问题村”的魏公村》经微信公众号的发布,迅速吸引了一大批读者。 谁说人类学者只会写高头讲章! 其实,这篇小文出自商务印书馆最新的一本图书——《北冥有鱼:人类学家的田野故事》。它既有别于学术专著,又不是一般性的旅行随笔。它是人类学者田野考察中有趣的“花絮”,也是一次次严肃的“悟道”。 会讲故事的人类学者 早在三年前,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郑少雄就认定这本书会火! 用短小的篇幅、诙谐的语言讲述人类学田野逸事的创意,来自英国人类学家奈杰尔·巴利的《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和《虫灾:重返非洲丛林》。作者也因此成为了不是凭借学术成就而“名声大振”的人类学家。 于是,当中国社科院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罗红光提出编辑出版一本中国人类学者的田野逸事集时,郑少雄就和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荣荣一起投入到了约稿工作中。 能写好田野故事固然有趣,但多数人类学者并没有这样的写作习惯,他们更关心能作为研究成果的学术论文。自然,拖稿就成了这些非职业写手丢给两位主编的难题。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的出版前后共花费了3年时间的原因。 而真正对作者们产生触动的,恐怕是在这本书正式出版以后。 《北冥有鱼:人类学家的田野故事》共征集到了国内外80多名人类学者的110篇文章,最终出现在书本中的是75位作者的98篇文章,大多数故事,这些同行彼此间也是第一次听说。罗红光还邀请到著名哲学家赵汀阳为新书作了颇有意味的漫画插图。 更让作者们感到意外的是,这本书未售先热,就连圈外的读者也对这些正经学者的田野工作产生了好奇。 其实,人类学者的工作本身就与其他学科有所不同,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人不是物。从标准学科意义上来说,人类学又是研究他者的,而他者的思维体系往往与我们存在差异,因此,文化的碰撞不可避免。 在郑少雄看来,“哪里有碰撞,哪里就会有高潮,这是产出好故事的必要条件”。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人类学就是这样一个天然的具有大众性基础的学科,只是过去没有发掘会讲故事的人罢了。 有人类学在,有田野在,还有“我”在 《北冥有鱼》的出版是罗红光做“好玩的人类学”的一次重要实践,但是不能因为它们看上去只是田野工作的“花絮”,而忽略其中的真义。 郑少雄认为,这98个故事展示了一种极其难得的多元性。一方面是人类学者与“他者”遭遇之后的文化震撼和相互理解,另一方面则是人类学者或深情或不堪的回忆。例如,张亚辉笔下晋水流域的村民去扑救山村火灾简直就是一场仪式和社交;何贝莉认为“和蝇共饮一杯茶”实际上是一种修行;王建民曾在广州的汽车上被劫走了数月辛苦搜集到的全部资料;还有历经数年准备,正想前往前东德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与文化的关系的罗红光,因柏林墙一夜坍塌,而遗憾地失去了“田野”…… 作者之一的中国社科院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鲍江评价这本书,不仅有人类学在,有田野在,还有“我”在。 事实上,这样的自我审视和认知并不是人类学历史上从开始就有的传统。过去,人类学者被定义为一种唯科学主义式的“技术性客观主义”者,研究者必须把自我意志掩藏起来。 然而,“人类学者常常独自一个人在外做长期的田野工作,所获不仅是民族志,还有与其田野及其研究对象割舍不下的那份情感。这份情感渗透于作为人类学者的学术立场之外,具有鲜活的,充满喜怒哀乐的情绪流动。”罗红光在本书“寄语”中写道。 “这说明在田野中人类学者并非仅仅以‘科学者’的姿态出现,他(她)首先是以与自己研究对象本质上并无差别的主体人的身份出现,客观上形成他者双方在田野中的邂逅”。 在他看来,彻底“净身”,没有意志的客观性,其实是一个伪命题!这些个体的情绪和反思,正是在他者双方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产生的,这也将为其他从事人类学研究和学习的人提供很好的借鉴素材。 人类学人人都该学 人类学研究的核心目的,是通过对他者的理解,绕道来理解自我。而这不仅仅是人类学者的工作。 潘蛟记录的田野故事里,有一些生活在21世纪的知识分子,他们质疑现有的民族承认政策人为地固化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界限,妨碍了国家的整齐合一。他们认为应该以一种无视差异的公民政治来取代民族差异政治。这就导致了,那些认为自己文化传统应该得到应有承认和尊重的少数民族反倒成为了一个“问题”。可在人类学家看来,那俨然是19世纪所倡导的论调! 它之所以引发读者的热议,不仅仅因为故事发生在大多数北京人都熟悉的魏公村,更因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可能就存在于你我的潜意识里。 张原笔下,一个农村的灾后重建项目最终演变为一场山外“爱心人士”与村民的对抗。前者帮助村子修建更为实用的水窖,得不到支持,而后者却主动筹资在水窖旁新建了观音庙。外来者为解决问题并没有错,错的是没有尝试去理解乡土之上的生活有何意义。扪心自问,多少灾后的社会重建与社区营造,首先做到了“贴心”。 事实上,这些来自异文化的冲撞,是每一个生活在人际交往中的普通人都会面临的。“而人类学的反思性、包容性可以帮助人们意识到,他者的任何一个行为背后都有着更为广阔的社会脉络,人们需要一种更为审慎和周全的态度,摆脱狭隘的文化偏见的束缚,学会理解和尊重人性以及文化的多样性。”郑少雄表示。 在欧美,人类学是高等教育通识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促进学生人文素质的养成。如果《北冥有鱼》这些深入浅出的故事能够吸引更多普通大众的关注,那么这将是国内人类学促进公众教育的一次积极的尝试。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陈洁 杨绛先生的梦
- 下一篇:孙述学 《辞源》数字版:研发加密技术创新销售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