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剧作家曹禺(1910.9.24——1996.12.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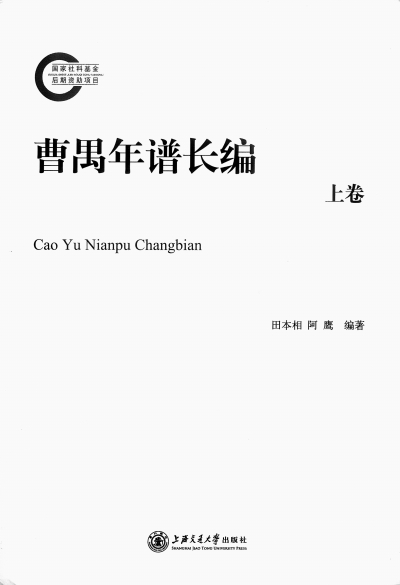
“要把我的苦闷写出来!”
20年前的12月13日,曹禺先生仙逝。曹禺先生,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我永远不能忘记我收到曹禺先生的第一封信的时刻,他不但对我写的《曹禺剧作论》给予首肯,而且约我在他访问美国回来后与我会面,由此开始了我和先生十六年的交往。
我虽然是先生的研究者,但是十多年来,我自认是他的学生。随着我对先生的几乎不计其数的访问求教,日益增加着对他的了解和崇敬,日益感受到他的为人种种,他的苦闷和焦虑:他自己的焦虑,对文坛的焦虑,对社会的焦虑,对中国文艺事业的焦虑和殷切期望。
如果说,当我在案头研究他的剧作时,也许会讲一点对他及其戏剧的评价;但是当我与他面对面交谈,就深刻地感到我的认识是太浮面了。在聆听他的教诲时,我深切地感到在我面前他是一个伟大的天才,一个可亲可爱的老师,让我更感性地体味到他的真诚,他的苦闷,他的胸襟,甚至他的天真。
我深深感谢先生对我的信赖。先生真诚地把他的内心世界袒露给我,放心地交代给我。他说:“你要写我的传,就要把我的苦闷写出来!”这是对我的郑重的委托和教导,这成为我写作他的传记时的座右铭。这让我深深感到我的责任。我就是在写先生的传记过程中,得到他的传承而成长起来的。
与鲁迅思想相通
作为他的一个学生,我是深深地感谢他的。也可以说是他把我引领到这个我所陌生的中国话剧研究领域(开始我还想:写完《曹禺剧作论》,还回到鲁迅研究中)。他从没有叫我这样那样地去做什么。完全是因为研究他的戏剧,我感到了中国戏剧的骄傲,中国话剧史研究的价值。话剧,中国话剧,它并非一个为人不屑一顾的冷门。是他让我站在中国话剧的峰巅之上,俯瞰和思考中国话剧的大千世界。
我是从研究鲁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走向曹禺研究的。这似乎又让我站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峰巅——鲁迅的峰巅——来研究曹禺。这就给了我一个宽阔的视野,一个权衡和评估文学作品的尺度。在对曹禺的潜心研究中,我真的感到曹禺和鲁迅的思想是相通的。由于我对鲁迅的感受,我内心对曹禺的评价是:他不但是中国话剧创作的第一人,而且我认为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创作中,鲁迅是第一,第二就是曹禺了。我相信,历史和现实已经或正在验证着我的看法。
如果说鲁迅先生以其伟大的理性和感性(他的文学作品和杂文等),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那么曹禺先生是以其剧作,成为一个伟大的剧作家和思想家,曹禺同鲁迅的思想是相通的。他们都有着不可否认的现代性,而且更有着时代所需要的当代性。
以对封建主义的深刻批判来说,鲁迅和曹禺都是对于封建文化思想的批判家。可以看看现代中国的文化思想,包括政治文化,封建主义的幽灵依然在游荡。“文革”的祸害,让人们看到封建主义文化思想,依然是可以葬送新中国的思想祸源。鲁迅的言论自不待说,就说曹禺的一个周朴园,是多么深刻地画出封建主义的幽灵怎样复活在一个近代的资本家身上。当下,封建主义的幽灵,附会在各种现代的时髦的名目和行动中。反封建主义,是一个长久的使命。曹禺作品的当代性就在这里。
我曾说曹禺的灵魂是一个渴望自由的灵魂,其原因是他亲身体会和看到封建主义的压抑。曹禺从他父亲万德尊身上体验到这种压抑;从沉闷的家庭生活中更感受到牢狱般的压抑;从他的保姆段妈以及他的大哥大姐的遭遇,也感受到几乎无处不在的压抑。他为什么转学清华?他说过他不喜欢南开。南开有治校的保守的方面,而清华在当时可以说是一所比较自由的大学。清华的自由氛围,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环境。《雷雨》产生在清华不是偶然的。
跳出社会学和概念化的框子
也许我的感觉是不对的:虽然先生是剧协的主席,是文联主席,但是,我看一些人并不是很懂得他,似乎他的话也不见得能够听进去。
就说他对社会问题剧的看法——他不是否定这些剧,而是希望跳出这个框框,也就是社会学的框子、概念化的框子。当初由陈恭敏的文章而引发的戏剧观大讨论——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以曹禺先生关于社会问题剧的文章来发难的,其目标就是针对僵化的戏剧观念。但是后来引到形式主义的方面去。曹禺对社会问题剧的批评,是意味深长的。譬如他对《假如不是真的》的批评,与一些人的批评是不同的。他是觉得戏这样写不是一条大路,今天批评一个市长,明天批评一个省长,或者单纯局限在揭发上,都是有局限的。所以他发出要写人,要写人性,要关心人类的命运的呼唤。他希望写出不愧于时代的伟大作品来。
我们对曹禺的研究,过去重视对他剧作的研究,而对他的戏剧美学思想研究不够,对他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新时期的戏剧美学思想研究不够。可以说,他对当代戏剧问题的思考,对戏剧创作的规律阐释,对一些剧目的批评,都有着他的真知灼见。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他对中国戏剧寄托着殷切的期望,把他毕生的经验和渴望都尽其所知所想,都说出来了。这些对于中国当前戏剧发展有着极为宝贵的现实意义。
在我走向戏剧研究的历程中,能够遇到这样一个老师,是我一生的幸福,是我终生难忘的。
我正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研究他,研究中国的话剧。今年送到大家手中的这部《曹禺年谱长编》,也是我感恩之作。我所以这样详细地记录他一生的行迹,是希望给人们提供研究的便利,希望有人写出更好的有关曹禺的研究著作,我很自信地说,这个年谱会有助于深化曹禺的研究,写出更好的《曹禺传》来。我期待着。
田本相,1932年生于天津,著名戏剧学家。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中国话剧理论与历史研究会会长、华文戏剧节委员会主席等。著有《曹禺剧作论》、《曹禺传》、《曹禺年谱长编》、《田汉评传》、《田本相文集》(十二卷)等,主编有《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中国话剧艺术史》(九卷本)等。
延伸阅读
为使《曹禺年谱长编》更具有资料价值和学术含量,编著者采取了如下方法:
一、锐意穷搜、博嵇广览。曹禺著作、有关诗文、杂史方志、有关年谱传记、日记笔录、遗址旧居、文物档案、期刊杂志等,均在搜索范围,可以说数以千计。
二、注重口述历史的调查。对曹禺以及他的亲朋好友的访谈,不下数十人,从中获得极为珍贵的史料。
三、年谱所录所记,虽不能说事事都追索原委,但做到每条记录,均有来历。多数年谱,一般不注明出处。田本相先生为了后人研究,也证明有所根据,几乎每一条都注明出处,任读者检索查证。同时,一则事实,有不同记录,而不能断定者,则提供不同说法。
四、最重要的是,在编写年谱长编时,有编著者的学术追求。年谱并非事实的罗列。它所展示的,虽然是一个人的人生历程,但是,却应是中国话剧史的、现代艺术史的侧影;也应是近现代文化史、思想史,甚至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