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漆香中慢慢安静
http://www.newdu.com 2025/12/18 10:12:11 中国作家网 林那北 参加讨论
 奔 放
奔 放
 四 季
四 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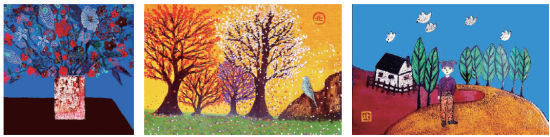 盛 开 问候季节 记忆一种
盛 开 问候季节 记忆一种
上中学后,恰巧我们这个年段的美术老师是我母亲。看她在讲台上说着画着,煞有介事得与平日灶台锅碗边那个浑身烟火气的中年妇女判若两人,觉得相当滑稽,不免一阵阵想笑。那时课堂已丧失基本尊严,所谓的课外兴趣小组倒是格外红火,学校美术小组由母亲负责,每周有两个下午活动,她于是想当然也把我拉进去。百折不挠这个品质,在父母对子女的殷切期望上,一次次得以明证。小时候我想必病得不轻,病名叫多动症。上树、下河、奔跑、跳跃才是强项,终日混迹宣传队运动队,身上潜藏的万千野性必须在挥汗如雨的动态中挥霍掉,让我拿笔安安静静画线条,真是对双方的折磨。但母亲屡受挫还是屡幻想,幻了十几年,甚至威逼我拜到另一位美术老师门下,练了一阵素描色彩,做起考美院的小梦,最终实在被我各种偷懒懈怠气得七窍生烟,才让绝望款款而至。若干日子后,当我女儿也学绘画,整天趴在画板上涂涂抹抹时,我对家中上下两个美术人才熟视无睹,依然觉得自己是跑在另一条道上的马,井水不犯河水,永远不会有与她们重合的可能。 但是意外还是出现了,有一天我竟然也玩起了画——漆画。 起步确实只是图个好玩。最初是正就读北京电影学院的女儿假期闲在家里,为杜绝她懒觉睡太多,而把她带到做漆画的朋友那儿学。她试了一阵,痛惜手变粗糙而放弃,作画的木板与各种漆材丢在那里看着刺眼,我索性就试着往下弄了。先用腰果漆做了几幅,然后迅速转向大漆。 大漆来自植物,是漆树被割开后,从韧皮里流出的白色黏性乳液,再加工成各种色泽的涂料,既防腐防潮,又耐酸耐碱耐高温。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那只7000多年前的朱漆碗,上面色泽犹存,就是大漆秀给世人的肌肉。我显然很快被这种奇特的液体迷住了,它可以那么柔软地流淌,又可以如此坚硬地凝固,对环境气温以及湿度不近人情地苛求,但只要你稍加用心,它又往往有超乎想象的完美呈现,剔透得宛若珠宝。 福州气候潮湿温润,与漆性相符,虽不产漆树,漆艺却一直遥遥领先,抬头低头间就会蓦然与一场漆画漆艺展或者一位漆艺漆画家相逢。“开了”,这是漆画界的一个术语。一幅画完成了,漆性却仍是活的,它还会按着自身的惯性缓缓成长,像一位含苞的女孩,在无人觉察间,自顾自地步步迈向最欲滴的饱满。贵如珊瑚、珍珠、宝石,贱似蛋壳、螺钿、炭粉、瓦灰、木屑、锡片、铝板、铁丝、麻绳、夏布……天底下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来,先一点点埋下,然后以漆一遍遍髹过,用砂纸一层层研磨,再不厌其烦地推光、揩清。整个过程像铿锵的奔腾,又像静穆的修行;是任性的挥洒,又是精致的磨砺。斗转星移中,肢体已经在疲倦中一年年慵懒懈怠下来,欲望与杂念却日日累积叠加,世事纷乱,心事浮躁,但漆味一起,刹时竟一切屏蔽。哪天如果要用蛋壳贴出图案,比如墙体或者树身纹理时,整个世界就一下子缩小至仅剩下手中这块方形木板,凝神静气,弯腰俯背,眨眼间大半天就一晃而过了。待直起身子,长吁一口气,觉得天地宽阔,岁月无尘。 这把年纪了,完全没有想到还能这样,我自己也不免屡屡暗惊,然后暗喜。 大漆过敏似乎是一个无解的大问题,红疹一片,痒至骨头。不时听到某某某某,已经与漆打了一辈子交道,仍一辈子被咬不放,碰一次倒霉一次,脸刹时可能红肿如烂南瓜。所以总有人问我:你过敏吗?我摇头,不会,我皮厚。问的人一定会连啧几声,他们赞的是我的狗屎运,居然天生有抗体。我却暗想,这其实是漆为诱我深陷而抛出的小福利,它耍个小计谋牵住我,能走多远是多远。 确实不知道能走多远,不谋划,不眺望,也不问结果。敞开自己,不为任何世俗名利所驱使,剩下的只是生命的需要,这便是一种最天人合一的放纵了。已陆续有人来问价欲购,我摇头。或者送呢?我也摇头。它们在眼皮底下一件件胡乱挂起或任性摆放,花花绿绿地热闹,几乎显出如花似玉的小妩媚和小家碧玉的小清新。得空时细细打量几眼,我的目光里想必已经泛滥起浓浓的母爱了。 事实上我尚不敢把它们放出家门,我清楚它们还不够好。目力所及,边界越辽阔高远,就会越明白自己站立处的低洼潦草。但我也从来不曾羞愧难当,起跑线不同,目的地也迥异,那些制作精良的专业画作不过是一个标杆,它们可以在前方隐约召唤,让我致以无限敬意,却未必能真正将我收归门下。 有一个秘密始终藏于心底——如果算得上秘密的话。当初那些被女儿废弃的材料被重新收拢利用起来时,我其实是暗揣“深入生活”的老套理念,为写一部与漆有关的小说做些准备。古往今来,福州这座城一直有无数漆匠漆艺可圈可点的故事在流传,那些命运多舛的人物,身上荡着浓郁漆香,双手沾着斑驳漆色,一生短促黯淡匆匆而逝,可倾其心力创造的漆器却历久弥新,仍然光彩熠熠地呈现于我们的日子里,并且还会继续呈现下去,与更多的春华秋实、晨光暮色相见甚欢。这里头肯定横溢着几分难以言说的苍凉,它完全可以成为一部小说潜在的质地,把悲欢、恩怨以及万千无奈逐一承载。只是几年过去,小说却尚未到来,随着一幅幅画制作完成,它们反而渐行渐远渐模糊,仿佛被大漆光茫一映衬,不免自卑了,胆怯了,退却了,萎缩了,一去千里。 我并不着急,在漆香中慢慢安静,慢慢神闲气定地等待。无论如何,总会等到它“开了”的一天吧?即使等不到,那也没关系,凡事皆是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