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蕾拉·斯利玛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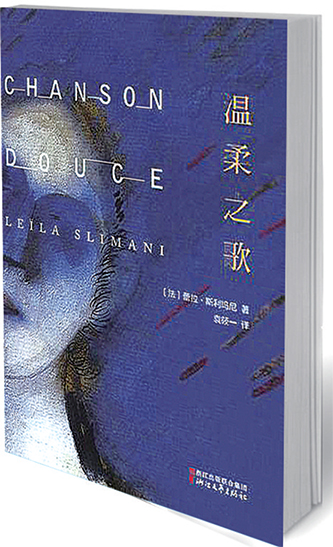
阿莱克西·布洛卡(以下简称“布洛卡”):和您的上一部小说《食人魔花园》一样,《温柔之歌》这部作品有一半也是留给读者去想象和填补的:对行为的描绘占了大部分篇幅,同时您给出了许多具有象征意义的细节——如保姆给保罗夫妻留下的干干净净的鸡骨头,这些细节给读者留下丰富的阐释空间,这是有意为之的吗?
蕾拉·斯利玛尼(以下简称“斯利玛尼”):我很欣赏读者应当介入阅读的观点。我不喜欢人们把文学当作纯粹的消遣,那样读者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当然,这类书是有必要的,但我在写作时会尝试写出其他东西,能够打动读者、让读者走出舒适区的东西,强迫他们看到那些不太愿意看的内容。在这样一个随处贩卖舒适感的世界里,我主张的是一种文学上的不适感。
布洛卡:您的作品里经常有童话世界的影子。比如《食人魔花园》这个书名就是一个黑色童话,在《温柔之歌》中,小米拉会说“我的保姆是仙女”。童话呈现的是一个理想化的、神奇的世界,但里面隐藏着许多能够用精神分析法研究的内容……
斯利玛尼:童话是一种隐喻。在童话世界里,每人都有一个既定角色——父亲、母亲、孩子们、仙女和女巫,最终,人物的面貌会随着故事发展而改变。我也欣赏童话能够带着某种距离感甚至漫不经心去挖掘最原始的恐怖。我的作品是扎根于社会的、现实主义的故事,但同时也建立在更普遍、更古老的基础之上。阿黛尔(注:蕾拉·斯利玛尼第一部小说《食人魔花园》的主角,一名女性瘾者),这位21世纪的女性,也是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和小红帽的女儿——在童话里,人物无法逃脱命运的掌控,无法逃离等待在前方的那只狼。
社会阶层
布洛卡:您的小说清楚地展现了这个家里雇主和雇员关系的转变。19世纪时,佣人不是“家庭的一员”,而更多是“家具的一部分”。保罗和米莉亚姆给予了路易丝很多善意的关注,他们在不知不觉间促成了路易丝的疯狂举动。
斯利玛尼:保罗和米莉亚姆不属于大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雇佣佣人是正常现象,而他们是布波族(注:即“布尔乔亚-波西米亚族”,该词因美国作家大卫·布鲁克斯《天堂里的布波族》而广为人知,指的是在信息时代进入社会中上层阶级的新知识分子,他们追求资产阶级式的生活享受,又兼具波西米亚人的自由不羁,崇尚独立精神和创新意识)。雇保姆对他们来说是经济上的牺牲,是一种奢侈的选择。然而,很快,他们意识到此举使他们进入了新的社会阶层,一个他们不希望进入的阶层。由于他们不想与路易丝产生等级关系,因此他们尝试用亲切和友善来消弭等级,而他们的行为往往会伤害路易丝。他们想把事情做好……但怎样才算做得好?
布洛卡:您几乎是用一种科学的手法来使用这些具有社会学意义的细节。通过人物所属的社会符号来将其分类,这是您写作时关注的重点吗?
斯利玛尼:人们以这种方法给他人分类,他人也希望以此被分类——有些人想显得比实际的自己更富有,或者更无辜,或者更低调。我对此很有感触。我确实对细节十分敏感。我认为一个人的吃穿、谈吐或走路的形象往往比长段的语言或者心理描写更有说服力。在这个问题上,我属于契诃夫一派,他说:“如果文中写到了枪,就要让枪派上用场。”要给予你呈现的普通细节以生命。这对小说而言是一个美好的挑战。
布洛卡:从前,人们的名字、出生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如今一切都混乱了。所以这些符号是否显得更为重要了?
斯利玛尼:确实,现在的一切都比从前更混乱,或许可以说冲突更剧烈,总之社会的融合度在下降。要说工人阶层的敌意和资产阶级故步自封于其规则和思维方式的程度,我感觉法国比摩洛哥更为严重。我认为这是我们面临文明困境的原因之一。不同阶层的人生活在一起困难重重,或者说,他们根本不愿意共同生活。在巴黎第十八区,政府打算把两所高中合并在一起,其中一所是布波族孩子的学校,另一所都是家庭条件较差的学生。这些布波族不愿自己的孩子与黑人或阿拉伯小孩成为同学,然而他们其实很友善,不是种族主义者,他们会送旧套头衫给难民穿。我也试着描述这个阶层的人内心的矛盾状态,他们没有人们想的那样夸张和讽刺。
母亲身份与个人发展
布洛卡:您在《食人魔花园》中探讨的另一个主题是母亲的身份。她承受着一种矛盾的折磨:如果她去工作,人们就指责她忽视了对孩子的照顾;如果她照顾孩子,人们就讽刺她的家庭主妇身份……
斯利玛尼:母性的问题在文学中得到的挖掘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多,由女性来挖掘的则少之又少。许多女作家不想成为母亲,认为这与她们的写作前途背道而驰。这并非一个无关痛痒的问题。如果你需要照顾小孩,这就与你坐在办公室里和写作的意愿相矛盾。如果你有孩子,而你花在写作上的时间比照顾小孩的时间多,人们就认为你是个不称职的母亲。这不同于你为了养活他们而出去工作。此外,做母亲的幸福感也是一个问题:这往往都出自男性之口!女作家如何看待“成为母亲的幸福”?我想要讲述围绕母性与“母亲的本能”建立起来的神话和谎言,我一直在做这件事。在现在的社会,人们告诉母亲,工作、母亲的职责和生活娱乐三者可以兼顾。但与此同时,人们又一点一点向母亲灌输罪恶感,这种罪恶感日渐沉重。在《温柔之歌》中,米莉亚姆看着她的孩子,心想:“人们只有在不彼此需要的时候才是幸福的。在我们自由的时候。”这种由照看孩子产生的晕头转向的感觉,以及意识到他们是多么需要你的感觉,是不容易摆脱或者成功适应的。在文学层面上,这种眩晕感有引人入胜的效果。
布洛卡:确实是这样。当我们思考文学中的母性时,我们会想到阿尔贝·科恩《我母亲的书》、罗曼·加里《黎明的承诺》等。
斯利玛尼:是的,这是一个小男孩对母亲的认知。“我最爱的人,我完美的妈妈,如果没有她,我永远不可能成为作家,是她对我寄予了厚望。”他写到过他母亲那些绝望的、或许对他感到厌烦、想把他扔到窗户外的时刻吗?没有!他想象不出这些。我想讲述的就是与这种美好的粉饰相反的东西。
布洛卡:人们认为母性代表着一种绝对的人生完整性,您是否被要求相信它,重新戴上一个“完整”女性的面具呢?
斯利玛尼:当你推着童车里刚满月的可爱小婴儿走在路上,别人对你说:“你一定开心极了吧”,你肯定不会说:“其实我并不幸福,如果可以话,我倒想把摇篮给你。”这是禁忌。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也把这种代表了人生完整性的母性形象当作是对孩子的保护。需要告诉母亲她们是幸福的,否则她们会抛弃自己的孩子。正是出于这一考虑,那些有名的心理学家或社会学家都维护着这个谎言。《温柔之歌》从根本上说是一部黑色小说。它以一桩杀害儿童的事件开始,回溯过去,人们看到了一个女人如何一步步变成杀人凶手,人们找到了证据。
关于写作
布洛卡:您的语言十分简洁,从来不为叙事制造障碍,不追求文体学上的雕饰以显示自我的与众不同。这是一种有意识的写作手段吗?
斯利玛尼:我给读者设置了其他障碍,因此在修辞风格上要让读者感觉简洁明了。由于人物和话语往往暧昧不明,在写作风格上,我就尽力做到明白晓畅。另外,我感觉简洁的法语是优美的法语。当我们囿于复杂风格时,就无法表达简单的东西,最终会给人留下偏离主题的印象。
布洛卡:您也曾为报纸撰写文章,积极介入社会,对社会事件发表看法。您的小说中也展现了一种政治维度,但并没有同样的愤怒情绪。在您看来,应当区分二者的界限吗?
斯利玛尼:坐在桌前写小说的那个我,是摆脱了愤怒、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社群归属的我。我关心的问题是:作为一个人,而非一个生于80年代的马格里布女性,我可以讲述怎样的故事?我也喜欢写介入社会的文章,把我的观点展示在世人面前。但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也许它们在未来会有交集。写作会受到所处时期、灵感和外界支持的限制。我正在构思的下一部小说将触及更为政治化、更有争议的主题。 (编译 刘舒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