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波丽娜·盖纳(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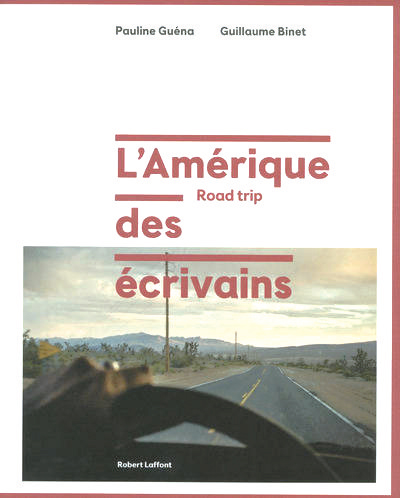
《作家的北美》法文版
法国作家波丽娜·盖纳遭遇了一场写作危机,遂同丈夫一起,带上孩子,奔向北美,意图求得疏朗开阔之道。他们见了北美的26位作家,从莽莽森林奔向辽阔海洋,从黑奴庄园聊到卡特琳娜飓风,从儿童凌虐提及枪支管械,于是便有了《作家的北美》。
由作家采访作家,面对思想上的同行者和共鸣者,作家们往往会给出更加真挚细腻的答案。北美文学除了美国以外,也包括加拿大文学,所以这场文学盛宴显得更为诱人。尽管福克纳的余晖仍照耀着北美,但仍有许多作家脱颖而出:威廉·斯泰伦、尤多拉·韦尔蒂、弗兰纳丽·奥康纳、凯瑟琳·安·波特、玛格丽特·劳伦斯、爱丽丝·门罗等等。而《作家的北美》中受邀接受访谈的26位作家,既有为人熟知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理查德·福特,也有年纪轻轻就已崭露头角的迪奈·门格斯图、克雷格·戴维森等等。
盖纳的问题很多,有琐碎的重复,也有出其不意的发问;有精心准备的访谈,也有可遇不可求的会面。作为读者,最关心的大概就是作家们是如何成为了作家的。有趣的是,我们看到作家们的职业生涯选择往往有天意注定的意味。即如约瑟夫·波登所说:“我从来没有真正地决定过,是写作选择了我。”约翰·毕盖奈还是个孩子时就渴望成为画家,为了参加阅读报告比赛所以画了39幅画,写了一个小段落,却因为最后的这个小段落拿了冠军,气得“眼泪都要哭干了”;上了中学后,因为上课无聊所以写诗,被老师抓到行政处,领导却对这些诗大加赞赏,寄去参加诗歌比赛又拿了奖,毕盖奈赶紧花钱收买学校报纸主编,千万不要透露“篮球队队长居然赢了一场诗歌比赛”!所以约翰·毕盖奈不无挪揄地自讽:“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生活一直在驱使着我写作,一直到我停止反抗为止。”而也正由于生活这无情的驱使,才有了他在《模子》《上涨的水》中对卡罗琳娜飓风后新奥尔良城中百态入木三分的刻画和对不作为政府的鞭挞。
提到政府,盖纳在这本访谈录中无数次地问到各位作家:“您是一位介入作家吗?”这也许是一个典型的法式问题,因为当提到介入作家时,首先跳入我们脑海的名字必然是如雷贯耳的萨特和加缪。和作家们不约而同地认为写作是宿命的选择不同,对于这个问题,作家们的回答莫衷一是。波义耳告诉盖纳:“我不认为文学有什么政治功能。我觉得文学可以给你带来欢乐和感动,它可以改变你的思想和观点。但文学并不是万灵药。艺术和政治是不能相融的。”詹姆斯·李·伯克说:“政治是我们写作的一部分,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是我们生活的扩展。”迪奈·门格斯图则坚定地认为:“我的写作决不能离开政治。”不可否认,无论是否介入,这些作家都坦承对于当今社会的担忧:“一边是赤贫,一边是极富!”多伦多的克雷格·戴维森提到加拿大和美国边境线人民生活时忧心忡忡。当然,这些作家中最激进的大约是大卫·范恩,他对美国感情深刻,却一生也不愿再回去生活和工作。为了揭露生活的某些真相,作家往往需要鼓起勇气揭开社会的某些鲜血淋漓而层层叠叠的伤疤。枪击案、恐怖分子都是美国的伤疤之一,范恩称之为“巨大的谎言”。频繁发生的枪击案刺痛了美国人的神经,但他们仍一厢情愿地相信着“我们是个善良的民族”。大卫·范恩冒了天下之大不韪,愤怒抨击美国政府和军队“政府想要将人民变成他们的奴隶”,“军队惟一给我们带来的,就是溃败”。自然,作家在如此强力地介入政治后,被戳到痛处的民众们往往会猛虎暴起而攻之,所以范恩迁居到了新西兰,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国家。真相往往残酷,这也让人想到了大声疾呼社会吃人的鲁迅,这样强烈的斥责总不会受到当时民众的欢迎,但当我们跳出当时的历史环境来看,鲁迅的《狂人日记》也正真实而鲜明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而同时也正如托马斯·麦葛尼所说,家里可以有纷争,外人却不能指责。但若是这纷争已影响到外人呢?或者说,在世界这个大家庭里,没有外人,我们都被全球化操弄于股掌之中?所以无论是美国枪支,还是恐怖分子和难民潮,我们永远也无法置身之外,漠然视之。
在访谈录中,有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是“暴力”,这让人多少有些惊诧,并显得突兀。但正如耶稣所说:“我来不是叫这世界和平,乃是叫这世上动刀兵。”所以暴力的反复出现又显得平常而自然。当然这暴力除了子弹出膛的巨响以外,还有民众的麻木和冷漠。正如范恩所提到的:“对于真正的恐怖来说,暴力和心理是完全分离的。”当你能对他人的苦痛漠然视之时,你便已经参与了暴力。而劳拉·卡塞斯克对暴力则有另外一种解读,她认为:“暴力主要还是心理层面上的,是平凡人物内心斗争的产物,而且会通过人物的外在行为表现出来。”因而有了《魂归故里》中残忍的姐妹会,《欲望悬流》中麻木的挥霍与嫖妓,《眼前的生活》中高中校园的枪击事件,又或是《冬天的心》中无法建立的母女关系。正如“百分百平凡的日常在我们眼前裂出缝隙,暴力以最惨烈的姿态喷涌而出”。
从《作家的北美》书名便可知作家对于地理意识的重视,所以书中在每一篇访谈前,都或浓或淡的笔墨勾勒当地风情,因而读者会看到阿第伦达克山脉在班克斯书中投下的倒影;詹姆斯·李·伯克书中受到毒害的路易斯安那州,阿斯维特书中的纽约和大城市……众所周知,地缘环境与个人身份及文化身份总是紧密相连,须臾不离的地理意识的背后蕴含的必然是对于身份的认知。来自埃塞俄比亚、生活在纽约的非裔美国作家迪奈·门格斯图坦言是对于身份的焦虑促使自己走上文学道路:“只有在文学中,才不用担心我有没有朋友,我够不够好,是德国天主教白人还是黑人……”“我一直认为我只能把自己定义为美国作家,因为我觉得没有其他的文化能够给予人如此复杂的身份了……”身份和地理是无法分离的褡裢,对于有色人种来说尤其是这样。当然也有对此十分坦然的非裔美国作家约翰·埃德加·维德曼:“我的全部人生,以及滋养我长大的文化,在大众眼中都是边缘化的,不是美国伟大传统的一部分。这不重要。如果您对此有所了解,当然更好,如果不了解,那也无所谓。“事实上,我们也看到有色与否并不能遮掩或放大作家们的光辉,身份与地理因素同样,都只不过是写作的机缘或是写作的一部分而已,写作的真正意义在于写作本身。
当谈及纯粹的写作时,作家们在访谈中始终坚持的一点是:写作之路是一场冷暖自知的苦役,需要坚持,不可气馁。因为写作也许无法给作家带来直接回报,甚至是没有回报……成就事业必然要忍受时间的凌辱,这一点大概是所有学科都共通的。詹姆斯·李·伯克说道:“为了活下去,脏活苦活我全都干过……”“我被出版社拒绝了111次”。丹尼斯·勒翰为了生存专门给人停车,一个月瘦了13斤……如今轻描淡写的,当初大抵也都是在焦虑彷徨中灼灼不安。当然能坚持到接受访谈的,必是从这些苦役中提炼出甘泉畅饮再继续踟蹰前行的。写作的确是件单调乏味的事,而同生活一样,正因为这单调乏味的一日又一日,写作才有了伟大的意义。然而一直话题不断的作家詹姆斯·弗雷在抗拒单调时又一次“倒行逆施”:在所有人都对“商品文学的大规模出版”这个概念愤慨反感之时,他却开始了自己的工作室,和其他五人一起,开始大规模出版商业文学,这些书的激进之处不在于其内容,而在于它们的创作方式,意料之外而又情理之中的是,有五部作品都登上过畅销书排行榜榜首……“文学是否可以被大规模出版”并不是一个新鲜的问题,但答案却久久未曾统一,在这个人工智能时代,一切都可以被大规模制造,文学应当进入车间的流水线吗?这倒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了,文学若是能大规模制造,是否还可以被称之为文学呢?毕竟我们深知,畅销书或可从思路手法相互效仿,但所有经典文学之珍贵之处都在于它们的不可复制性。也许终有一天文学要走上商品线,也许不会。无论如何,我们终将满怀热忱地期待着作家们的思想点燃文学未来的道路。
正如佩索阿在《惶然录》中所言,写下就是永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