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尔森·怀特黑德
美国时间2017年4月10日,普利策获奖名单公布,《地下铁道》获小说奖,科尔森·怀特黑德成为全美最忙碌的作家。2017年5月,他通过邮件接受了澎湃专访。
十七年前,科尔森·怀特黑德意识到,如果把那条著名的“地下铁道”写成真正存在的地下铁道,应当会很有意思。在美国历史上,“地下铁道”是18世纪形成,19世纪中期达到鼎盛的一个由秘密路线和安全屋构成的网路,据估计,有十万美国黑奴借由这一网路,在废奴主义者和盟友的帮助下,逃往禁止蓄奴的自由州,或邻国加拿大。“地下铁道”只是一个比喻,强调这一网路的秘密性,它并不一定是地下,甚至不一定是铁路,在后期,这一名词还可以指代帮助逃奴的废奴主义者。总之,它象征一条通往自由的小路。而怀特黑德试图让它成真:有地洞,有轨道,有站长。
但他也意识到自己还未做好准备。“就纯粹的技巧方面而言”,当时的他还不够好——“凿入奴隶历史是一件恐怖的事儿,我那会儿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个体还不够成熟”。
十七年来,这个灵感跟着他,“似乎把你唬得最厉害的那个灵感,你一直在躲避的灵感,正是你需要写的东西”。2016年,小说《地下铁道》出版,怀特黑德获得当年美国国家图书奖,次年获得普利策小说奖。他对澎湃新闻记者说,“那些你摆脱不掉的念头,那些一直跟着你的念头,证明了其自身的价值”。
《地下铁道》讲述了生而为奴的少女科拉从佐治亚州种植园一路途经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州、印第安纳州瓦伦丁农场,最后抵达北方,获得自由的故事。科拉的母亲梅布尔在她大约十一岁时逃离了庄园,再无音讯。正是在梅布尔的“成功”的激励下,科拉同意了同伴西泽的逃跑提议;加上朋友小可爱,三人一起逃离了庄园。然而不久后,三人的命运便产生了分歧。
逃亡故事有一个天生的便宜可占:好心的读者怀着对女主人公的同情,对她未知但必定多舛的命运牵挂在心,看到任何一点蛛丝马迹都会荷尔蒙飙升,故事读起来自然好看;然而如果作家过于依赖逃亡的悬念,悬念本身反而会变成陈词滥调,让人哈欠连连。而怀特黑德在悬念的拿捏上有分寸有克制,节奏张弛有度,在科拉线性的逃亡之旅中常常出乎意料地穿插一些其他人物的小传、回溯、揭秘,给这本选材、用语上颇有“古意”的小说增添了现代色彩。
怀特黑德对澎湃新闻记者坦言,西泽、梅布尔等人的“小传”是他在虚构土壤上进行的试点测验。“谁的故事更说得通,西泽还是小可爱,埃塞尔还是马丁?(有了答案后)我将他们扩写,追求最大化的戏剧、主题和结构上的效果。是紧跟着佐治亚章节揭露梅布尔的去向,还是把她挪到更后面?怎么样写最有助于整个故事?”
《地下铁道》的魅力,以及阅读它所带来的满足感,来自于它层次丰富的现实肌理,光谱式的全景扫描,以及对标签和固有印象的粉碎。
于是我们得知,在“蓄奴”之下,有无数以个人为单位构建起来的子集:既有特伦斯·兰德尔这样的大庄园主,唯利是图,“当黑色的血就是金钱,(他)知道怎样把血管切开”;也有西泽的旧主人这样的小农场主,一个守寡的小老太太,认为奴隶制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恶”,但教授奴隶知识与技艺,许诺在她死后给他自由。
同理,支持“废奴”的人也各怀动机和理念,南卡罗来纳州医院开展科学研究,诱劝获得自由的非裔妇女绝育,从而做到“去黑人化”;帮助科拉的地下铁道站长马丁的妻子埃塞尔,从照顾科拉的过程中获得教徒救赎愚昧人群的满足感;而建立瓦伦丁农场的约翰·瓦伦丁,从白人商贩的父亲那里继承到地产,他渴望通过教育,让黑人获得精神上的自由。
科拉沿地下铁道逃亡所经过的每一站,都代表了美国蓄奴-废奴历史上各方博弈、思想碰撞的艰难历程,因此每一站在高度写实的同时,也是富含寓意的精纯象征。虚与实从未如此紧密地相连过,怀特黑德对澎湃新闻记者如此解释他在历史与虚构之间的灵活跃迁:“历史学家得遵照现实。小说家却不用。这个故事的前提就是虚构的、奇想的——一条名副其实的地下铁道——因此打一开始,它就不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小说。我希望遵从‘真实’,而不是‘事实’。我又不会被某个‘历史小说家联盟’给踢出门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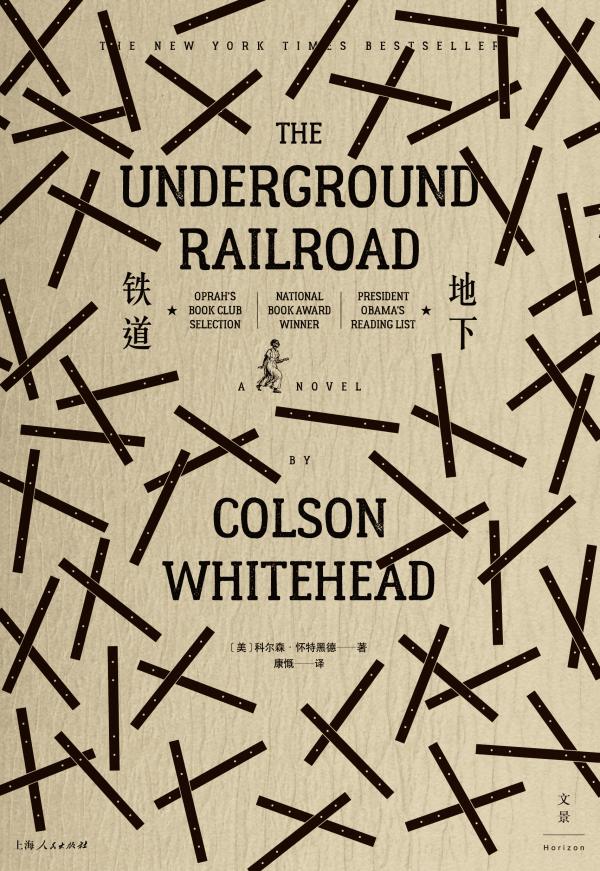
他以同等的勇猛跃入反派们的视角。猎奴者里奇韦的父亲是一名铁匠,既锻造钉子、马掌,也铸造奴隶主禁锢黑奴的铁链。在铁匠的眼里,铸铁是“侍奉神明”。痛苦于无法匹敌父亲,里奇韦在十四岁那年加入逃奴巡逻队,他信奉弱肉强食,认为白人占领美洲大陆,是美国的天命。
里奇韦对“神明”“天命”的误读乃至篡改让人警醒,从而意识到独立思辨之重要。从古至今,不同的群体像瓜分月球一样争夺着语言和文本的解释权。其中最为突出的例子之一就是宗教。蓄奴者信教,废奴者信教,黑奴也信教,上帝的肤色,从来不是一个小问题。谈起小说中埃塞尔和科拉对《圣经》进行的讨论,怀特黑德对澎湃新闻记者说:“在19世纪50年代,人们可以指着同一段《圣经》片段,说这是在支持蓄奴或谴责蓄奴。有的奴隶主认为宗教是一个工具,它给予奴隶关于更美好的来世的希望,因此让他们变得平和顺从;而另一些奴隶主则反对宗教,因为它让奴隶开始思考自由。”
提起描写逃奴的黑人文学,就不能不提到托尼·莫里森的《宠儿》。在写作时,怀特黑德的案前不仅有废奴主义者哈丽雅特·雅各布斯的著作《一个黑奴女孩的经历》、曾经受奴役的非裔美国人的口述史、非裔美国俗语字典,也有这本《宠儿》。在他动笔前,他心想,“我已经有三十年没读《宠儿》了,让我来看看托尼是怎么处理奴隶题材的。”他读了三十页,对自己说,“我完蛋了——莫里森他妈的是个天才,我可比不上她。”于是合上小说。然而这并没有将他吓退。“无论你在写什么——黑奴、战争、家庭——总有比你更聪明、更有才华的人写过了,并且比你写得更好。你只能希望你的主意和视角能带点新的东西进来。”怀特黑德对记者说。
他为这个充满悬疑和张力的逃亡小说注入了一种知识分子气质。书中瓦伦丁农场面临一个抉择,是继续留在蓄奴州印第安纳,变成众矢之的,还是向西迁,加入有色人城镇。农场管理者之一的明戈主张留在本地,不再庇护逃犯,追求渐进式的发展;而雄辩者蓝德则更主张西迁,包容逃犯,他认为瓦伦丁农场是一个妄想,但却是一个有用的妄想,而“一个有用的妄想有时要好过无用的真相”。
明戈和蓝德进行的这场以悲剧收尾的辩论很容易让人动情,它让人想起民国思想者对中国飘摇命运的思考;二者都是在黑屋中思考突破重围之出路。
怀特黑德对记者坦言:“明戈和蓝德的辩论受到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十九世纪美国废奴运动领袖),布克.T.华盛顿(美国黑人政治家、教育家)和W.E.B.杜波依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先驱、历史社会学家)的启发。保守路线和改革进步路线,哪一个更好,更能带领黑人崛起?”对于仍然存在种族主义、只是“进步了一点点”的美国来说,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开放性问题。
在蓝德口中,“美国也是一个妄想,所有妄想中最壮观的一个。”当问及“美国梦”与“妄想”的关系时,怀特黑德对记者答道:“我宁肯让文字来说话,但很显然,如果你的建国宣言里说‘人人平等’,那么当女性和有色人种不平等时,这就是一个妄想。只有当美国切身履行其推举的理念时,我们才离开了妄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