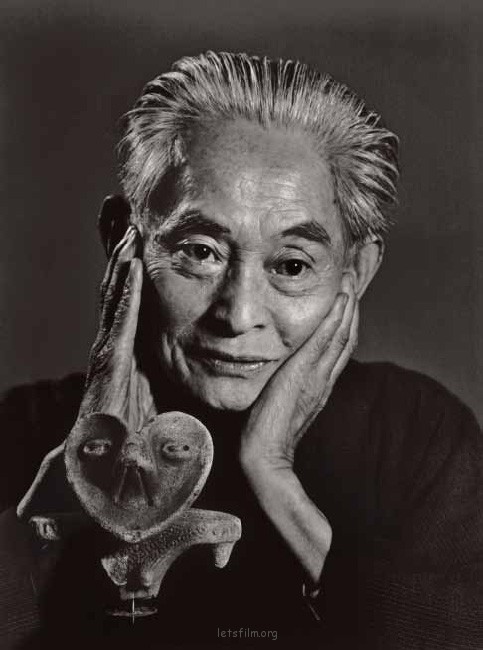
无法摆脱的哀愁
1948年11月12日,日本东京。今天,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对七名最重要的日本战犯进行宣判。
受《读卖新闻》的委托,川端康成前来参加旁听。也许是因为感冒的缘故,原本消瘦的他显得更加憔悴。此刻,他揣着怀炉心事重重地坐在旁听席上,像湖水一样雍塞川端康成整个身心的,是难以名状的忧愤情绪,那就是他说的:“日本人的残暴行为,受到惩罚,这是最大的耻辱。”被告席上的七位战犯表情各异,有的垂头叹气,有的麻木不仁。目睹这些曾经翻云覆雨的大人物此时的表现,川端康成竟然也一时难以辨别出“这是觉醒的救助呢,还是虚伪的逃避?”
目睹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之后,川端通过两篇文章《东京法庭上的老人》和《东京审判判决日》表达了他诸多悲欣交集的复杂心情。其中他在前文中情难自抑地愤愤写道:
这些人如此指导国家和民族,却不相信是愚蠢的。他们是国家动荡时期的得势者,他们把我们的过去放在被告席上。我看到他们作为无力的被告而受到审判,就对国家、对历史产生了怀疑。我觉得:想想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会有教益的。
然而对于日本必然战败的可悲下场,他有着强烈的预感。这种强烈的失败预感并非未卜先知,而是来自三个月前,他亲赴鹿儿岛鹿屋海军特攻队基地的一段采访经历。
1945年4月24日,位于日本九州的鹿屋海军航空兵特攻队基地,迎来了“海军报道班”的三位作家:川端康成、新田润和山冈壮八。所谓“报道班”是指战争时期,日本政府要求作家“奉公出征”,开赴前线各地采访撰写战地作品的一种动员组织。此时,日军在亚洲各个战场上已节节败退。从1944年的6月,美国就开始了对日本本土大规模的战略轰炸,盟军光复马尼拉、重返菲律宾、收复密支那,一路势如破竹,兵锋直逼掩护日本的最后一道屏障——冲绳。日本最后的崩溃,已近在眼前。
冲绳之战成为日军孤注一掷的困兽之斗。在战役展开前,日本当局为鼓舞士气,发动了强大的宣传攻势。全体国民再一次相信了日本军部掩耳盗铃的欺骗宣传,继续做着自欺欺人的黄粱美梦。山冈壮八在《最后的从军》中回忆当时的情形说:“那个时候——在失掉冲绳之前,国民基本上都还认为我们可能会打胜。至少没有人肯定地认为我们可能会战败。”
川端康成显然更加乐观。作为海军报道班的成员,他也坚信在“神风特攻队”的攻击下,不出十天半月冲绳一战就将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终。可等到他们赶到鹿屋海军基地,看到的却完全是另外一番绝望的景象。川端康成在1955年发表的《战败之时》里这样描述道:
然而到达之后,即使从侦查照片中也可看出,战争形势日益严峻。很明显我们已经没有了舰队,飞机数量不足。我滞留在水交社,将校服配上飞行靴,目送特攻队的出击。我无法忘记特攻队员,那其中有队员对我说你不该来这种地方,也有队员对我说还是赶紧回去的好。还有队员在出击之前拜托安部先生(能成氏,当时一高的校长)多多照顾我。机场遭到连日轰炸,已经几乎毫无抵抗了,只有待在防空洞里才是安全的。
战争结束后,川端康成对在鹿屋海军基地一个月的采访情形记述特别简略,他似乎有意回避谈论这段历史。在这难忘的一个月中,川端康成不但没有看到一点儿预期中的胜利迹象,反而深切地感受到日本处于战败边缘的惨烈悲凉。
在日本帝国行将灭亡的疯狂时刻,日本海军组织“神风特攻队”驾驶满载炸药的飞机,采取同归于尽的方式直接冲撞美舰,以挽救帝国日薄西山的命运。对于这种可怕的“集体自杀”行为,川端这样描述道:
在日本最南端的特攻队基地,特攻队员从各地的飞行队中空运回来,接着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出击。然后就有新的队员和飞机到达基地接着出击。补给消耗得十分剧烈,这里的规律是昨天的队员今天从基地消失,今天的队员明天就看不到了。
“神风特攻”是日本军国主义穷途末路下的疯狂之举,堪称近代战争史上的一大怪胎。那些狂热而绝望的特攻队员,每天都饱受着“等死”的漫长煎熬。作为富有同情之心的作家,可以想象川端康成一行耳闻目睹每天都在发生的战争惨剧,内心应该有着怎样一番矛盾纠结?
关于鹿屋基地的这次采访经历,川端康成十年后在《新潮》杂志发表《战败之时》自述道:
冲绳之战也没有希望了。日本即将战败,我忧郁地回来了。关于特攻队的报导,我一行字也没有写。
虽然这次的采访经历让川端康成早已预见了战争的结果,可当他真的有一天不得不直面日本战败的现状时,他内心的亡国之痛无可名状。他在《独影自命》中写道:
我不曾有过对日本像神一样的狂热和盲目的爱。我只不过经常地怀着孤独的悲哀为日本人感到悲伤。因为战败,这种悲哀渗透进了我的骨头。但是反过来它又使我的灵魂获得了自由和安定。
那么在整个战争期间,川端康成是否真的如他所言,逍遥世外,“不曾有过对日本像神一样的狂热和盲目的爱”?
满洲之行
1947年10月,川端康成在随笔《哀愁》一文中,这样描述战争时期他的生活状态:
战争中我在往返于东京的电车中和受灯火管制的被窝里阅读《湖月抄源氏物语》。这是因为我的眼睛不可能在阴暗灯光和摇晃电车中阅读小文字的缘故,当中也隐含着些许反抗时势的自我嘲讽。在横须贺沿线的战事愈加严酷的时节,阅读王朝时期的恋爱故事是件怪异的事情,但是车上的乘客却没有发现我的这种与时代错位的行为。我戏谑地想,万一途中遇到空袭受伤的话,这种结实的日本纸压在伤处应该些许有点用处的吧。
很难想象,在美军空袭的凄厉警报中,在灯火管制的黑暗夜幕下,川端康成却沉醉在描写男女恋爱的被列为战时禁书的《源氏物语》中。这种在别人眼里所谓的“非国民”行为,正如他自己所写的那样,的确是与时代氛围“错位”的怪诞举动。沉浸在这样一种超脱的境界里,川端康成认为“这是一种摆脱战争色彩的美”,是他自己“对时势的反抗和讽刺”。对于自己和战争的关系,川端后来在随笔集《独影自命》中表白道:
我是相对来说没有受到战争太大伤害的日本人。我的作品在战前战中战后并没有很显著的变化和断层。我的创作和生活都没有因为战争受到太多的影响。
对于川端康成的这种表白,战后许多研究者都深表认同。他们普遍认为战争期间,川端康成如同闲云野鹤,保持的正是这样一种“躲进小楼成一统”的独立状态,在日本的“传统美”中坚守着文学的纯粹性。他既没有投身战争风潮狂热地鼓吹“圣战”,也从未创作发表过肯定和赞美战争的言论,他只是一位置身事外的逍遥看客。借用日本学者羽鸟彻哉的说法就是——“川端在战时所发挥的作家的努力,只是悲痛地凝视着消逝在历史潮流中的一个个可怜的生命。”
那么,在整个日本战意高扬的疯狂时代,川端康成真的能做一位远离是非的观众,能始终问心无愧地出淤泥而不染吗?
历史总能于无声处听惊雷,从小细节处看到大关节。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李圣杰博士在《关于川端康成的战争体验》一文中披露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细节,顿时让人有恍然大悟之感——原来,此川端非彼川端,他对于战争的态度和行为,并非人们想象中那么坦然自若!
最为微妙的故事发生在1955年。日本战败十年后,川端康成在《战败之时》这篇作品中,刻意抹去了两个人的名字:村松梢风和火野苇平。然而,就在《战败之时》发表的前一年,川端在自己编制的“年谱”中,还明确记载了他和这两人在“满洲之行”中的交往经历——
1941年4月,川端康成和著名棋手吴清源、围棋评论家村松梢风一起到中国东北出席《满洲日日新闻》主持的围棋大赛。其间川端康成和村松梢风共同观战了围棋大会,接着又奔赴吉林和奉天、哈尔滨、大连等地,两人还一起在广播电台做了对谈节目等等。对于川端康成来说,一直同行这么久的村松梢风不可能是被无意间遗忘的。同年初秋,川端康成又受日本关东军的邀请,与山本改造社长、高田保、大宅壮一、火野苇平再次前往中国东北,飞赴黑河、海拉尔等地。在军方的安排下走访了学校、煤矿、工厂等,慰问各地的陆军部队和开拓村,出席各种座谈会和演讲会。川端在《渡满叶书通信》中还回忆到:“这次春季回国坐的阿根廷号,是艘旧船。很是期待前往北方。在船里和火野君下围棋输了两局。”此外,还有川端康成和火野苇平公开发表的合影为证。
但令人奇怪的是,对于这两次、前后长达4个月的考察,川端康成为何要讳莫如深,甚而采取掩耳盗铃似的方式加以切割呢?
原来,1932年,作家村松梢风以川岛芳子为原型创作的小说《男装的丽人》发表,在日本风靡一时。但好景不长,随着日本战败,川岛芳子被捕。据村松梢风的儿子村松瑛回忆:“梢风曾说川岛芳子是说谎的名人,那些谎言听起来十分真实并且很有趣。”
正是这些“有趣”的描写,在战后成为中国政府判处川岛芳子汉奸罪的证据之一。1947年7月3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日报》登载了对川岛芳子的起诉状,其中第八条这样写到:“日本人村松梢风的《男装的丽人》中,具体地证明了被告的间谍行为。”那些为川岛芳子鸣冤叫屈的日本人,便一齐声讨正是村松梢风的小说将芳子逼向了死刑。川岛芳子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这样的指责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诛心之论。但战后川端康成为何也顾及舆论,对受人非议的村松梢风避之不及?这其间的缘由似乎不言而喻:川端康成不想和这样一位与侵略战争密切相关的人物牵涉过多,以恐引起有些人不愉快的联想。
而川端康成有意识地淡化“满洲之行”的经历,还隐含着对于自己在战争期间某些行为复杂不安的隐秘心情。正如他本人所述,两次“满洲”的考察体验给他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归国后他在《满洲国的文学》中写道:
在满洲到北支的旅行后,有两年左右工作起来很困难,我想是由于这个时期旅行给我心灵带来的振动过于强烈的缘故。
在中国东北亲眼目睹了开拓团和工厂里中国女工的悲惨境遇后,川端的心情久久无法平静。他曾希望创作一部以“满洲”毛织公司厚生工厂为题材的作品,但由于时局动荡的原因,这一构想最终未能实现。回国当年他写了《满洲国文学》和《满洲的书》两篇文学杂感,次年又编辑了有关“满洲”的两本书。但这些文章和选集都对他所见到的中国人的悲惨遭遇只字未提,他自觉地“遗忘”了日本发动这场罪恶战争带给中国的苦难,仿佛那些挣扎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从未在他的记忆中出现过一般。相反,川端康成留下的另一些白纸黑字,却清楚地记录下“满洲之行”中被他“健忘”了的事情。
1941年4月,当川端康成访问中国东北时,正值“伪满”皇帝溥仪按照日本内阁决定的《满洲国指导方针纲要》要求,强迫东北青少年接受日本奴化教育,实现“日满一体化”。川端康成看到“伪满”的小学生竟然没有用日文写作时,就感到“惊叹”,特别提醒日本当局“孩子们的灵魂是最应开拓的处女地”,还大声呼吁“开拓移民并不限于农业。我看到在各个领域工作的日本姑娘,最需要的是好的女教师”。在川端康成的意识深处,“满洲”并非日本统治下的殖民地国家,而是实现所谓“五族共和”理想之下的“王道乐土”;而他大力提倡在“满洲”推行日语教育、建构独立的“满洲文学”,自然不算是从思想上分裂奴化中国的罪行,而是协助日本政府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善举了!
除此而外,川端康成针对日本军部的“大东亚理想”忧心忡忡地指出:“我们最大的朋友,最大的敌人,唯有汉族。”他所说的“最大的朋友”,专指“伪满”政权和汪伪政权管辖区内亲日的“汉族”;而“最大的敌人”则指中国的抗日“汉族”。因此,和“最大的朋友”来“共同完成大事业满洲国是至关重要的”(李圣杰:《关于川端康成的战争体验——以<战败之时>为线索》,文明信、母丹翻译)。
川端康成的两次“满洲之行”,都受到日本关东军的热情接待。他确实并没有因为“吃人口软”而直接发表歌颂战争的言论,更没有充当为军国主义摇旗呐喊的急先锋。这使许多人误以为川端康成从未“顺应时局”,而是采取了“沉默的抵抗”。但随着战争进程的深入,川端康成内心那种无比深厚的“日本情结”,已逐步受到时代风潮的蛊惑而发生变异:极度崇尚日本传统美与“皇统崇慕”的愿望纠结相汇,使他将侵略战争与日本的未来、对天皇的尊崇连在一起,思想开始飘移倾斜,促使他对战争的态度从迷惘到接受、从屈从到肯定。他既想拼命逃离政治,又不自主地开始与日本当局合作。
当川端康成把侵略战争作为日本人的命运最终接受下来,坚守多年的文学阵地已悄然失守,事实上他已充当起日本军部“文化侵华”的一个过河卒子。
既是风也是水
至于被川端康成在战后作品中故意删除的另一个人火野苇平,两人的交往历程则更加耐人寻味——其间折射的正是川端对于战争态度的嬗变历程。
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期间,火野苇平可谓大名鼎鼎。他因创作了《麦子与士兵》、《土地与士兵》、《花儿与士兵》三部作品,成为红极一时的“军队作家”。日本投降后,由于火野苇平与众不同的影响力,日本共产党的《赤旗》报将他指定为“第一号文化战犯”。1948到1950年,火野苇平作为“战犯作家”受到严厉追究。川端康成创作《战败之时》一文时,正好是侵略战争结束十周年,此时火野苇平虽已被取消“战犯作家”的处分,但毕竟是一名曾经大力鼓吹侵略战争、战时污点十分突出的“军队作家”。川端康成刻意规避与火野苇平的关系,目的就是要撇清和这种“污点人士”的联系。
战前战后,川端康成对火野苇平的态度曾经几度“变脸”,可谓正是他对待侵略战争自相矛盾的心态晴雨表。
战争结束后,川端康成对火野苇平如同“躲瘟神”一样避讳。但在战争期间,却曾对火野褒扬有加。1943年12月10日,川端康成在《东京新闻》发表《英灵的遗文——壮美之<皇兵>》一文,就拿火野苇平的纪实作品当做成功范例,对“战争文学”作了一番阐释论述:
火野氏的战争文学正是从这样的日记和书信中诞生的,而出征的将士又是抱着这样的心情写下了日记和书信……优秀的战争文学,是整理好的战史的一方面,而由出征将士所写文章整合而成的战争记录,也应该当做国家的财富、民族的财富而流传万世。
所谓“英灵的遗文”,是指战争期间川端康成主动怂恿某个出版社所做的一项大型出版工程,即把一些在侵略战争中毙命的日军士兵“遗文集”,包括他们的日记、书信、诗歌,以及他们亲属的慰问信等编辑出版《英灵遗文集》,用以宣扬所谓“圣战”和忠于“皇道精神”。川端康成把这样一部充满侵略血腥的书,鼓吹成“日本精神的结晶”,同时颂扬道:
这种殉忠精神的纯洁性是庄严悠远的,而且是悲愿极致的,所有这些英灵的遗文,就是这种日本魂经过战争而净化了、闪光了。
他雄心勃勃地鼓动出版社按照诸如“上海卷”、“南京卷”、“汉口卷”等战场划分,抑或按照部队序列为类别进行编纂。此间每逢太平洋战争周年纪念日,川端康成还应报刊之邀撰写所谓“纪念文章”,向在侵略战争中丧生的士兵表示哀悼致敬。战争后期,可以说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行动上,川端康成的调子已经同日本当局基本靠拢了。
如果时光回溯到战争初期,就会发现川端康成对火野苇平的态度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1938年8月,名不见经传的火野苇平凭借《麦子与士兵》一炮走红,在日本文坛迅速刮起了一股“报国文学”的逆流,响起了一片军国主义的鼓噪声。面对这股逆流,川端康成内心产生了强烈震动。就在日本文坛众口一词追捧火野苇平的喧嚣声中,唯有川端康成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他对火野苇平不但没有丝毫欣赏之意,反而公开撰文表达鄙夷不屑,对军部一手扶持炮制的“战争文学”表示讨厌反感。1938年8月22日,他在《东京朝日新闻》发表评论,以极为尖锐的语气批评道:
我吃惊地感到,近来的小说很是无聊。由于战争,作家也跃跃欲试,这虽然是很自然的事情,但这不也正是文学精神的堕落和衰退吗?……身为作家,在战场上如何谈得上文学?简直是胡闹!
同年,他在9、10月的“文艺时评”所写的或明或暗的批评质疑中,也表达了对流行文坛的所谓“报国文学”的反感之意。
风起于青萍之末。“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当局向法西斯道路狂奔而去,实行白色恐怖的军部和政府对进步作家的镇压进一步加强。思想文化的绞索越套越紧,许多反对侵略政策的作家和学者被禁止执笔,日本军部威逼利诱作家们去鼓吹所谓“报国文学”,战争阴云笼罩下的日本文坛进入最黑暗的时期。面对日本文坛“万马齐喑”严峻局面,川端康成于1936年1月写了《告别“文艺时评”》一文,他失望地批评道:“泛读每月的小说,已经不仅是一种无效的徒劳,而且是一种精神的堕落。”他呼吁作家们不要在一夜之间写出粗糙的战争文学,以免留耻千载。他还在另一篇“文艺时评”中感叹“现在连自由主义作家也几乎无人写出多少有点进步或有点良心的作品了”。于是他愤然宣布中断已经连续写了十几年的文艺时评,表达他对战争体制下的“国策文学”的一种独特抵制(叶渭渠:《东方美的现代探索者——川端康成评传》)。
川端曾在《文学自序传》中这样解剖自己在战争时局中的表现:
只是,我能自我辩护的,是我随波逐流,顺风来顺水去,而我自己既是风也是水。
川端康成这种左右飘移的状态,看似他为逃离政治漩涡所找的无奈借口,其实是随着时局的变化,不断妥协退让的一种无奈选择。
最消极的合作,最消极的抵抗
川端康成战后在《天授之子》一文中说:“我对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日本,是最消极的合作,也是最消极的抵抗。”但进入战争后期,他连“最消极的抵抗”也不可能了。
在法西斯高压政策下,摆在日本文学家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像宫本百合子、西泽隆二等反战人士一样甘把牢底坐穿,也要保持高洁节操;要么就是顺应形势,被迫参加到协助侵略战争的行列。从前那种所谓“艺术的抵抗”已经完全没有空间了。于是,自认为“没有受到战争影响、也没有受到战争损害”的川端康成在“文学报国会”成立一年之后,他的名字也被赫然列在“文学报国会”花名册上。在举国支援战争的狂潮之下,日本作家总共4000多人参加了“文学报国会”,没有参加者凤毛麟角,甚至先前反战的人也有一部分开始赞同战争,并将“共荣”视为“摆脱欧美列强压迫”、“解放亚洲”的绝佳途径。
战争后期,日本已经内外交困。近卫内阁以达成“国防国家”为目标,于1940年10月12日宣告成立“大政翼赞会”。该组织将日本全国所有家庭纳入110多万个“领组”严格管控,实行下级服从上级、组内互相监督,形成“一君万民”、“万民翼赞”的军国主义“总体战”体制,以武士道的绝对服从精神统治全体国民意识,尤其将日本广大妇女动员起来,通过塑造一批所谓军国之母、靖国之妻的“模范典型”,号召国民继续为苟延残喘的侵略战争无偿买单,盲目牺牲。
在这样的背景下,1942年10月,川端康成听命于日本当局的安排,受“日本文学报国会”的派遣,同《读卖新闻》一名记者到长野县郡松桦尾村的贫苦农妇井上傅家采访,为宣扬“国策”体验生活。井上傅的丈夫被迫充当了侵华战争的炮灰死于前线,小叔也被征召入伍。家中上有白发老母,下有未曾见过父面的幼女。井上傅像千千万万的日本贫苦农民一样,不仅要肩负起本应属于男人承担的繁重农活,艰辛地养活一家老小,还要负担政府强硬摊派下来的沉重税赋。漫长的战争压弯了这位农妇的双肩,她如同一片风中枯叶苦苦挣扎在生死边缘。
然而川端康成经过短暂采访后,很快写出了《日本的母亲》一文,浓墨重彩地宣扬井上傅“妇女勤劳报国”的“光荣事迹”。接着又写了《访日本的母亲》。川端康成不仅无视侵略战争给井上傅这样的无辜平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描写她们的痛苦悲哀,反而竭力渲染说这个家庭“没有阴影也没有不安,家属的面色充满和平与希望”,“家中气氛是明朗而和蔼,生活是愉快的”。川端康成如此美化战争摧残下的日本现社会,罔顾事实已达顶点,和他曾呼唤坚守的一个作家的良知早已背道而驰。令人难以想见的是,1944年川端担任了日本文学振兴会“战争文学奖”评委,在评奖活动中明确主张作家多写“战争文学”,为“大东亚圣战”助威。
然而这样的违心之举终究要受到良心谴责。1945年8月15日,听完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广播后,川端康成担心盟军占领日本之后,会加强新闻出版的检查制度,便一个人悄悄把他主持的“镰仓文库”租书屋收藏的左翼和右翼图书,统统付诸一炬。与此同时,他还将自己在战争末期写就的《英灵的遗文》和有关感想全部收藏在箱底。对于即将到来的盟国占领军,川端康成心中充满了某种担心秋后算账的不安情绪。就川端康成来说,“亡国末世”之民不仅意味着在战争中的失败,还意味着战败的日本在西方民主浪潮冲击下,传统文化精神的崩溃和缺失,这才是川端感到日本最大的悲哀,而众多的日本人对此却混沌无知。
在这种普遍的沮丧消沉状态中,川端康成既看到国家战败的衰亡,痛恨战争的悲惨,也看到战后日本再生的希望;他既摆脱不了“内心的悲哀”,“不相信现实的东西”,也痛切地感到“要回到古老的日本去,又要面向宽阔的世界前进”。而日本要获得新生,就必须对惨痛的战争进行深刻的反思。川端康成毕竟是一位世界级的伟大作家,日本战败后他的思想和作品都重新获得涅槃飞升,呈现更加复杂的思想倾向,与战前相比有了新的探索和创造。拥有一颗“执拗的爱美之心”的川端康成,努力表现“日本传统的美”,其实是要努力寻找战败后日本人早就已失落的精神家园。对传统文化、传统美不遗余力的追求和描绘也恰好掩饰了川端康成内心的凄凉和寂寞。战后的川端没有简单地停留于描写战争的残酷,抒发内心的愤懑,他的目光穿透了过去,凝视着现在,同时也投向了未来,这正是川端康成与众不同的深刻之处。他曾在战争中迷惘过、矛盾过、挣扎过,但这些最终都未能遮住他作品的文学光芒。当文学遭遇战争时,当作家的责任良知与国家意识发生强烈冲撞,川端康成的心理流变过程为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思索空间。
1972年4月16日,川端康成突然离开人世。在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三年多之后,川端康成却在荣誉的巅峰采取自杀的形式离开人世了,这令世界文坛都受到极大的震动。川端康成生前未留下只字遗书,他想留下的话,其实早在1962年就已经说过了:
“自杀而无遗书,是最好不过的了。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
摘自《文学自由谈》2017年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