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著名艺术批评家、作家、画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2017年1月2日在法国病逝,享年90岁。作为当今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苏珊·桑塔格也曾表达过对约翰·伯格的尊崇并热爱——“在当代英语作家中,我奉他为翘楚……他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与思想者。”约翰·伯格在视觉艺术欣赏领域拥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改变了一代人观看艺术的方式。
评论人马小盐认为,约翰·伯格是继本雅明、巴尔特、桑塔格之后,又一位对影像艺术如痴如醉的批评家。而在其关于“看”的著作中,名气最大的《观看之道》并非最好的,《另一种讲述的方式》《看》《毕加索的成败》《约定》都要更为厚重与深邃。同时,在艺术批评的光芒下,伯格还是一位拥有巨大才华的小说家,严谨的理性思维一点也不曾伤害到他柔软的感性经验,稍纵即逝的感性经验亦一点也不曾抵触过理性的严谨。无论影像理论,还是小说艺术,伯格都深受本雅明的影响。他的离去,对这个世界而言,某种程度上也是文化塌陷的一种隐喻。
伯格,一位著述丰盈,批评、绘画、小说领域皆有超俗表现的文化大师,元旦刚过,便匆匆离世。相较2016年(2016年2月,埃柯离世),伯格的离世,似乎预示着2017年的文化气候,将会更为寒冷。文化巨擘的消逝,对这个世界而言,往往是文化塌陷的隐喻。我们身处塌陷之地,唯有目送那些曾在我们的灵魂里留下深深文字印记的前辈就此远去。
我读伯格,是在2010年左右,当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伯格的一套丛书。这套丛书里,令我惊喜的反而不是他的理论文集,而是他的小说集《我们在此相遇》。这本小说集,按传统的文体分类,似乎不属于小说,而是一本卓绝的随笔集。实际上这本集子是典型的跨文体写作:整部作品间于真实与虚幻、小说与随笔、当下与追忆之间。以个人经验为底色的半回忆录小说,在世界范围内写得如此诗意优美的并不多见。在我看来,这本小说结构上的地志学写作可与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相媲美,编织语言丝线的记忆术则可与纳博科夫的《说吧,记忆》一比高低,只是纳博科夫用循环往复的长句编织着他的记忆神毯,伯格则是长短句兼而有之。

《我们在此相遇》,是一本追忆逝者之书,也是一本追忆自身消逝时光之书。整部小说在书写消逝而去的人物与安放人物所处的空间意象之间,处处匠心独具。伯格将他记忆里的每一位值得追忆的逝者,安放在一个与逝者精神气质完全吻合的城市之中。这是一种令人吃惊的地志学写作方式。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所有的人物与城市都是虚构的,伯格这本小说中的所有城市与人物却是真实的存在。这种真假参半的叙事方式,比起纯虚构更有挑战性。这显然是一位艺术批评家给予自身小说文本特意制造的一道难题,也只有批评家才会以一种美学的分类法来书写小说。整本小说,语言轻盈,情感哀伤,虚构奇丽,一些段落读起来宛若在阅读不曾分行的诗歌。读完合上书籍的刹那,令人震惊的同时怅然若失。伯格的这本小说,对我而言,是秘而不宣的珍宝。今天,他已远消逝,让我再次复述当初阅读它时给予我难以解释的阅读经验,唯有一个词:震惊。
在我看来,国内关于伯格文本的翻译,由于偏重其艺术批评家的光芒,遮盖了其作为小说家的巨大才华。到目前为止,关于伯格的小说翻译,我只读到《我们在此相遇》这一本书。事实上,伯格是一个非常会讲故事的人。这一点,他深受本雅明《讲故事的人》一文的影响。本雅明把讲故事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定居者,一类是旅行者。早年生活在英国,中年之后移居至法国阿尔比斯山下的一个小村庄的伯格,定居者和旅行者的身份皆而有之。在那个小村庄里,他既是一个前来定居的人,也是一个异乡人来的“讲故事的人”。我期待在国内,早点看到伯格其他小说的汉译本书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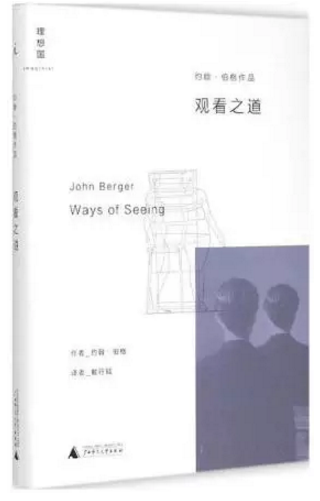
伯格的《观看之道》,是在世界范围有着巨大影响的文论集。事实上,这本文集是伯格与他人合著(共五人)的一本影响范围很广的关于“看”之理论的文集。它原本是伯格为BBC策划的一系列关于“看”之艺术的电视节目,后因节目播出后广受欢迎,从而特意扩充整理而成的一部集子。在我看来,仅就影像理论而言,《观看之道》并非伯格最好的著作,这本书之所以知名度高,是因当时搭乘了电视媒介的飞扬之翼。事实上,伯格所著的《另一种讲述的方式》《看》《毕加索的成败》《约定》比《观看之道》更为厚重与深邃。前两本著作伯格侧重于对摄影的阐释,后两本的重心则倾向于绘画艺术,《毕加索的成败》一看标题便知,是一本专门论述毕加索画作的批评文集。我想,伯格的这四本书,是每一位负责任的艺术批评家的必读之书。当然,那些在中国艺术批评界浑水摸鱼的艺术批评家,显然不在此列。
伯格是继本雅明、巴尔特、桑塔格之后,又一位对影像艺术如痴如醉的批评家。他一生的批评文本,都在强调“被看到”,在强调“看”的独特经验,在强调“看”之表象本身。这种对“看”的痴迷,最初源于他对绘画艺术的热爱。伯格不但是一位对色彩敏感的画家,还是一位绘画教师。在22岁到29岁的青年时期,长达七年之久,他的主要职业便是给学生讲授如何绘画。他对“看”的敏感,应该源于早年的人生经历。26岁左右,伯格在给学生教授绘画的同时,开始给伦敦激进的左派杂志《NEW STATESMAN 》(新政治家)撰稿,并迅速崛起,成为英国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批评家。在流行一时的共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伯格成为一位秉持左派信念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为农民与工人鼓与呼,他信仰共产主义,他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徒。
无论影像理论,还是小说艺术,本雅明对伯格的影响,宛若父于子的血脉相承。同样是本雅明文本的传承者与阐释者,比起阿甘本哲学理论的晦涩,伯格的批评文本更为明晰与清澈。这也是伯格在国外,深受大众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伯格的批评文本,对我国大众而言,似乎已经无比晦涩,因今天他去世的消息,很少看到普通读者惯性的点蜡烛。这种现象,一方面显示出民众正在学习着不盲目跟从,另一方面则说明,伯格这个名字,比起桑塔格,对中国很多读者而言,显然无比突兀与陌生。
伯格一生,左手理论,右手小说,严谨的理性思维一点也不曾伤害到柔软的感性经验,稍纵即逝的感性经验亦一点也不曾抵触过理性的严谨。感性与理性,在伯格的笔下彼此互补、完美互融。比起桑塔格被理性严重殇饬的颇显固化的小说文本,伯格的小说文本更为柔软、优美与诗意。伯格曾言:大多数故事以死亡为开端,从这个意义上讲,讲故事的人是死亡的秘书(大意如此)。在我看来,伯格本人,便是一位将批评文本与小说艺术完美结合的死亡秘书。我相信,作为一名死亡的秘书,即若在公众的视野消逝,亦从未真的死去。他会在很多年后,在与心有灵犀的阅读者的惊喜相遇里,再度从纪录下来的文本中,翩然复活。
文章来源:凤凰文化原创栏目《洞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