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茨杰拉德猜到了一心想成为名流会落得什么下场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6:11:00 澎湃新闻 克莱夫·詹姆斯 参加讨论
关键词:菲茨杰拉德  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1896—1940)的人生是一个警示故事,但这个故事更多是关于我们而不是他。他饱受一段光鲜却失败的婚姻折磨,喝酒自毁,与此同时还要写二流作品来付账单,迷失在好莱坞那个注定会挫败他最后一点创作力的生产体系中,他成了无数关于文学天才如何荒废的新闻故事的焦点。他在多篇自我鞭笞的文章中最早为这种做法发出了信号,这些文章后来被他的朋友埃德蒙·威尔逊整理收入文集《崩溃》(The Crack- Up ),这部作品文风直白,充满了对危险的创作生活的真实记述,无疑是一本值得阅读和记住的书。不过,我们最好先读一读并记住(事实上是熟记)《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夜色温柔》。否则我们可能会荒唐地以为,作为最重要的现代作家之一,菲茨杰拉德的整个创作生涯都在为他颇具警示意义的崩溃作准备。传记作者的后见之明难免会贬低传主的远见。正如他那两部伟大的小说所证明的那样,菲茨杰拉德非常清楚明星文化是民主体制的一个缺陷,它把天才变成可操纵的传奇故事,并通过这种平均化的机制带给我们安慰。假如他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之后没再写其他任何东西,这本小说仍然是二十世纪最有预见性的书之一。菲茨杰拉德猜到了一心想成为名流必定落得什么下场:游泳池里的一具死尸。 优美的风格不可能产生,除非你每年从五六个一流作家那里吸收养分。更确切地说,风格形成了,但并不是下意识地融合了你所领会的所有文风,而只不过是你上次读过的作家的反映,一种稀释过的新闻体。(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给他女儿的一封信,埃德蒙·威尔逊在《崩溃》中引用了这段话,第296页) 我第一次读这两句话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病痛中的作家写给十来岁女儿的话依旧让我感到由衷的兴奋和认同,当年读到这里时,我忍不住起身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激动地喊着“是的”!此刻我坐在椅子上没动,可是在形而上的意义上我还是一样被它们感动。菲茨杰拉德是在1940年写的这封信。那时他已经把身体喝垮了,事业每况愈下:他竟然相信好莱坞的工作帮他渡过了难关,而不是让他越陷越深。(此处要赶紧补充一点,这并不是好莱坞的错:有的作家可以同时做到既忠于自己的天赋又满足电影公司的要求,但菲茨杰拉德不可救药地缺乏保存工作精力的意识,这是他的诅咒,或许也是他的福祉。)但他还没糊涂到不想把自己扮成智者,给女儿留下好形象。当然,从长远来看,这是个天大的笑话:他确实是智者。巨大的失败造就了他的智慧。只有伟大的艺术家才会有巨大的失败,而菲茨杰拉德太了不起了,他甚至可以把致命的个人缺陷变成诗歌的素材。《崩溃》中收录的杂志文章让崩溃也显得值得:他的神经濒临崩溃的时刻,正是他的文风最接近完美流畅的时刻。这很明显,因为他的文风一向连贯自如。菲茨杰拉德似乎从练笔之日起就形成了一种格外自如的风格,也是他自己独特的风格:一种理想的自然平和的笔调,节奏感是那么恰到好处,以至于读者相信他们自己的旋律感在词组到词组、语句到语句和段落到段落的流动中得到了回应。我们真能相信他之所以有自己的风格,是因为他阅读了大量其他文体大师,吸收并融合了他们各种各样的影响,而且设法剔除了残留的痕迹,甚至包括最近刚刚读过的那些东西的残存影响吗?这让人难以置信。埃德蒙·威尔逊捍卫并弘扬了菲茨杰拉德的声誉:事实上,是他挽回了菲茨杰拉德一落千丈的名声。《崩溃》这本珍贵的文集就是威尔逊编辑出版的,前言中是他写给菲茨杰拉德的深情的送别诗,开头是:“司各特,你最后未完成的文稿我今晚整理……”:在我看来,这首诗是真正的现代诗歌之一,而且因为不合时宜而更有价值。《崩溃》也选录了部分信件,我在里面第一次读到上面引用的那句话,那时我还没从《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夜色温柔》带来的震撼中缓过神来。这两本书总是让人印象深刻,而最初的强烈触动让菲茨杰拉德成了整个世界的中心:任何有关他的消息都极其敏感,而且那个时候——五十年代末——几乎总是威尔逊在发布消息。威尔逊没有指摘菲茨杰拉德的才华,可他确实把菲茨杰拉德描述成一个笨头笨脑的学生,跟瑟伯在大学回忆录中对橄榄球员博伦虬茨威克兹的形容不无相似之处:他“虽不比公牛笨,但也好不到哪里去”。就此而言,威尔逊笔下晚熟的菲茨杰拉德没什么太大变化,就像当年那个年轻的普林斯顿大学生,对语言全凭感觉,最早拼凑起来的一些书显然是受了高明不到哪里的康普顿·麦肯齐的影响。回过头来看的话,威尔逊对自己这个不开窍的同班同学的慷慨褒奖倒有点像转弯抹角的攻击:他赞扬那个了不起的男孩,但前提是那个了不起的男孩总也长不大。按照威尔逊的说法,菲茨杰拉德虽然天资过人,却并不很严肃。威尔逊把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作了常有的对比——这个对比一直很常见,不过威尔逊是最早用它来阐发教训的人之一——他认为海明威会为了艺术饿肚子。言下之意,海明威有上流社会无法扭曲的资质。好莱坞可以把海明威的书拍成愚蠢的故事片,而海明威甚至也可以写让好莱坞感到有利可图的愚蠢故事,但至少海明威不受好莱坞工作的诱惑,也没有非在那里工作不可。海明威对文学是严肃的。他对文学懂得更多。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都是作家,但海明威也是读者。继续看菲茨杰拉德给他女儿弗朗西斯的信,我们倾向于认同上述说法。菲茨杰拉德问她最近有没有读什么好书,而他在一系列信件中提及的作家作品算是提供了一张点到为止的书单。里面有一些很好的作家,菲茨杰拉德显然相当仔细地读过:亨利·詹姆斯、屠格涅夫、德莱塞、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易卜生、D.H.劳伦斯、福楼拜和托马斯·曼等等,他都研读、分析和比较过。但在其他方面,这个单子相当混乱。当时好莱坞流行“左倾”,所以《共产党宣言》被包括在内不足为奇,但是当他推荐《震撼世界的十天》(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时,你会开始感到纳闷。如果菲茨杰拉德那么晚才开始读当代政治方面的书籍是为了给自己补课,那么他认为尚且年轻的女儿也应该读,这里面肯定有某些缘由;可是就文笔而言,《震撼世界的十天》乏善可陈。当时有些美国记者和非虚构作家的文风值得学习:威尔逊、门肯,甚至也包括乔治·让·内森,尤其是内森对语言修饰的狂热还没有把他的文字大厦压垮的时候。有一些文化记者后来无可避免地过时了,因为他们报道的内容已经被完全吸收,而他们报道的方式从未特别到值得长久留存:你可以把吉尔伯特·塞尔迪斯归在此类,还有古怪的詹姆斯·吉本斯·赫尼克。(在我看来,颇受埃德蒙·威尔逊青睐的保罗·罗森菲尔德没什么好说的:虽然他写现代音乐的文章奇特有趣,可他基本上相信爵士乐只要还掌握在黑人手上,就会永远无足轻重。)但约翰·里德即便在他那个时候也属于根本写不来的那一类。在《震撼世界的十天》中,他有全世界最重大的素材,却没有讲故事的本领。克里姆林宫的城墙把他压在下面,而读者也感到了同样的重量。对菲茨杰拉德来说,作品是完成硬性任务还是才华展现应该一望而知。因此,菲茨杰拉德觉得应该把里德那部名气很大而质量欠佳的作品归为好书,可能是因为政治立场的因素。这实在有损他的声望。我们不得不断定,菲茨杰拉德不仅拒绝把自己的文学判断绝对化,他也认为自己必须服从某种绝对化的标准——要是他能弄明白是什么标准就好了。 菲茨杰拉德说的是真的,只是真相更多在我们手中,而不是在他那里。考虑到他讲话时的处境,自欺并不罕见,随之相伴的自夸也一样。菲茨杰拉德酗酒已经到了只喝啤酒就觉得自己是在戒酒的地步。(那时的美国啤酒酒精度数很低,但他都是成箱买的。)同样,他认为自己还是一名认真投入的文学家,也许只是因为他记得自己在所有那些派对上是做过计划的,第二天醒来就要系统地阅读学习,然后在宿醉期间也做过同样的计划。相比而言,海明威的确是更严肃认真的读者,虽然他对自己的成就有些夸大其辞,这也显示了菲茨杰拉德在这方面是多么谦虚。《非洲的青山》中的爸爸在篝火边声称他要和托尔斯泰平起平坐,那副故作姿态的样子有些可笑。他的说法实在尴尬,但其中暗含的作家本人熟读托尔斯泰,这却是事实。海明威对托尔斯泰的作品几乎了如指掌,但他并不张扬自己对托尔斯泰的热衷——别忘了,这种热衷的前提是谦卑。海明威对罗纳德·弗班克的称赞可不只是讨好。像埃德蒙·威尔逊和伊夫林·沃这样背景和兴趣完全不同的批评家都曾发现,海明威安排对话的技巧是悄无声息地从弗班克那里搬来的。海明威这个粗脖大汉和面色苍白、衣着考究、敏感地藏在沙发里的弗班克:两个截然不同的作家看上去不可能有什么关联。其实,他们之间可不只是关联那么简单。弗班克对海明威的影响就像菲茨杰拉德在他信中讲的——吸收养分。菲茨杰拉德那番说教的潜台词,是你必须从众多名家那里吸收精华才能得到良好的影响。如果你只受一个人影响,那一定会有痕迹,而吸收养分的核心在于不留痕迹。不过,菲茨杰拉德的不留痕迹依然有不曾受到任何真正影响的嫌疑:他独特的文笔基本是与生俱来的。他建议女儿好好读书,是因为他自己当年总是逃学,而且由于逃脱了惩罚而感到更为羞愧。菲茨杰拉德自己练就的文风,主要特征是去除了错综复杂的套路。孟德斯鸠在他的性格形成时期也是这样:他生性容易被名家的表面魅力所感染,但是他的艺术天性克服了那些巨大的影响,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凝练的风格,即使思想浓度极高的时候也清新流畅。或许可以说,这些强大的作家不需要任何榜样的影响:他们只要遇到一些范例,向他们展示自己一直渴求的不加雕饰的表达就够了,他们本身已经具备了表达的能力。如果说菲茨杰拉德已经吸收和融合了最优秀的英语文体家的风格,那可能是因为他的文笔本来就是这样。他对济慈的感情(《夜色温柔》这个标题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让我们想到一个问题:济慈的风格从何而来?济慈的笔触和语调(我们会注意到他的浓墨重彩,因为那是他自己的,而不是他借来的) 自始至终都很成熟:尽管他在短暂的一生中读了大量的书,但那似乎主要是想证明他并非像自己感觉的那样,是个异类。菲茨杰拉德也一样,只不过他很少长时间独处,所以没发现自己很孤独。从很早开始,他的笔调就和别人不一样。海明威年轻的时候听上去像格特鲁德·斯泰因,后来越来越像海明威了,那是自我模仿的典型,我们通常称之为矫饰主义。 菲茨杰拉德从不刻意模仿,尽管他并不这么想,而他的想法甚至也变得不可预知,直到在他生命最后的关口,那些后来被称为《最后的大亨》的未完成手稿集中展现了他的态度。从我们所知的来看,其他作家对菲茨杰拉德最主要的影响,在于他力图避免呼应他们的节奏和语气。如果天才生来就有超强的吸收能力,这也许永远是最主要的影响:次要作家的口吻一听就是他们所欣赏的作家的滑稽模仿,而强大的作家则努力要摆脱这种影响,这也是他们力量的一部分。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菲茨杰拉德精心营造的长岛幻境有点布思·塔金顿笔下的田园小镇风情。杰伊·盖茨比和彭罗德·斯科菲尔德也有遥相呼应之处。要不是菲茨杰拉德压抑了记忆中塔金顿那种通俗杂志风格的浪漫情调,这种呼应还会更明显;如果这些记忆不是如此深刻,从而容易识别的话,它们或许就不那么容易被压抑了。对任何文学创作者而言,年轻时读过的作家一定会在主题、情节和心理等方面开启思路。在这些方面带来启发最多的那些作家,很有可能根本称不上是艺术家;可如果他们是的话,他们一定也会在措辞、节奏和叙事技巧方面提供新的可能。越有才能的作家越不会重复别人的特征。如今已不大有人记得,活跃于五十年代的写手罗伯特·鲁阿克在《猎人的号角》(Horn of the Hunter)等书中对海明威的拙劣效仿。他想像海明威一样生活,把非洲的动物猎杀个遍。对他的创作和动物们都很致命的,是他还想像海明威一样写作,模仿他所有的抑扬顿挫。他从不会试图模仿菲茨杰拉德,但是模仿海明威看似容易很多——至少在一代人中,每一个平庸的美国作家都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海明威的腔调——鲁阿克表现得尤为彻底,他作为海明威第二个可怜的下意识效仿者的地位不容置疑。第一个嘛,唉,是海明威自己。他的作品越来越空洞,他也越来越像在模仿自己,他的例子有力地说明了为什么风格和内容终究是可以分开来的。我们可以认为——事实上,很难不这样认为——自莎士比亚以降,英国文学中的每一位作家都不得不尽力不去模仿他。不可能再出现一个莎士比亚,主要原因是作家不必再浪费时间重复劳动。莎士比亚在每一个传统的主题和表达领域都永远打破了既有的平衡,以至于要逃脱他的影响毫无可能,故意视而不见更是做不到。(以为一无所知就可以保证纯粹的表达,这纯属谬见。)顺从和回避的过程如此根深蒂固和历时长久,以至于实在很难剖析透彻。但是,随着科技和社会组织结构的发展,总会有人做出新的发现。新的领域会被开启,各种探索方式也会不断发展,但是开采新矿也只能在个体的艺术品格所允许的范畴内——在讨论风格、语气、措辞和影响的时候,一定要考虑个体的艺术品格。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可以媲美托尔斯泰描写的高加索森林、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发生的战争。托尔斯泰为现代作家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战争如何把文明人带回原始蒙昧状态。1942年年底,恩斯特·荣格在《高加索日记》中特意呼应了托尔斯泰的影响,还引用他的名字予以证明。海明威无需提名道姓:他早期故事里的森林和树木环绕的小溪回荡着托尔斯泰笔下的枪声和马匹的嘶鸣。海明威借鉴了托尔斯泰的每一种技艺,但是在他所有作品中,并没有安娜·卡列尼娜和渥伦斯基那样的关系。在《太阳照常升起》中,海明威可以想象自己是性无能的男人;可他绝不会把自己想象成懦弱的男人,一个坚强的男人因为情感依赖而变得软弱,这根本不在他的想象范围之内。(这种情况也许在他的现实生活中存在,但可能正因为这样,他就没必要去想象了。)而对菲茨杰拉德来说,安娜和渥伦斯基正符合他想象的内容。在《夜色温柔》中,妮可的存在本身对迪克·戴弗的影响,就好像安娜的存在本身对渥伦斯基的影响。菲茨杰拉德的作品中从没有托尔斯泰的影子,但是他的主题,尤其是爱情主题,总是和托尔斯泰颇有可比性。他们的头脑很像,或者应该说他们的才华很像:因为在艺术中头脑就是才华,尽管艺术才华/头脑是如何形成的也许注定是个谜,因为除了艺术作品这个最表面的现象,我们压根无法深入其中进行分析。不过就菲茨杰拉德而言,分析它的出发点不在《崩溃》,虽然它的确是一件艺术品,但它仅仅表明了一点:当他更广阔的创造力变得支离破碎时,他的文笔仍然能够达到完美的程度。我们可以从两部代表作中任选一部开始阅读,他的创造力在其中得到了完整的体现。 当艺术家的才华/头脑确实存在而且有条件施展的时候,它似乎会自然而然地蓬勃生长。针对这个话题的学术研究可能会产生误导,美术史尤其如此。有很长一段时间,原始蒙昧笼罩着广大地区,但是这可能仅仅意味着绘画、雕木头和制陶器的那些人有问题。很难扼杀这种想法:自然条件下形成的美术作品都不过尔尔。这个想法符合我们自身的能力,毕竟我们这些人连侧身像都画不好。可是法国洞穴壁画即便不是纯粹的原创,也不可能继承自任何深厚传统。 从历史的角度,走向完美只不过是一瞬间的事。岩壁上的那些动物足以让所有艺术发展理论破产。这种艺术已经没有提升的余地了:只能越来越抽象。我们有理由相信,不光自然状态下的美术是这样,所有艺术都一样,甚至包括音乐:需要表达的东西会很快把它所需要的一应技术手段集中起来加以利用。也许可以说,要等到交响乐传统发展到一定阶段,贝多芬才能写出《英雄交响曲》。确实如此,因为有现实的考虑:首先,所有乐器得要发明出来,很少乐器是为了凑齐一只管弦乐队而发明的——大多数乐器的发明是出于各种不同目的。但是巴赫不需要太多前人的经验也照样创作出了《十二平均律》,他甚至不需要太高级的击弦古钢琴:只要平均率就行。 上述思路并非是要把个人才华及其构成的问题简单化。恰恰相反:这个问题变得越发费解,更显复杂。解释似乎全无可能。才华可以被剖析,但不是在活力四射的时候。菲茨杰拉德文笔中既优雅又自如的韵律,正因为无从分析,所以不会被误解。创造力也许是科学家以外的人所能遇到的最复杂的现象,要理解它,他们首先要意识到,只有一样东西可以也必须从科学家那里借来用——那就是科学家对什么构成证据这一问题的警觉和关注。比如,一个人说他受到某个人的影响,并不等于他真的受了影响,而一个人没有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他没受过影响。在哲学领域,有才华的人们总是努力说真话,可他们当中很少有人能把自己的才思如何运转讲明白。在创造性艺术中,幻想占据了重要位置,内省更不可靠。知名艺术家的建议、经验和教训总是值得听取——歌德显然认为这些犹太法典一样繁琐细致的材料是有意义的——但不能保证艺术家自己也遵循了同样的路径。他们给你的也许是经验之谈,但也完全有可能是系统性地表达出来的天分。他们也许在努力教给你他们自己不需要学习的东西。 不幸的是,很少有人警告我们天分是教不来的。我们猜想,而且很可能猜得没错,如果一个艺术家掌握了超过自身表达所需要的技巧,结果只能是矫饰。同样的猜测也会让我们看到这种可能:艺术家的才华会驱使他们去掌握真正需要的技艺。如果开设一门课程,不管是教音乐还是绘画,那些最好的学生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可是一门创意写作课程除了补充阅读材料之外还能教点什么,的确让人生疑。我们欢迎菲茨杰拉德的建议,是因为他推荐的也正是我们在做的:大量阅读我们能找到的最优秀的作家,包括他本人。事实上,菲茨杰拉德的女儿的确成了一名作家:但和他始终不一样,因为他的天分无法传递。 同样的情况还有里尔克和他写给一个青年诗人的信。《给青年诗人的信》是写给玩具城里魔法娃娃那样的头脑的,不过在我们被它对仗工整、魅力十足的座右铭感动地说不出话之前,我们应该记住,那个青年诗人后来成了一个乏味的老商人,唯一的杰作是配平到无可挑剔的账簿。里尔克和菲茨杰拉德是同一种神经质的两种不同表现,但是在他们所经历的最黑暗的时刻里,两个人多么希望能像他们指导的青年人一样有着普通的抱负和追求,哪怕为此付出再多也愿意。然而,语重心长的建议从需要慰藉的人传给无法从中受益的人,从方向上就错了。若是菲茨杰拉德的女儿给她绝望的父亲写一封实实在在的信,要涉及的方面就太多了:她要告诉他离开好莱坞,回到从前,别总想象自己酒量很大,在上流社会寻找素材可以,但别以为自己可以活在其中,还有最重要的,换一个人结婚——一个他不会伤害,所以也不会伤害他的人。 他当然不会听。让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自救,他也只能表面上承认之前的所作所为全是徒劳——他知道承认也没用。关于菲茨杰拉德有一个基本原理,虽然没法在创意写作课上传授,在普通文学系里讲授也相当困难,但还是值得在这里说说:他的失败让我们少了更多像《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夜色温柔》一样优秀的作品,可他如果不是那样的话,我们根本不会有这两部作品。菲茨杰拉德的文风堪称销魂,因为它的魅力中融合着悲痛。他的写作风格从没改变过,即使有一段时间,按他自己后来的标准,他已经写不出什么东西了。在死亡向他发出召唤时,他还是会那么写。他那么写,因为他就是那样的人:文如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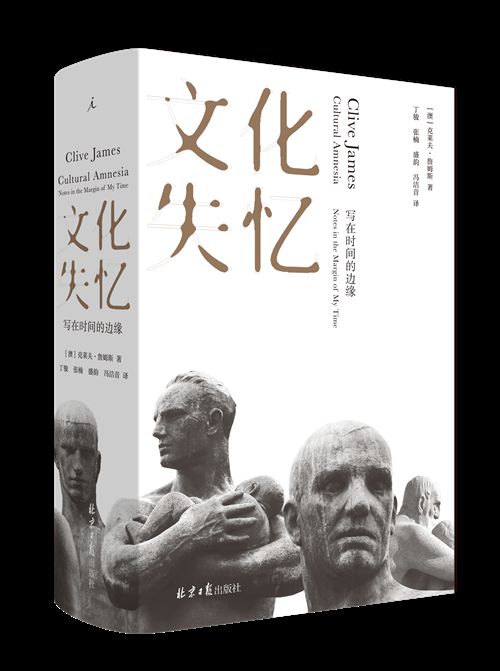 《文化失忆:写在时间的边缘》,[澳]克莱夫·詹姆斯著,丁骏、张楠、盛韵、冯洁音译,理想国丨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9月。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特罗洛普笔下的“养老院”
- 下一篇:华兹华斯诞辰250周年|《水仙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