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的萨哈林之行
http://www.newdu.com 2025/12/16 11:12:10 澎湃新闻 刁绍华 姜长斌 参加讨论
关键词:契诃夫 《萨哈林旅行记》 《萨哈林旅行记》是俄国著名中短篇小说家和剧作家安·帕·契诃夫(1860-1904)的一部大型游记,是他在1890年赴萨哈林旅行的产物,最初出版于1895年。 契诃夫于1880年登上文坛,名声与日俱增。到了80年代后半期,他虽然尚不到而立之年,但已成为闻名全俄的大作家,相继发表了《草原》(1885)、《命名日》(1888)、《乏味的故事》(1889)等名篇佳作。此外,他的第一个多幕剧《伊万诺夫》(1887-1889)也成功地在舞台上演出。1888年他因短篇小说集《黄昏集》而荣获普希金奖金。可是1890年1月26日,莫斯科报纸《今日新闻》突然发表消息说,著名小说家契诃夫不久将取道西伯利亚赴萨哈林旅行。这一消息引起人们议论纷纷,有人同情和支持,但多数人则感到莫名其妙,不可理解。而作家本人又多半以开玩笑的口吻来掩饰他此次旅行的真实目的,譬如2月2日在给C.H.费里波夫的信中说:他“想要从生活中抹去一年或一年半”。 那么,契诃夫究竟为什么要放下成效卓著的文学创作,不顾千难万险,万里迢迢地到孤悬海外的萨哈林岛去呢?  一 契诃夫早在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学习和毕业后行医时就曾参加过法医鉴定,写过这一题材的短篇小说《死尸》(1885)。后来他采访过法庭的审判,写了这方面的报道(如《雷科夫及其同伙的案件》)和短篇小说《法庭》、《审判中的一件事》、《昏头昏脑》(1881-1887)等。他还有些短篇小说,如《小偷》(1883)和《呻吟》(1886),直接描写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的犯人,而《幻想》(1886)则再现一个将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在押犯人的思索。在《打赌》(1888)中,死刑和终身监禁的问题则成为主人公争论的对象。由此可见契诃夫对流放和苦役等刑事惩罚问题的关心。 萨哈林原为中国的领土,称作库页岛,欧洲航海家误用黑龙江口地区的蒙语名“萨哈林(连)”称呼该岛。19世纪60年代,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强占库页岛,沿用了“萨哈林”的名字。为了开发这个面积比希腊大一倍的海岛,沙俄政府开始在这里进行苦役殖民。到了80年代,萨哈林已成为俄国最大的流放苦役地,囚禁着成千上万的在押苦役犯、流放犯和强制移民,其中有俄罗斯人、乌克兰人、鞑靼人、芬兰人、波兰人、高加索人、犹太人、茨冈人等等。这个时期,司法、监狱、流放、苦役等问题,为俄国社会所普遍关注,人们的这种关注反映了对沙皇专制的不满。因此,考察苦役地的情况和了解各种犯人的命运,应该是契诃夫萨哈林之行的重要目的之一。1890年3月9日,他在给苏沃林的信中说:“萨哈林只是对于不把成千上万的人流放到那里去并且不为之花费几百万巨资的那个社会来说才可能是无用和无意思的……萨哈林——这是个无法忍受的痛苦的地方……遗憾得很,我并不多愁善感,否则我会说,我们应该到类似萨哈林这样的地方去朝圣,就像土耳其人去麦加一样,而特别是海员和研究监狱的学者则应该看看萨哈林,犹如军人应该看看塞瓦斯托波尔。从我所读过和正在阅读的书籍中可以看出,我们在监狱中已虐待死了数百万人,无缘无故地虐待,失去了理性,野蛮……”考察流放地的状况,了解犯人被判刑以后的处境,以便引起社会对他们的命运遭遇的关注,这表现出契诃夫作为作家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但契诃夫的萨哈林之行还有更深远的目的。 19世纪80年代是俄国历史上最反动、最黑暗的年代。这个时期,民粹派运动已经瓦解,大规模的无产阶级革命正在酝酿之中。反动势力甚嚣尘上,资产阶级卑躬屈膝、苟且偷安的市侩习气笼罩着俄国社会,一般的知识阶层过着醉生梦死、得过且过的灰色生活。契诃夫从创作一开始便以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为思想基础,深刻揭露了沙皇俄国的黑暗,表现出当时俄国社会“脱离开生活标准到什么程度”,反映了广大群众要求摆脱种种迫害和疾苦的强烈愿望。他向往新的生活,但另一方面却又不了解通向新生活的具体道路。作家明确意识到自己的创作以及整个世界观的这一严重缺陷,他写道:“比较优秀的作家都是现实的,他们写的是现有的生活,但是因为字里行间充满浓厚的目的性,所以除了现有的生活之外,你还可以感觉到应该有的生活,使你入迷的也正是这一点。至于我们呢?唉,我们!我们写的是现有的生活,可是再进一步呢?无论怎么逼,即使是用鞭子抽,我们也不行……我们既没有近期目标,也没有远大目的,我们的灵魂里空空洞洞,什么也没有……”《乏味的故事》就反映了包括作者本人在内的当时俄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这种深刻的精神悲剧,女主人公卡佳刚一踏上人生旅途,便遭受种种挫折,于是向她所崇拜的保护人,有威望的著名学者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教授发问:她该怎么办?可是教授自己也正为这个问题所苦恼,因为他缺少“一般的思想”。“如果没有这种东西,那就等于什么也没有”,“一辈子也找不到归宿”。契诃夫本人当然也深刻意识到这一点,80年代后半期他对自己的生活更加不满意,精神上感到无限苦闷,在给友人的信中抱怨说:“唉,朋友,多么苦闷啊!如果说我是个医生,我就需要有患者和医院;如果说我是个文学家,我就要生活在人民中间,哪怕是一点点社会政治生活也是好的。可是现在这种生活,关在四堵墙里,接触不到大自然,看不到人,见不到祖国,身体不健康,食欲不振——简直不是生活!”正是为了走出“四堵墙”,深入接触社会,解脱思想危机,他在1887-1889年间过着一种“流浪汉”式的生活,四处漫游,先后到故乡塔甘罗格、乌克兰、高加索、克里米亚等地旅行。他还想要去中亚和波斯,甚至产生过环球旅行的念头。他在赴萨哈林途中,在西伯利亚遭受到难以想象的困难,一度发生动摇,想要返回莫斯科,可是一想到自己近年来的精神生活,立即决心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因此,契诃夫萨哈林之行的深远目的即在于从生活中寻找“该怎么办?”这一极重要问题的答案。1890年3月22日,他在给作家伊·列·列昂节夫的信中写道:“若是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办……福法诺夫就不会待在精神病院里,迦尔洵至今还会活在人世,巴兰采维奇就不会患上忧郁症,我们也不会感到寂寞和苦闷,您可以不被戏院所吸引,我也无须奔赴萨哈林。” 二 契诃夫决定赴萨哈林旅行,至少不晚于1889年夏。这时,他的哥哥尼古拉逝世,《新时代报》的发行人苏沃林建议契诃夫赴欧洲旅行,但被他拒绝,因为这时他已另有打算,即赴遥远的萨哈林。同年6月,契诃夫在敖德萨向70年代末去过恰克图和萨哈林的女演员克·亚·卡拉狄根娜第一次透露自己的打算,向她了解旅行的路线和途中有关注意事项,并要求她为之保密。直到翌年1月,契诃夫准备赴萨哈林的想法才被其亲友所知。 契诃夫行前搜集和阅读了许多有关萨哈林的资料,他的“书单”包括六十五种书刊(后来写作《萨哈林旅行记》的过程中又增加了两倍)。按照他的说法,他那些日子完全脱离了“文学”,整天关在家中,谢绝会客,埋头读书和做笔记,满脑子“装的全是萨哈林”。 3月中旬,契诃夫确定了未来的旅行记的总体性质,这将是一部文艺性和学术性兼而有之的考察报告。他还决定在书中加进插图,企图说服画家列维坦与他同行,但没能成功。这个时期,契诃夫也大体上规划了这次旅行的路线:从莫斯科乘火车到下诺夫哥罗德,然后乘轮船沿卡马河到彼尔姆,再乘火车到秋明,从那里乘马车经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伊尔库茨克赴涅尔琴斯克,再转乘轮船从石勒喀河 (俄人称阿穆尔河) 入黑龙江,抵阿穆尔河口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后横渡鞑靼海峡赴萨哈林,在那里逗留两个月;回程是:新潟-上海-汉口-马尼拉-新加坡-马德拉斯-科伦坡-亚丁-塞德港-君士坦丁堡-莫斯科。 契诃夫充分估计到旅途中可能出现的种种危险,对此做了足够的思想准备,启程前夕(4月10日)在给B.M.拉甫罗夫的信中说:“我要长时期离开俄国,有可能永远也不回来……”他甚至留下类似遗言的嘱托,4月15日写信给苏沃林说:“我有一种感觉,好像是我准备去参加一场战争……如果我淹死,或者发生类似的事情,请您记住,我现在所拥有的和将来所能拥有的一切皆归我妹妹所有。” 1890年4月19日,契诃夫从莫斯科启程,但旅行路线略有变化。为了能够多多观赏伏尔加河的风光,他从莫斯科乘火车赴雅罗斯拉夫尔,在那里换乘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号轮船,4月23日抵达喀山,改乘米哈伊尔号在伏尔加河上又航行五天,然后溯卡马河而上,4月27日抵达彼尔姆,翌日乘火车赴叶卡捷琳堡。契诃夫因病在这里耽搁了数日——咳嗽,甚至咯血,他作为医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并没因此而退缩。后来契诃夫向别人谈起他的肺结核时,说在赴萨哈林途中便已开始。5月2日,契诃夫乘火车从叶卡捷琳堡抵达秋明,从此开始了漫长而又十分艰苦的马车旅行。 西西伯利亚真正的春天尚未到来,寒风凛冽,道路难行,桃花水使大小河流泛滥,两岸草地多被淹没,不得不换乘小船,而且途中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险情。5月5日夜间,契诃夫乘坐的马车跟迎面飞驰而来的邮车相撞而被撞翻。5月7日,他冒着生命危险在被额尔齐斯河汛水淹没的草地上行驶,随时都有可能连车带人一起掉进深渊。5月14日,他乘小船渡托木河,天气异常恶劣,风雨交加,险些翻船。尽管如此,契诃夫在旅途中仍然坚持“用铅笔记日记”,记下途中的见闻和感想。5月16日,他抵达托木斯克,在此停留数日,整理“旅途印象”。从托木斯克到伊尔库茨克,契诃夫走了两个星期,这两千俄里的路程更加艰难,常常为了修理被颠簸坏了的马车而等上十到十五个小时,有时又不得不徒步行走。6月4日,他终于抵达伊尔库茨克,6月5日出发赴贝加尔湖,由于途中不能在驿站及时更换马匹而耽搁,到达湖边的落叶松屯时轮船已经开航。他和旅伴们(《寄自西伯利亚》中提到的两位中尉——施米特和麦列尔,还有伊尔库茨克工专的学生尼基金)决定冒险,搭上一条开往克留耶沃的轮船,从那里徒步走了八俄里,到达地角屯,然后乘马车赴鲍雅尔斯卡亚驿站。6月20日,在叶尔马克号轮船启航一个小时之前,契诃夫赶到涅尔琴斯克,结束了从秋明开始的历时两个多月,行程四千多俄里艰难而又危险的马车旅行。 三 登上叶尔马克号轮船,契诃夫的心情轻松下来,他当天写信给友人阿·尼·普列谢耶夫说:“马车旅行结束了;大皮靴收藏起来,脸洗干净了,换了衬衣,莫斯科的小瘪三变成了老爷。”契诃夫在航行期间由于船体摇晃抖动而无法写作,只能利用轮船靠岸的短暂时间给亲友写信。从这些书信中可以看出他乘轮船在石勒喀河和黑龙江上旅行的大概情景,他深深被黑龙江两岸壮丽的自然风光所吸引。 叶尔马克号轮船驶入石勒喀河和额尔古纳河的汇合处,便进入黑龙江,俄人称作阿穆尔河。契诃夫在这条中俄两国的界河上航行,有机会接触到中国和中国人民,对他们产生了浓厚兴趣,叶尔马克号进入黑龙江不久便撞在礁石上,停下来修理。契诃夫在6月21日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我们的船撞到礁石上,撞了一个洞,现在正修理。我们搁在浅滩上,从船上往外抽水。左边是俄国的河岸,右边是中国的。假如我现在回家,就有权夸耀说:‘我虽然没有到过中国,但是在离我三俄尺远的地方见到了她’……在中国的岸上有一个哨所:一个小房,岸上堆放着一袋袋的面粉,一些衣衫褴褛的中国人用抬架往房子里搬运。哨所后面便是茂密的无边无际的森林。”契诃夫早在伊尔库茨克便开始接触中国人,在6月6日的家信中说:“我看见了中国人。这是一些善良而聪敏的人。”叶尔马克号轮船在黑龙江航行时,他有了更多的机会观察中国人。叶尔马克号轮船于6月26日抵达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契诃夫第二天写信给苏沃林说:“从伊尔库茨克便开始遇见中国人……这是最善良的民族……我招呼一个中国人到餐厅去,请他喝点儿伏特加,他在喝酒之前先把酒杯举向我,举向餐厅管理员和仆役们,说道:请!这是中国的礼节。他不像我们那样一饮而尽,而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呷,每呷一口必吃点儿东西。最后,他为了感谢我,给了我一些中国铜钱。真是非常有礼貌的民族。他们穿得不好,但很整洁,吃的东西很有味道,并且很讲究礼节。” 契诃夫在布拉戈维申斯克换乘穆拉维约夫号轮船,他利用启航前的空闲时间游览了对岸的中国城市瑷珲。遗憾的是他在6月29日的家信中对此没有详细叙述,只是写道:“ 我在27日游逛了中国的瑷珲城。我渐渐地进入一个幻想的世界。” 在穆拉维约夫号轮船上,契诃夫跟一个中国人同住一间一等舱。他在29日的家信中说,这个中国人叫宋留利(译音),在7月1日的信中又更正为孙乐礼(译音)。此人会俄语,吸食鸦片,有一定文化,从这些方面判断,可能是地方官员或者在中俄边境一带活动的商人。他向契诃夫“不断地讲述”,说“在中国往往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脑袋搬家’”。他还为契诃夫“按照曲调唱了他的扇子上所写的东西”。这显然是吟诵中国古诗。应契诃夫的请求,这个中国人在空白信纸上写了两行汉字:“我上庙街,我Я也杜你可来子可杜拉四杜”。庙街,即位于阿穆尔河口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因明代建永宁寺而得名。俄文字母“Я”是“我”的意思,下面的一些字是俄文“去尼古拉耶夫斯克”和“您好”的汉字注音。契诃夫用这张写着上述汉字的信纸给自己的家人写了一封信,向他们解释这些汉字的意思。作家还和这个中国人一起在轮船甲板上照相,照片和这封家书原稿至今仍然完好地保存着。 四 契诃夫于7月5日抵达尼古拉耶夫斯克,因市内没有旅馆而在贝加尔号轮船上住了两夜,8号乘该船横渡鞑靼海峡,11日登上萨哈林岛。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他先后寄居在当地医生Б.A.彼尔林和岛区长官公署司库Л. A.布尔加列维奇的寓所。7月12日,契诃夫拜会萨哈林岛区长官弗·奥·科诺诺维奇将军,一周后参加欢迎阿穆尔边区督军安·尼·考尔夫男爵视察萨哈林的活动。这位督军于22和23日两次接见契诃夫,准许他在岛上进行各种调查活动,但不准接触政治犯。7月30日,岛区长官公署发给契诃夫“证明”,准许他为文学写作搜集素材,访问监狱和屯村,采访居民和犯人,查阅有关文件。但与此同时,岛区长官又给其下属下了一道秘令:“密切监视,务使契诃夫先生不得与因犯有叛国罪而被流放和服苦役的人以及受警察监管的行政流放犯有任何接触。” 契诃夫在萨哈林滞留了三个多月,工作紧张而繁重,主要方式是挨门串户地进行人口调查,从监狱到屯村,几乎走遍岛上一切有人烟的地方。他专门印制了一种卡片式的表格,分为十二项调查内容,调查时逐项填写。这种办法使他有可能走进每一个家庭和监狱号房,和每一个苦役犯、流放犯和强制移民谈话,亲眼看到他们的生活状况,了解他们的历史,得到有关他们的法律地位、家庭情况、思想情绪等各方面的资料。这些调查卡片的内容丰富而准确,是作家了解社会的有效方式。虽然有些卡片已经散失,但至今仍保留有七千六百多张,由此可以看出契诃夫当年工作量之大。此外,他在萨哈林还研究了从岛区长官到公署办事员,从监狱看守到普通士兵的生活。岛上的农业生产、商店、建筑工地、学校、医院、娱乐场所等等,以及居民的饮食、服装、居住条件、卫生状况、婚丧嫁娶、生儿育女等等,甚至岛上的自然环境、气候、物产、自然生态等等,以及土著居民基里亚克和爱奴人的生活习俗等等,所有这些都无一不是他考察的内容。 契诃夫不顾当局的禁止,想方设法接触政治犯。前苏联学者在档案中发现,契诃夫访问萨哈林期间,当地共有四十余名政治犯,其中有俄国民意党人,有波兰的社会革命党“无产者”的成员,有波兰立陶宛社会革命党“秘密委员会”的成员。在现存的人口调查卡片中,契诃夫亲手登记的政治犯有二十多人,还有他们的家属,只不过是没有注明其政治犯的身份。这些卡片证明,契诃夫起码与岛上一半以上的政治犯有过直接交往。 9月10日,契诃夫乘贝加尔号轮船离开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前往科尔萨科夫哨所。他在南萨哈林又进行了历时一个月的调查,10月13日乘志愿商船队的彼得堡号轮船启程回国。他原计划归途中访问日本和中国,但不巧的是当时远东一带正流行霍乱,因此他没有可能访问上海和汉口,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停留了五天,然后经日本海和中国海直达香港。这是契诃夫第二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只不过香港当时正处于英国统治之下。他在12月9日给苏沃林的信中写道:“我们经过日本,没有停留,因为日本正流行霍乱……在我们的旅途中第一个外国港口,就是香港。海湾非常美丽,海面上的交通情景,我甚至在绘画上都从来没有看到过。” 1890年12月5日,契诃夫乘彼得堡号轮船抵达敖德萨,经过八个多月的长途旅行之后于12月8日返回莫斯科。他此行最直接的收获,便是《萨哈林旅行记》和《寄自西伯利亚》。 五 契诃夫启程之前就曾答应苏沃林为他的《新时代报》撰写西伯利亚旅行随笔,但要“过了托木斯克之后才能动笔,因为从秋明到托木斯克之间的旅途早已被人描写过,并且已经被人用了上千次”。可是作家在托木斯克停留期间仍然整理了从秋明到托木斯克的旅途印象,写成《寄自西伯利亚》的前七章,并且为该报寄出前六章,后来在伊尔库茨克又寄出第七和第八两章。他在给苏沃林的信中允诺还将陆续寄出“关于贝加尔湖、外贝加尔地区和阿穆尔河的篇章”。但上了轮船以后,情况完全不像原来设想的那样。他在6月21日写信给苏沃林说:“叶尔马克号轮船疯狂地抖动,因此根本不可能写字。由于这种小小的麻烦,我原来寄托于乘轮船旅行的一切希望都落空了。现在能够干的只有睡觉和吃饭。”于是6月20日写完的《寄自西伯利亚》第九章,便成了西伯利亚旅行随笔的最后一章。 《寄自西伯利亚》虽然没有反映出契诃夫在西伯利亚旅行的全过程,但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是相当完整的,其主题与《萨哈林旅行记》一脉相通,是它不可缺少的“序曲”。首先,作者在这里即已开始反对惩罚的终身性,反对沙皇政府奉行的西伯利亚流放殖民政策。其次,这些随笔还提出其他一些重要问题,如崎岖不平、艰难而又危险的道路,地方官吏的专横与腐败,西伯利亚居民的风俗习惯,单调而恶劣的西西伯利亚自然条件等等。作者像是写私人信件一样,无拘无束,信笔写来,使人倍感亲切。他时而援引“驿站里的谈话”,时而借助他人的讲述,时而直接描写个人的种种印象,从而勾画出一幅幅鲜明的画面和众多的人物肖像,如流放犯、官吏、车夫、移民、能工巧匠等等。俄国大画家列宾读过契诃夫的《寄自西伯利亚》之后,1890年7月25日写信给艺术评论家斯塔索夫说:“安·契诃夫寄自西伯利亚的信真是美妙绝伦!” 萨哈林之行对于契诃夫来说绝不是一次休闲的旅游观光,而是一种艰苦而重要的劳动,是一项艰巨的创作任务。他回到莫斯科家中立即投入《萨哈林旅行记》一书的写作,书名为《萨哈林岛》,副题为《旅行记》。但本书的写作不得不时断时续,因为这期间作家还有其他一些事情要做,有许多新小说的构思需要写出来。1891年上半年,除了到欧洲旅行四十天之外,他还写了短篇小说《古塞夫》、《女人们》和中篇小说《决斗》,但到5月底仍然写完《萨哈林旅行记》的前三章。同年12月底,旅行记的第二十三章在文集《救济饥民》中先行发表。1892年上半年,契诃夫又写成《在流放中》、《邻居》、《六号病房》、《恐惧》等小说,下半年则埋头写作《萨哈林旅行记》,1893年6月最后定稿。全书从1893年年底到1894年上半年首先在《俄国思想》杂志上连载,1895年6月出版单行本。 《萨哈林旅行记》不无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的影响,融汇了各种笔法。这里有艺术性很强的描写与叙述,也有带有浓厚抒情和政论色彩的议论,还有客观的考察纪实;作者时而直接记述个人的观察和思考,时而引用他人的讲述和有关文献,从而使本书包罗了丰富的资料。不动声色的艺术性描写、带有抒情成分的议论和学术性的分析论证,相互穿插,加强了旅行记的揭露和批判倾向。全书明显分为两个部分,第一至十三章按照作者的行踪,以时间先后为序,描写叙述了他在萨哈林旅行的过程和对岛上三个行政区的哨所、监狱、屯落、矿坑、各类人物的生活状况以及自然条件的考察;而下半部,第十四至二十三章,则以翔实的材料为基础,每章集中分析论述一个或两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如南萨哈林的爱奴人和日本人,殖民地的农业和渔业,妇女问题,流放居民的衣食和文化教育、道德面貌和重新犯罪的问题,家庭婚姻状况和儿童问题,驻军士兵和地方官员、流放犯外逃问题,流放犯地医疗卫生和疾病死亡等等。但不管怎样变换写法,全书自始至终贯穿一个基本主题:萨哈林是一座人间地狱。 契诃夫在《萨哈林旅行记》中既是一位艺术家,又是一位学者,不仅以极大的艺术感染力描写了婚礼、送葬、肉刑等一系列生活场面,塑造了叶戈尔、“小金手”等许多栩栩如生的流放苦役犯的形象,而且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社会调查和自然考察的第一手资料和数据,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但是,书中艺术描写和学术考察论证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二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譬如岛上的气候本是气象学家的研究课题,但在契诃夫笔下却被描写得生动有趣,使读者有亲临其境之感。作者写作过程中在给友人的信里说:“昨天一整天都忙于描写萨哈林的气候。这种东西很难写,但是终于抓到了要领,找到了门路。我提供了一幅气候的画面,读者读到此处就会感到冷如冰窖。”可以说,全书写人状物都达到了这种艺术境界。契诃夫以冷静客观的态度,通过大量精确的材料,对流放苦役犯和强制移民的悲惨处境做了真实的描绘,字里行间随处都饱含着他对被蹂躏的囚徒深切的同情和对沙皇专制制度的强烈憎恨。 萨哈林之行是契诃夫一生中的重大事件之一,对他后半生的思想发展和文学创作都起了积极作用。可以说,假如没有萨哈林之行,他后来的许多作品就无法写出来。这次旅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促进了他的“成熟”,使他“产生了数不尽的计划”,也就是说,加深了他对许多社会政治和人生哲理问题的认识,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生活和艺术视野,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 契诃夫旅行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决心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感到需要有“哪怕是一点点社会政治生活”,为此而把家从莫斯科市区搬到郊外乡下。他这次旅行之后的创作也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新特点。1892年,契诃夫正是根据萨哈林之行的总体印象,在中篇小说《六号病房》中才能够把专制制度的俄国概括成一座阴森恐怖的大监狱的形象。他的短篇小说《匿名者的故事》早在1887-1889年即已动笔,但一直未能完成,正是由于他在萨哈林与流放此地的民意党人有了交往,对他们有了了解,才于1893年完成这篇反映恐怖主义者活动的作品。契诃夫在萨哈林最早结识的邮局职员爱德华·杜琴斯基是一个莱蒙托夫式的业余诗人,作家后来写作剧本《三姊妹》时即以此人为原型塑造了索连内的形象。完全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作者的西伯利亚和萨哈林之行,诸如《在流放中》等作品也就无从谈起。 至于《萨哈林旅行记》,这部作品虽然被作者戏说成是他的“散文衣橱里”一件“粗硬的囚衣”,但却为这位小说和剧作大师的创作增添了许多光彩,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光辉灿烂的俄国文学宝库。 1995年1月于哈尔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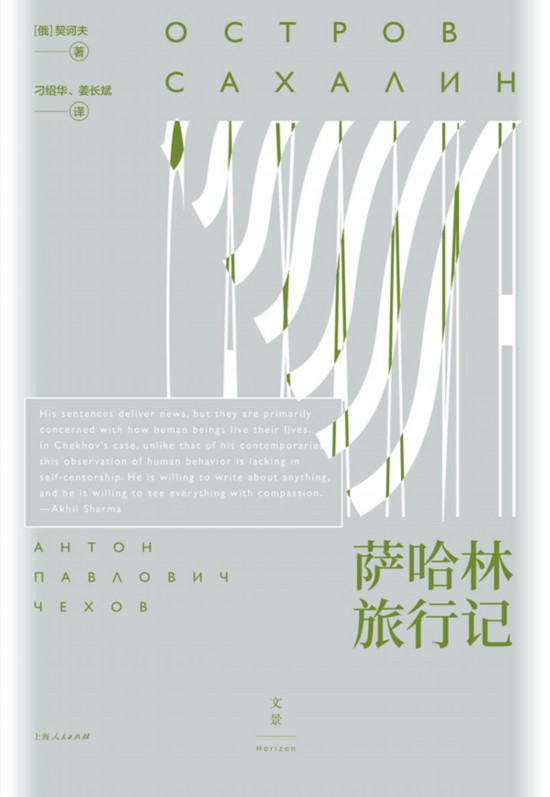 《萨哈林旅行记》,【俄】契诃夫/著 刁绍华、姜长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1年12月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