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生活中最简单的行为转化为艺术:梭罗丰饶的一生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9:11:01 澎湃新闻 钱佳楠 参加讨论
关键词:梭罗 钱佳楠 1.两个梭罗 2014年《纽约客》杂志发表了凯瑟琳·舒尔茨(Kathryn Shultz)对亨利·戴维·梭罗的讨伐文章《湖渣》(Pond Scum),舒尔茨列举了梭罗身上的三大罪状:伪善,厌世,自恋。以梭罗的传世名篇《瓦尔登湖》为例,其实他在湖边住了两年两个月零两天,但是书里将这压缩成一年,如果这可以算作“艺术加工”的话,舒尔茨认为其他的“粉饰”则完全在篡改真相。梭罗每个周末都回家吃晚饭,他的朋友常常来到这座湖畔小屋看他,他的母亲很有可能帮他洗了衣服。对舒尔茨而言,正是因为梭罗从来没有像他书中所说的那样在湖畔生活过,他才会浪漫化这种孤独的生活,他的讴歌乃至以其为基础的道德教谕都是空中楼阁,全无事实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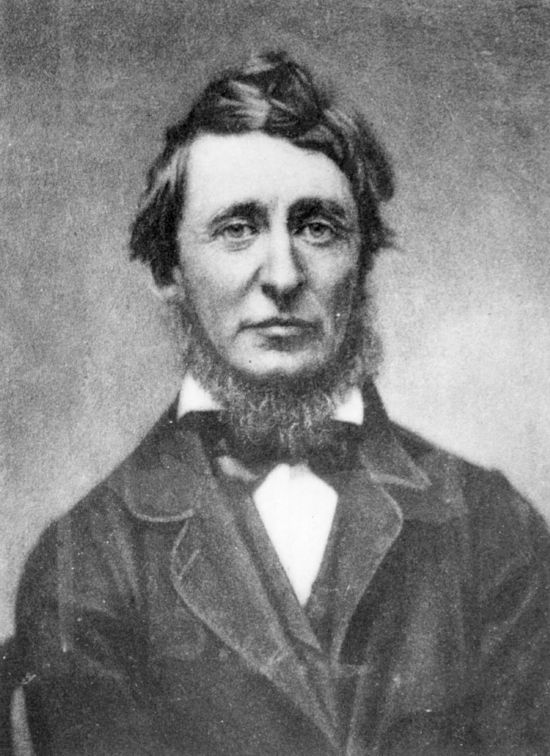 亨利·戴维·梭罗(1817年7月12日-1862年5月6日) 虽然舒尔茨的檄文毫无意外地引起轩然大波,但她远非第一个做出类似批评的人。历史上一直有两个梭罗:一个是《瓦尔登湖》里拒斥人类文明的隐士,他亲手造起自己的小屋,歌咏自立,以此保持道德上的自洁;另一个是《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里愤怒的斗士,他因拒绝缴人头税而入狱,但是他并不惧怕,他走上讲坛,号召他的康科德邻居们不要苟同奴隶制和美墨战争,而要成为“勒停这架机器的反摩擦力”。前一个渴望避世,后一个勇于承担政治责任;前一个栖身于自然,后一个却积极介入人类社会的纷扰。很长时间以来,读者都在思考:究竟哪一个才是梭罗本尊? 劳拉·达索·沃尔斯的最新传记《梭罗传:完整的一生》(Henry David Thoreau: A Life)并不提供这道选择题的答案,而是告诉我们这道选择题本身就是假命题。 在沃尔斯看来,两个梭罗并不矛盾,他们统一于梭罗对信仰的追求之中。众所周知,梭罗是超验主义者(transcendentalist)。美国超验主义受到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的影响,比起规则、逻辑和平衡,他们更重视自觉、直觉和情感;但与此同时,美国超验主义还和新英格兰基督新教独神论派有着更亲密的联系,而爱默生和梭罗毕业的哈佛大学正是当时独神论派的大本营。独神论派和更正统的圣三一教会的最大区别在于,独神论派驳斥基督的神性、祂奇迹的降生以及复活,还有三位一体的概念,通过强调基督的人性一面,独神论派和超验主义者们暗示:人可以直接与上帝交流,且每个人都可以依赖自己的直接经验在此世实现基督的道德完满。(纳撒尼尔·卡普兰和托马斯·卡察罗斯《美国超验主义的起源》)而对于梭罗而言,基督的道德和智慧首先显现于自然。 梭罗出版的第一部作品《康科德和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记录的是他和兄长约翰生前所做的最后一次郊游。他在《一周》的开篇就描绘了鱼儿遭受工业文明蹂躏的画面,它们被无情地卷入比莱利卡水利机械。“谁听见了鱼儿的哭声?”梭罗问道。而后,他总结说:“只有纯真和一项正义的事业来护卫它们的肉身。”可他不知道什么能够帮忙撬开水坝,只能宣誓:“我与你们同在。”也就是说,是在自然里,梭罗见证了爱默生所言的“人就是一捆关联和一团根蒂”(爱默生《论历史》)。这种人与世间万物相互依存的关系威胁了梭罗对人寄寓的道德理想,按照沃尔斯的总结,梭罗在“护卫任何与我们相关的生命体”:遭受人类工业文明威胁的树木和野生鱼类,整个生态系统;奴隶,在掠夺战争中受苦的墨西哥人,以及盎格鲁文明所否定的印第安土著居民。 梭罗见证了他所在世代的人的道德危机,但他没有就此消沉,他相信人可以通过与上帝对话来达到道德上的完满,也就是说,在最有限的程度上,人至少可以抵制周遭的恶,坚守自己的道德。这也是他搬去瓦尔登湖最初的原因,他可以对工业文明和物质主义说不,也可以在自然中接近上帝:他用白松木造起的小屋是“一座庙宇”,“吃”是“一桩圣事……坐在世界的圣餐桌面前”,他希望自己写下的文字成为“一部给现代世纪的经书”。之后,他不断扩大他的责任感,他拒绝缴纳的人头税其实是对奴隶制和美墨战争的拒绝;他一生不断行走,记录,相信“野外保存着这个世界”,他每年记下的康科德每种花的花期、瓦尔登湖融冰的日期、树叶变色的时间,还有降雪的时长和积雪的深度,这些都将成为后世生态学家(当时生态学这门学科尚未诞生)研究气候变化的珍贵材料。他的家庭是马萨诸塞州运送黑奴出逃的“地下铁路”(underground railway)关键的一站。1850年,《逃亡奴隶法》通过之后,每个公民都被要求帮助拦截、保管、归还可能是“财产”的逃亡奴隶,即便后者已经是自由民。这项法案把梭罗的家乡直接变作了奴隶制的温床,震怒的梭罗发表了“马萨诸塞州的奴隶制”这一演讲:“我对国家的记忆糟蹋了我的散步,我的思想对于国家无异于谋杀,我非自愿地走向了对她的颠覆。”九年之后的1859年10月,约翰·布朗以暴力袭击的方式来反抗奴隶制,起义失败,布朗入狱,面临的是叛国罪的指控。在所有人都将布朗视作疯子或者以沉默谋求自保的时刻,梭罗第一个挺身而出,在公开场合发表名为“为约翰·布朗上校抗辩”的演讲,他在布朗身上看到的是基督的道德完满,以殉道的方式来救赎美国的原罪,这和他年轻时候的想法一脉相承:“没几个公民会接受召唤或有能力成为殉道者,但有些人是殉道者,”梭罗的责任在于,“当这样的异见英雄现身的时候,他们不应被视作疯子,而应被视为救世主。” 2.时间的深处,星辰的高度 梭罗1817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距离今天已经过去了两百年有余,很多梭罗成长时期的“常规”在今天看来或许不可思议。这其中首先包括他所接受的学校教育:梭罗就读的康科德书院是镇上精英阶层改良原本免费但不尽如人意的公立学校的产物,他们致力于把男孩们送入大学(当时的女性无法入读大学),书院设有全套课程:拉丁文和希腊语,外加法语和意大利语,英语的修辞学和作文,数学,一些化学和自然科学,一点儿历史和地理。 虽然这个学校将会走出一大批杰出人士,法官,参议员,至少一位著名作家,但是学生们认为这是“最差劲的学校”。当时学校教育的常态是用戒尺建立权威,有一天,不满如此“伺候”的男孩把戒尺在校长菲尼亚斯·艾伦(Phineas Allen)头上敲成了两半,在此以后,学校“彻底降格为无用的机器”。中学毕业后,他就读的是赫赫有名的哈佛大学,但这所名校当时正处于其历史上的低谷,督导会记录下晨祷的缺勤和违纪(包括没有穿上规定的黑色外套),以此给学生评定成绩,批评家说学校的课程“落后于时代”,每届学生被严格分开,同一拨学生一起上每学期的标准课程,由同一批教师执教,听不到其他观点。哈佛的教授在课外不和学校交流,梭罗感到自己来到了另一个康科德书院,“年轻人被置之不理,只能依靠同伴的相互学习以取得进步”。 所幸的是,非常有限的学校教育让梭罗把目光投向了学校之外。更幸运的是,一场打破学校围墙,倡导全民教育与知识共享的学园运动很早就影响了梭罗的一生。这场运动由约西亚·霍尔布鲁克(Josiah Holbrook)发起,“他想象这样一个美国:所有工作阶层(不,所有公民!)能够受到科学知识(不,所有知识!还有艺术、文学和历史,所有有用的、和生活密切相关的知识)的启迪”。1828年,梭罗11岁的时候,康科德学园(Concord Lyceum)的动议经过全镇公民投票一致通过。每年两美金的费用,每个公民可以在周会携带“两位女眷,如果结婚,可以带上孩子”,会议由演讲和辩论组成,多有关政治议题,比如“该州是否应当建造连通波士顿和奥尔巴尼的铁路(是),学校是否应当禁止体罚学生(否),把印第安部落从他们的原住地迁移到密西西比以外是否正确(没有结论)。学园的讲座总是引来满屋的听众,大家都迫切地学习地理、历史、政治、神学和科学知识”。 如沃尔斯所言,学园对梭罗的重要意义是无法估量的。梭罗在这里汲取知识,开阔眼界,他母亲运营的家庭招待所常常是讲座嘉宾下榻的不二选择,年少的梭罗不用出家门就能看见世界,因为世界自会来到他家。而当梭罗成为作家之后,他包括《瓦尔登湖》《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科德角》在内的诸多名篇都首先作为讲稿在这里发表,学园的听众——他的邻居——给他提供了最初的反馈和建议。 更重要的是,学园启发梭罗把生活本身就看成是对真理的追求。梭罗思索着,我们为什么要在“成年的时候离开教育”?“应当让乡村成为大学”,成为公民可以在余生继续追求文理知识的不寻常的学校,大家联合起来支持艺术和教育,不是为了让这个村镇能走出几个杰出人士,而是让它成为“所有人的高尚村镇”。 他的知识没有边界,正如对真理的追寻不应存有边界,年幼时,康科德“独神论派”和圣三一教会的纷争造成了梭罗家内部的分裂,母亲辛西娅和三位姑妈持有不同的宗教观点,梭罗目睹着冲突所造成的伤害,暗暗决定“拒绝一切”:“不应该建礼拜堂,因为真正的教会不在某栋建筑里,而且不应当被某个体制限制。”在往后的人生中,他除了要求自己钻研《圣经》,还进而学习其他主要宗教流派的经文,包括印度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他希望找到“精神真理的真正源泉”。往后,他把印度教和基督教放在同一纬度赞颂的篇章会被保守的新教徒视为“亵渎”,但这却是他超越同时代人的卓越视野。文学也一样,对他而言,文学从始至终就是“世界文学”:“荷马,维吉尔,《圣经》,印度和中国的典籍,古英语诗歌……一直到新近的德国哲学和科学,法国人关于新大陆的历史研究,英格兰最前卫的浪漫主义诗歌,苏格兰最雄壮的散文。梭罗把上百卷书里摘录的笔记填满了几十本本子,创建了属于自己的图书馆:诗歌,历史,科学,人类学,旅行,探险。他无穷的好奇心意味着他家后院的蛛丝马迹都可以将遥远的时代和地域带到他身边:耕作的农民让他想起维吉尔的《农事诗》(Georgics);南极探险者帮他分析的是新英格兰的冬天;爱尔兰的劳工为他展现的是瓦尔登湖里的《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 其实梭罗一生因为受限于经济条件,主要的活动范围就是康科德以及附近的新英格兰地区。但是,他对知识的好奇让他对这些包括森林、田野、山丘在内的“公共领域”的探索具有了非同凡响的意义。如沃尔斯所说:“当梭罗在康科德和梅里马克河上泛舟时,他经过的是时间的深河;当他沿着科德角的海岸行走时,他把脚趾探入了环绕地球的大洋;当他站在卡塔丁山的山脊上时,他是在星辰的高度呼吸这颗星球稀薄、冰冷的空气。”当他成为测量员之后,他用双脚一步一步获取马萨诸塞州的知识,“漫步成了写作的同义词,测步距宛如衡量音步”。因为从不限定自己的知识边界,时间的深处、星辰的高度就成了梭罗看待世界的视角。 3.行为艺术与思想的播种 梭罗的另一个成长背景,如沃尔斯所言,是当时颇为“原始”的美国民主制度,这一制度充满实验性和不确定性,尤其在康科德,“美国完全成了家族产业,由一代人挣得,再传递给下一代人”。这种粗野制度的好处是,作为康科德公民的梭罗感到了无上的责任,他“为自己重审美国民主制度的根基”;但是另一方面,这个根基千疮百孔,物质主义猖狂,经济完全仰赖奴隶制,既得利益阶层想方设法使这项处处不平等的制度继续运转下去。梭罗深感自己不能相信这些人,“他必须为自己来实验”。 值得注意的是,梭罗不能完全相信的人也包括当时美国文坛的雄狮: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不可否认,在梭罗的一生中,爱默生都扮演着对他影响至深的导师和挚友的角色。1836年,梭罗正在哈佛大学依靠奖学金苦苦支撑,爱默生则搬到了康科德定居,次年8月,爱默生会在哈佛发表重要的演说“美国学者”,宣布学者的“自由”和“独立”。梭罗并不在听众席里,他和爱默生初次见面的具体时间如今仍无法确知,但是至迟在1837年10月22日,他们相遇了,因为那一晚梭罗记录下爱默生对他看似无心的建议:“‘你现在在做什么?’他问道,‘你记日记吗?’”就是因为这句话,梭罗开始了这项会一直延续到生命尾声的习惯:记日记。两个月之后,梭罗应邀加入了爱默生的“超验主义俱乐部”。但是,比起已成为文学常识的两人之间亲密的友谊,沃尔斯所追溯的两人之间思想的嫌隙展现了梭罗对自己的不同期待。 1844年,27岁的梭罗应邀在波士顿发表有关反对奴隶制的演讲。此前,爱默生刚在同一个地方做过题为“新英格兰改革者”的演讲。在演讲中,爱默生嘲笑了两种改革的极端:“一种是骄傲的异见者和‘形单影只的否决者’,他们只拥护‘王国为我造’;另一种是放低身段只‘适应协会能够达成的绝对共识’的公民。”爱默生的立场是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地带。然而,梭罗在自己的演讲中,首次公开划清了和爱默生的界限,因为梭罗自己就是骄傲的异见者和形单影只的否决者,他不再相信爱默生固守温和派立场的“言辞”,他对听众说:“给我们看行动”,“行为要比言辞有力”。也就是说,从这一刻开始,梭罗的偶像不再是爱默生,而是践行道德标准的废奴主义者温德尔·菲利普斯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后者是《一个美国奴隶的生平自述》的作者),梭罗渴望用自身的生命经验来“颠覆并持续颠覆封闭的传统和舒适的习惯”,把他的抗争“变作一项又一项行为艺术”。 “行为艺术”是沃尔斯的原话,她在此用作褒奖,意指梭罗把生活中最简单的行为都转化为富有内涵的艺术。但她当然也知道这个词的贬义外延,在谈到梭罗在当时就富有争议的“瓦尔登湖”生活实验时(爱默生警告说:“绅士不会住在棚屋里。”),她也不无遗憾地感慨:“他在瓦尔登湖生活的两年两个月零两日会成为而且永远是讽刺的行为艺术。”这也是后世,尤其是政治学者争执不休的论题:类似梭罗这样的“形单影只”的公民不服从行为究竟有没有效力? 汉娜·阿伦特是对此类“行为艺术”最有影响的批评者之一,在她看来,如梭罗和苏格拉底这样独异个体的“公民不服从”只会被公众当成怪物围观(阿伦特《公民不服从》)。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杰克·特纳(Jack Turner)则反驳说,当梭罗在公众面前“表演良知”(performing conscience)的那一刻,这种表演已经在观众之中得到转化,观众的良知会被唤醒。 这里边一来一回的论证牵扯很多维度,特纳的驳论作为与阿伦特的对话写于阿伦特逝世多年之后,但是,阿伦特原文中的很多观点仍然可以用来质疑特纳,比如,所谓“良知”应该如何定义?梭罗的良知是他在《瓦尔登湖》里谈及的“更高的律法”,有着重要的信仰语境,然而在阿伦特看来,当社会走向世俗化,上帝的“良知”不再被共享,也就是说,让梭罗感到“污浊”的恶并不影响其他人的良知和生活,因而,指出“罪恶”的行为本身不具备转化力量,更不可能是启蒙的保障。 沃尔斯换一个角度来看待梭罗的实践——作为作家而非政治活动家的梭罗。她不否认梭罗在世时影响力有限,他的巅峰之作《瓦尔登湖》在他离世的时候也没把首印的两千册卖完,他的演讲在吸引喝彩的同时也饱受批评和抵制,在世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指责他厌世、伪善和自恋,这些都符合阿伦特的观察。但是,以为暴力反抗奴隶制的约翰·布朗上校辩护为例,梭罗的朋友奥尔科特的评价是中肯的:“布朗直接攻击体制,梭罗只满足于从旁批评他们。”沃尔斯把这些看法都纳入了她的传记,然而她同时指出,如果没有梭罗,没有之后所有追随者的话语,“布朗的刀剑和来福枪不具备更大的力量——它们只是残杀身体的武器,是抵抗国家的暴力工具,而这个国家当前用同样的武器摧毁了布朗。约翰·布朗的刀剑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没有那些文字,它们只是刀剑”。也就是说,梭罗的文字和行为把他自己和其他杰出个体的生命经验“转化”为思想和艺术的同时,这些经验就超验于平凡且会随时间流转而失去价值的日常生活。 梭罗所践行的这项事业像极了在他生命末梢带给他莫大希望的种子。“毁灭是容易看到的,它突然而且壮观:每个人都能听见大树的垮塌。但是谁能听见树的生长,听见生命缓慢,但永不停歇的创造过程?”梭罗认为,只要把时间的维度拉长,从整个星球而非人类本身的维度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到自然“缓慢但确凿”的再生。 距离梭罗离世大约一个世纪之后,他的“公民不服从”在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各自的民权运动里被转化成武器,梭罗原本显得过于天真的号召在那两场影响深远的非暴力抵抗运动里成为现实:官员出于道德愧疚而辞去公职,有意识抵制的公民一度将监狱填满,使得政府机器被这些“反摩擦力”拖垮,不得不做出让步和调整。梭罗的效力不是通过“表演良知”那一瞬间得以实现的,而是通过书本,通过作者和读者一对一的精神交流,他播下思想的种子,润物无声,我们把时间的维度拉长,最终在一个世纪之后见证了人类社会“缓慢却确凿”的成长。 梭罗的一生短暂,他45岁那年死于肺结核的时候,南北战争刚刚打响不久,而且此时的北方仍处于节节败退的时刻。可以说,梭罗的一生正是在美国终结奴隶制最黑暗的前夜中度过,他的愤怒、哀愁、沮丧或许是那个年代有良知的人再正常不过的反应。不过,令沃尔斯敬佩的是梭罗身上对走入“良夜”永远做出拒绝的姿态,也是因为这个姿态他永远在其对人性、对自然和对文学的笃信中发掘出无限的希望。他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不是徒劳的。这就是文学的价值”;他相信“大地上没有一个地方低到不能望见天堂”;他也相信人可以挣脱物质的枷锁,不断往前走,“自由地走进天堂”。 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黑暗,每个时代有良知的人都有着各自的无奈和绝望,然而,梭罗的希望和信仰或许能够给予我们力量,让我们不畏于或许注定是痛苦且在我们在世时看不到结果的生命实践。 钱佳楠 2020年1月1日 于美国圣路易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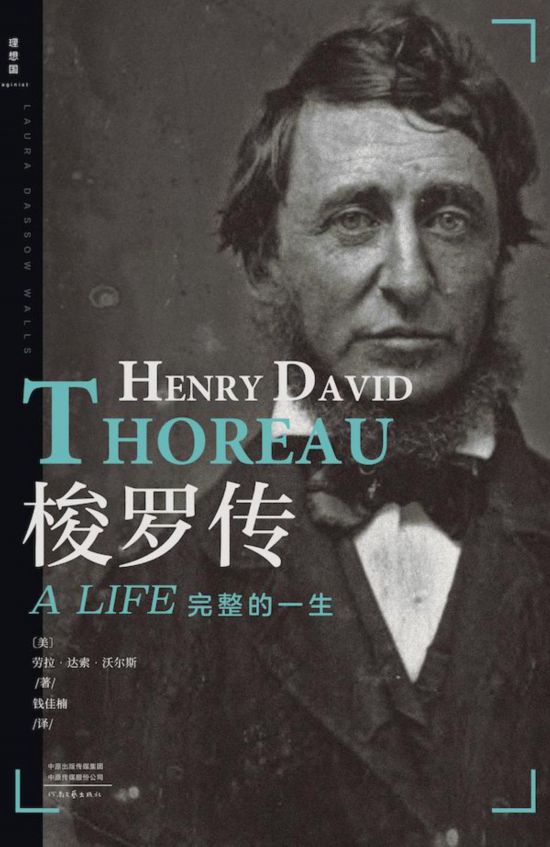 《梭罗传:完整的一生》,【美】劳拉·达索·沃尔斯/著 钱佳楠/译,河南文艺出版社·理想国,2021年1月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