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小说作家”、“雨果奖中短篇获奖者”,这些符号在指向了刘慈欣之后,再次指向了一位“80后”作家郝景芳。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郝景芳却在近期出版了一部被诸多媒体称为“现实主义方向”的作品《生于一九八四》。想到“1984”,最有名的自然是奥威尔在《1984》的政治寓言。虽然《生于一九八四》中有诸多致敬《1984》的桥段,但作者郝景芳并没有聚焦大历史的诸多变化与内在动因,而是以个人为切入点,进行叙述,聚焦于日常生活的种种压抑、曲折。事实上,尤其是在今天,作家对于日常生活的处理相对于宏大叙事有时更为棘手。正如南帆所说:“个人以及日常生活之中,压迫与解放的主题复杂多变,远非政治学、经济学描述的那么清晰。压抑也是一种压迫,但是前者远比后者隐蔽、曲折、微妙、广泛,焦点更多地聚集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区域。”
《生于一九八四》将注视点转移于日常,本身就是一种勇气。而这种勇气出现在一个“80后”作家身上,则更显得可贵。作者以1984年为时间节点,记述了当时中国的众多变化:工商银行成立、邓小平视察深圳特区、中国夺得奥运会金牌……这些在1984年发生的标志着现代化重大事件,成为了属于当时的特殊符号,足以彰显1984年本身的特殊性。在许纪霖、陈达凯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中,曾经将M.列维所分类的后发的现代化国家的刺激诱因总结为“生存挑战和现代化的示范效应”。可以想见,1984年的中国,个人所面临的情况则更加严峻:一方面,瞬间的开放使得诸多本来逐渐推进的现代结构瞬间爆发,资本所带来的物质富足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对于物质的需求的阈值;另一方面,过去的国家意识形态的瞬间转向,“集体意识”转向了“个人意识”,使得个人变得无比迷茫。而在《生于一九八四》中,这种迷茫以两代人的生活轨迹加以呈现。

轻云的父亲是最先应对1984年诸多变化的一批人。作为一切变化的起始点,父亲的经历既是一种“生活典型”,面对的生活与过去的割裂也更加的痛苦。父亲1984年与朋友王老西合作,利用制度的灰色地带去深圳倒卖外汇,而王老西的错误举动使得这一行为接受了调查,父亲为躲避风头,从而出走英国。而父亲在国外的生活却也并不如意,屡次更换国家以疏解自己的心结,却愈发不解。
而轻云(我)的故事则是始于大学毕业。轻云面临毕业的时候踌躇不定,几乎没有任何计划,而后被母亲安排进审计局工作。而后轻云不甘于这样生活,投奔了朋友林叶,短暂地收获了一段爱情,却仍旧内心无所依靠。最终,轻云在经历了病痛之后回归了内心的平静。
如果用一个词可以形容轻云的状态的话,便是“格格不入”。作者在后记中表示:“这是一本非自传的‘自传体’小说”。在采访中,郝景芳谈到这本书的创作时也说过:“这是内心‘焦虑’和‘解决焦虑’的过程。我曾在生活中遇到各种压迫感,有来自同龄人的压力、有比较的焦虑。而这些焦虑的根源是什么?我试图追寻这个来源,于是动手写下了这本小说。”虽然轻云的人生经历郝景芳或许并没有经历过,但轻云所遭受的生活中的各种压迫与焦虑,正是郝景芳作为一个现代人所正在承受的。那么一个问题就此提出:小说中,主人公轻云的焦虑感来自哪里?是否只是表面的生活压力与焦虑的投射?
事实上,作者给出的答案并不那么简单。作者在文中给出了诸多压力与焦虑的来源:个人精神的物化,社会评价体系的资本化,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功利性……然而这些更像是郝景芳所提供的现象,而并非本质。我认为,郝景芳所认为的内心焦虑来自于两点:一、外部价值观对人的自主性的麻痹;二、外界对于人的个人价值评价。前者是焦虑的来源,而后者是焦虑传递给每个人的途径。以轻云为例:在郝景芳对于轻云的书写中,轻云仿佛一直处于一种“出离状态”,即几乎没有自己的想法与见解。轻云的生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最开始选择就业的焦虑期,与林叶在北京的“自由”期,和最终的放下一切的释然期。抛开最后一个阶段不谈,在前两个阶段,轻云的行动除了“追求自由”的一次辞职,她的每一次行动几乎都受到了身边人的各种影响。诚然,每个人的行动或多或少都会为他人所左右。然而发生在轻云身上的则是自我的抽离——自己没有决定,命运为他人的价值观所裹挟。这里面我需要提到一个使得轻云做出改变的人——平生。平生出现于轻云在北京的时期,并与轻云成为了恋人。他知识丰富,旁征博引,积极入世。然而他却不愿甚至是不敢发表自己的见解。轻云也感觉到了这点:“对所有问题都只点评他人,不谈自己。他引述西方大师、推崇某些人、对某些人不屑,可是当我问他自己对这个问题是什么看法,他每次都能用其他引述把问题转开。”可以说,平生与轻云有着某种相似性。对于外部社会两人有着某种恐惧,恐惧于被人忽略,恐惧于被别人的价值观所抛弃。只不过平生有着“自信”与汗牛充栋的理论作为伪装。最终,他背叛了轻云,喜欢上了一个崇拜他的女性,或者说是喜欢上了被注视与崇拜的快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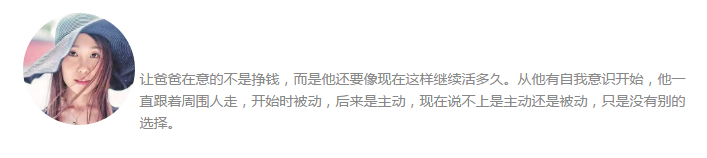
可以说,轻云对于平生的审视促成了轻云自己的反躬自省。他者在注视自己的同时,他者同时也在渴望着被注视。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只能是“压抑”。郝景芳在书中为轻云解决压抑的方法是摒弃他人的注视,回归自己内心的自由平静。除此之外,郝景芳也指出这种压抑的外在环境会随着时代变化有所不同,其精神内核却有着高度一致性。为了表达这点,郝景芳刻画了父亲追求自我自由的生活历程。
相比于轻云的情感历程,父亲的情感则更为隐蔽。父亲在1984年的出走,虽然情节上是一种偶然,但同时郝景芳也用自己的记述指出了其中的必然性。郝景芳记述了父亲在过去的两件事情:第一件是父亲在下乡时期的恋人为了回城的机会果断地抛弃了他,获得了回城的机会。第二件是在“文革”时期,父亲啐了自己的父亲一口唾沫。在特殊的年代,爱情、亲情的背叛仿佛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一旦政治语境抽离,日常生活降临之时,羞耻、愧疚,逼迫着父亲去逃避、抵触别人的注视与注视背后的价值评价。郝景芳这样描写父亲在考虑做生意前的心理:“让爸爸在意的不是挣钱,而是他还要像现在这样继续活多久。从他有自我意识开始,他一直跟着周围人走,开始时被动,后来是主动,现在说不上是主动还是被动,只是没有别的选择。他不曾选择那些事情,他只想挨过那些日子,一段难受的日子接着一段难受的日子,挨过这段,争取再挨过下一段。他有过抱怨,但他也明白他没资格抱怨,这是他第一次觉得也许可以做个抉择。”父亲确实自己做了抉择,但是却无法逃避他人的关注。不断更换国家,便能看出他一直在渴求着自由,却从未真正找寻到。当然,作者也给读者留下了悬念:除夕夜的敲门声是否是父亲的归来?如果是,父亲是否已经获得了内心的平静,从而能重新弥补之前的遗憾?

郝景芳在作品中的一个突破,就是在处理当代题材时并没有预先设立社会道德的善恶,而后机械地重复当代社会的种种问题并加以批判。简单地重复不仅容易沦为现象的堆砌,且更像是一种责备,缺乏深度与力量。正如李敬泽所说:“对小说家来说,善与恶不应是先验地给定的,而应是在对人的生活、人的灵魂的追问中雄辩地榨取和展现的。”
但在《生于一九八四》中,郝景芳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在这里我愿意提及郝景芳的雨果奖作品《北京折叠》。故事将北京分为三个不断折叠变换的空间,三个空间的等级森严异常。故事的主角老刀为了生存,不得已穿越三个空间的分界,以赚取报酬。很显然,郝景芳以折叠的北京隐喻阶层的固化与残酷。虽然这部作品属于科幻小说范畴,但是其内核同时也具有现实主义特征。而郝景芳这篇文章的创作动机仍旧来自于日常生活。媒体这样形容她的创作:“郝景芳租住在北京北五环外的城乡结合部。楼下就是嘈杂的小巷子、小苍蝇馆子和大市场。有时候,她在楼下吃东西会和店主聊天,听他们说着远方的家人孩子,听他们在北京看不起病的忧伤困扰。她坐出租车的时候,会和司机攀谈。司机讲起自己的孩子上幼儿园排一夜的队,还未必能入园。北京有重大活动,会采取一些限制措施,街道不再熙熙攘攘,而是变得整洁漂亮。郝景芳想:‘有一些人是可以藏起来的,藏在看不见的空间。有了这个暗黑的想法,当然可以把某些人群永远藏在地下。’”郝景芳专注于日常的表达,但是《北京折叠》的创作,却为了表达而舍弃了人物的复杂性,使人物脸谱化。譬如《北京折叠》中的老刀是社会底层希望改变生活的劳动人民的典型,秦天是社会中层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学生典型,依言则是社会高层具有主宰社会权力的人的典型。作者将北京划分相对独立的、个性鲜明的三个阶层,却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整个社会的复杂度。读者在读完之后不禁想问的是:这样的设计是否真正表达了作者的写作意图?三个阶层的划分对于政治的隐喻是否存在着过度阐释?
而在《生于一九八四》中,郝景芳笔下的轻云相对于《北京折叠》中的老刀自然生动了许多——轻云有了复杂的自我变化。但是,轻云身边的人,仍旧存在着脸谱化的问题。以轻云的同学何笑为例,她智慧、干练、果敢、有思想。她的未来读者几乎可以预测到——她会成为一个具有富足生活与独立品格的完美女性。同样,林叶的伪装与博取关注的欲望,使得其个性过于单薄,人物的性格整体偏向于“单向度”。郝景芳对于描绘社会有着自己的野心——在《生于一九八四》的第十三章中,郝景芳罗列了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符码与情感宣泄,并不加任何分隔符号。显然,她在隐喻纷繁复杂的社会状态,并希望在自己的作品中描绘整个社会的生活境况。郝景芳对于自我境遇的洞悉已经开始成熟,那么她现在需要解决的是如何洞悉他者的精神状态,并正视其复杂性。
虽然,郝景芳的创作仍旧存在着改进的部分,但是至少在郝景芳身上,读者能看到未来郝景芳的文字的无限可能。而对于文学批评者来说,则可以看到反思当代社会的一个新的着力点:细致考察当代人的精神境况,或许比书写社会的荒诞更能直抵人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