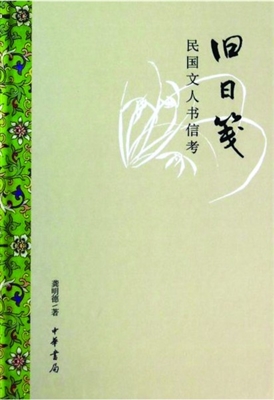二十五年前初识香港著名文学史料家卢玮銮,笔名小思。她不无感慨地对我说:“真佩服内地学者,弹指之间就能写出一部文学史。我是香港人,搞了半辈子香港文学史料,也还不敢写香港文学史!”小思所说的“佩服”当然含有弦外之音,但也切中当下内地学界的时弊。可不是吗?少则半年一年,多则三年五载,一部“新时期××史”,“二十世纪××史”“中华五千年××史”乃至“世界××史”就热腾腾地出笼了。我也曾有此经历。那是1958年夏天,我还是南开大学中文系二年级学生。当时全国各条战线都在创奇迹,放卫星,牛皮吹破天也不纳税。我跟一些同学在高年级同学、诗人小剑(已故孟伟哉)的领导下,发挥诗人的想象力和激情,居然在半月内写出了一部《苏联文学史》。当时敲锣打鼓向系党总支报喜的情景,至今历历如在目前。 我特别崇拜那种思想深邃的理论家,在擅长搞宏大叙事的学者面前也自惭形秽。不过,按生活常识判断,兴建崇楼广厦不也先要备好一木一石吗?言不及义的烦琐考证固然不可取,但科学的探微索隐难道可以缺失吗?有学者说,原典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如果原典的面貌模糊,甚至颠倒错乱,以此为据的“宏大叙事”岂不等于痴人说梦?最近有人发表高论,说文学研究(特别是鲁迅研究)不是科学,理由是阐释作品没有标准答案。我倒是认为文学研究不但是科学研究体系中的一个分支,而且文学研究中的考据学是最符合科学求真精神的一门学问。然而在当今的学术评估体制下,倾情于考据的学者受到的待遇是极不公正的。不管用什么手段,只要能在所谓核心期刊上发表两篇所谓论文,就可以评上研究员或教授,工资、奖金也会随之飙升。而考据方面的文章却往往不被当作学术成果,写这类文章的人或被视为迂腐,或被视为低能。有人把当今社会里出现的某种畸型现象概括为“劣胜优汰”,比如在市场上大豆酿造的酱油被化工调制的酱油击败,正常的黄心鸭蛋被注射过苏丹红的红心鸭蛋击败,优质食用油被廉价地沟油击败……当然,一切比喻都是跛脚的。我这样说,绝不是不加辨析地以微观考据为“优”,而以宏观思维为“劣”。只是认为微观考据中有可以传之久远的“干货”,而有些峨冠博带的宏论,其实掺有必将迅速化为泡沫的“水货”。我更希望这两种研究能在学界受到同等尊重,这两种类型的学者(不是“伪士”)能长相敬而不相鄙。如果比喻失当,言词偏激,也无非是为那些被冷落的考据派学者鸣不平而已。记得鲁迅说过,鹰攫兔子,叫喊的是兔子不是鹰;猫捕老鼠,啼呼的是老鼠不是猫。发点牢骚,说点怪话,鸣点不平的人,往往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寂寞者,被压抑者。 跟当今那些像华威先生频频参会又频频早退的“学术明星”比较起来,龚明德其人的确是寂寞的。他曾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六场绝缘斋”,表示他置身于当下这个急功近利、喧器浮躁的社会,执意要跟官场、商场、赌场、情场、舞场、赛场绝缘。我曾请教他为何要把“赛场”也归入“绝缘”之列?回答是:“赛场除开斗牛、赛马,主要是人跟人较劲,我不愿把有限的精力耗费在与人明争暗斗上。”明德兄不仅立斋明志,而且身体力行,这在当今学界当然难免打入另册。不过,“六场绝缘斋”飘溢的书香,不仅有浓郁的芸草香味,而且蕴含了无穷的人生智慧。学术智慧,这又是令人羡慕,令人神往的。 据拜谒过“六场绝缘斋”的人士说,这其实是一处五十平方米的宿舍,居住着明德兄一家五口。那几万册珍本书刊,有的藏在墙壁内,有的则打包装箱。古代搞考据的文人有“鬻田买书”或“廉俸所入,悉以购书”的传统。明德兄也是布衣粗食、囚首垢面而购书。1997年2月,我收到了明德兄寄赠的《新文学散札》,收录了他五十篇精彩纷呈的考据文章,后来才听说,这本书是靠友人捐助才得以出版的;用句糙话说,就叫做:“赔本赚吆喝。” 一部学术史证明,很多传世佳作都是在坎坷困顿中诞生的。我可以断言,明德兄的很多文章都会历久弥新而不是昙花一现。他在文学史料研究领域的成就,除了发掘出一些不应该被忘却的作家(如章衣萍)的生平逸事之外,还有两个亮点:一是版本的考证和汇校,二是书信的钩沉和解密。当今已进入新媒体时代,电子邮件取代了书简尺牍,所以书信的钩沉十分不易,正应了一句古诗:“可怜大地鱼虾尽,犹有垂杆老钓翁。”明德兄就是这种力图竭泽而渔的钓翁。他收集书信的范围从珍稀书刊扩展到文献档案(如1982年5月14日巴金至胡乔木信),又从文献档案扩展到拍卖图录。这些信函大多为作家“文集”“全集”“书信卷”所未收,实可谓用心良苦,功莫大焉! 明德兄收集资料具有视野的开放性,考证资料具有科学的严谨性。一封年久发黄的信,断头短尾,少日缺年,要考证清楚谈何容易?明德兄凭着他的学术功底,增补和纠正了若干信件的写作时间。如原定为1935年12月30日冰心致林语堂信,因涉及向《人间世》 投稿事,被明德兄订正为1934年。手迹辨字也是一门学问。有一封徐志摩致梁实秋信,不足百字,一些版本中的释文错误竟多达十余处。明德兄当然不是什么都懂的神人,但是他细心加虚心。凡认不准的草书他就向书法行家请教。搞史料考证的人,细心和虚心是缺一不可的。 在一般读者心目中,史料考证的文章味同嚼蜡,不堪卒读。明德兄的功力,却表现在能让人从一封看似鸡肋的函件中嚼出美味。比如,郭沫若1959年2月17日致巴金、靳以短简,仅24字,落款尚缺年月。《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 信函卷收入此信时,释文又把“谨请审阅”误辨为“望请审阅”。经作者考订,不仅订正了释文的讹误,确定了写信的年月,而且考证出“谨请”《收获》 杂志两位主编审阅的作品即为历史剧《蔡文姬》。作者又根据1959年2月14日郭沫若致周恩来信,进一步指出直接授意他为曹操翻案的就是周恩来。这就让读者了解到一个经典剧目的发表过程及其创作的政治背景。 在中国学术史上,考据学原本占有一个十分显赫的地位,特别是明清之季,出现了引领风气的顾炎武,堪称中坚人物的戴震,以及集大成者王国维; 考据的范围既有历史事件和书籍版本的真伪,而且包括了音韵、校勘、训诂乃至历算学、金石学等诸多领域,出现了举世公认的学术辉煌。但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考据学的被冷落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除开有前文提及的评估体制、学术偏见等外在原因,也跟考据学后继乏人,未能形成一支充满学术活力的队伍,以及未能产生相应的学科理论、形成具有指导意义的学术专著不无关联。在这种情况下,珍视龚明德这样的“熊猫级”人物,不断发掘其著作的学术价值,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诗经·小雅·伐木》中有一脍炙人口的名句:“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意思是鸟儿在树上啼鸣,是想寻求友伴的共鸣。瑞士汉学家冯铁出版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在拿波里的胡同里》,特请明德兄撰写了一篇序言,题为《富有实证意识的国外学术同道》。此次明德兄增补再版《旧日笺·民国文人书信考》一书,降格以求,邀我写序,也是视我为“实证研究”队伍中的一员。我在引以为荣的同时,仓促写出了以上读后感言,虽自觉敷浅,但也是作为对这位寂寞的耕耘者一种友情的回应罢。 (龚明德著《旧日笺·民国文人书信考》,2013年1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近期将增订再版) 原载:《文学报》2015年08月27日 (责任编辑:admin) |